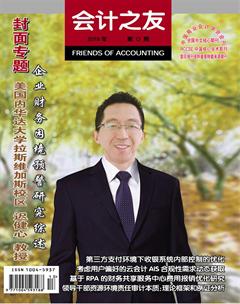共享單車會計核算問題研究
俸芳 籍晶瑩
【摘 要】 隨著智能手機的推廣以及移動支付消費習慣的形成,當前基于“互聯網+”模式下的共享單車實現了共享經濟從閑置資源共享到專門資源共享模式的擴展。比達咨詢數據統計,共享單車2016年用戶規模為1 886.4萬人,2017年用戶規模更是呈爆發式增長。作為具有生命力的新興共享單車,其運營模式受到廣泛關注,因行業特殊性,對共享單車的會計確認和核算仍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文章主要從共享單車的初始確認、共享單車APP軟件的性質界定及確認、后續收入確認三方面提出問題,并就該問題提出相應的建議,為共享單車以及為“互聯網+”模式下共享經濟的會計核算提供參考。
【關鍵詞】 共享單車; 資產確認; 資產計量; 收入確認; 收入計量
【中圖分類號】 F230;F570.5;F572.8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8)13-0133-04
一、共享單車會計核算及運營的相關文獻評述
李漫[1]介紹了基于互聯網分時租賃下共享單車的運行模式,以ofo共享單車為例,從初始確認、后續計量以及押金等會計核算方面提出問題。她指出,共享單車應作為固定資產加以確認,在分析固定資產經濟利益預期實現方式的基礎上提倡采取加速折舊法進行后續計量,相關的調度以及維修成本予以費用化;對于押金收入做負債處理,同時對規范押金收入,保證押金安全提出相關的對策建議。岳會玉等[2]針對共享單車具體營運環節的會計核算進行分析,從共享單車的初始確認和后續費用化、資本化處理簡要概括,在綜合收入和費用的基礎上,就其盈利模式進行探討,指出共享單車行業的利潤維護是可觀的。唐力力[3]就共享單車的成本核算內容加以說明,將共享單車本身作為固定資產加以處理;根據共享單車平臺的具體營運,將收入類型分為租賃收入、廣告和流量收入以及押金沉淀收入三項,分別予以核算,加強共享單車平臺的監管與引導,實現共享單車的規范化、綠色化發展。
通過對當前文獻的搜索,發現較多文章更多地從共享單車押金資金沉淀的性質以及監管問題出發,對共享單車的“共享效益最大化”給出意見和建議,涉及共享單車的會計處理文獻研究不足且只是簡單定性,所以本文將側重于共享單車的會計核算,從共享單車的初始確認、共享單車APP軟件的性質界定和計量以及后續收入確認過程中的確認時點和金額問題加以分析,為共享單車行業以及現行互聯網行業的會計核算提供參考。
二、共享單車的初始確認與計量
對于共享單車的確認問題存在很大爭議,當前大多數涉及共享單車確認問題的文章也是將其按傳統的觀點確認為固定資產,但2006年的企業會計準則對固定資產的概念和范圍進行了重新界定,取消了原定義的固定資產2 000元的價值標準,將固定資產定義為“為生產商品、提供勞務、出租或經營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壽命超過一個會計年度的有形資產”。目前市場上共享單車造價雖不盡相同,但共享單車由于缺乏政府和社會的有效監管,存在人為上私鎖及破壞現象,損壞率極高,很多單車使用壽命超不過一個會計年度。所以將其界定為固定資產并不是十分合理;因此筆者認為應將其確認為周轉材料或低值易耗品,在報表中的“存貨”項目列報。根據準則,存貨是指“企業在日常活動中持有以備出售的產成品或者商品、處在生產過程中的在產品以及在生產過程或提供勞務過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資等”,該定義雖然只提及了“持有以備出售”,而并未將“持有以備出租”囊括進來,但是從報表中存貨的概念可以發現其由很多個會計科目組成:原材料、在產品、庫存商品、周轉材料、低值易耗品等。其中周轉材料,是指企業能夠多次使用、逐漸轉移其價值但仍保持原有形態不確認為固定資產的材料。共享單車價值不高且可以多次使用,雖不滿足狹義上存貨的概念,但由于其行業特殊性,可以將其計入“周轉材料(或低值易耗品)”科目,在財務報表的存貨項目予以列示。
將共享單車作為“周轉材料(低值易耗品)”初始確認,可以采用分期攤銷法、五五攤銷法、一次攤銷法等進行后續計量。正常情況下,類比固定資產攤銷方式,采用分期攤銷法更為科學,但是,由于共享單車的行業特殊性,可以采用更為簡單和適用的處理辦法——一次攤銷法。這雖然看似不合理,無法實現使用期間收入與成本的有效配比,且一次性的全額攤銷較為保守,但是由于共享單車的粗放型使用方式,很難準確地估計其使用壽命。據中國經營報不完全估計,摩拜單車的損壞率高達10%,而ofo單車的損壞率達到20%。若分期攤銷可能會出現實際價值和賬面價值誤差較大;此外,經營期間對損壞的車輛進行補位投放,也可以算作是一次攤銷;由于損耗率較高,維修調度成本居高不下,該部分計入當期損益的支出也可以算作是后期單車的攤銷和對收入的補償。
三、共享單車APP的性質界定以及計量問題
通過互聯網平臺,實現B2C模式下的對外出租是當前單車實現“共享”的必要手段,而作為實現這一目的的網絡平臺——APP系統該如何確認及核算目前并未有文章或規范加以確認,當前將其與共享單車一同確認為“存貨”項目還是單獨確認為“無形資產”也存在爭議,同時對于成本計算中費用化還是資本化問題存在疑問,確認后的攤銷與減值該如何計量也值得探討。
新修訂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第8段指出,無形資產是沒有實物形態的、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第9段單獨列舉了不符合無形資產定義但界定為無形資產的項目大類,其中包括計算機軟件;類比之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解釋公告第32號中將網站成本也界定為無形資產。但是解釋公告第32號同時指出,當主體不能證明未來經濟利益會流入時,專門或主要為廣告和營銷主體自己的產品和服務而開發的網站,不應確認為無形資產,并且為開發網站而發生的所有支出應在其發生時確認為費用,初始確認為費用的無形項目支出,不應在以后確認為無形資產成本的一部分。在某些情況下,當且僅當有證據證明該項目的開發階段比研發階段更進一步,并且將產生很可能的未來經濟利益時,主體可以在內部項目的開發階段確認一項無形資產。
同時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講解》第七章——無形資產一章中也談到,某些無形資產的存在依賴于實物載體,具有依附性,在確定一項既包含無形又包含有形要素的資產是屬于固定資產還是無形資產時,通常以哪個要素更重要作為判斷依據。而作為共享單車大數據監控以及收入確認的APP平臺,與共享單車“周轉材料”(上面已對共享單車本身的性質進行了界定)綁定使用,作為整體的“現金產出單元”,離開了共享單車沒了其存在的必要性。所以為盈利而研發的APP需要與共享單車一同作為存貨入賬,還是作為無形資產單獨入賬仍值得商榷。在研究階段費用化,后期不得轉入無形資產的做法是否能準確地反映其真實賬面價值?在后續計量過程中是否需要攤銷與減值?這些問題仍值得探討。
由于與共享單車共同使用的APP開發有明確的目的,“有完成該無形資產并使用它的意圖”,所以開發成功的可能性比較大,該軟件在內部使用時,可滿足其有用性;且該軟件的使用,相比于之前“有樁”模式的單車租賃更為簡便快捷,當一個簡單易操作的APP平臺為廣大消費者所接受時,可以提高企業知名度,吸引顧客在單車租賃時優先考慮本企業,有利于擴大企業服務規模,增加銷售收入,從而增加企業經濟利益流入,為共享單車帶來超額利潤,所以根據無形資產的確認條件可以將其確認為“無形資產”。
對于該APP在開發過程中發生的支出應予以資本化,計入其成本。美國財務會計準則指出,對于無形資產在研發過程中的研究、開發費都應費用化,但計算機軟件的開發適用例外原則,技術可行性得以確定后可以將其確認為資產;此外,類比制造企業產品制造過程中成本歸集的方法,廢品損失同樣需要計入完工產品的成本中予以攤銷,所以該APP的研究開發費用都需要在其成本中歸集,即使開發失敗的成本也應計入資本化項目。通過“開發成本”予以歸集和披露,同時設置“開發成本減值準備”作為“開發成本”的備抵科目,用于核算在開發過程中發生的減值損失計入當期損益。
在其后續計量過程中,如果是維護平臺正常運行所發生的支出,應當予以費用化;若后續在該平臺開發了新的功能板塊或提高服務質量而帶來超額利潤的支出(比如藍牙便捷開車系統),可以將其計入無形資產的成本,予以資本化。無形資產準則規定,企業應當于取得無形資產時分析判斷其使用壽命,根據經濟利益的預期實現方式予以攤銷,無法預見無形資產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期限的,應當視為使用壽命不確定的無形資產,在持有期間不需要攤銷,在每個會計期間進行減值測試。由于該APP是與當前共享單車的存續期間保持一致的,其為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的期限從目前情況看無法可靠估計,應視為使用壽命不確定的無形資產,而不能簡單地按照某一批共享單車固定資產的折舊期限來進行攤銷;與其他的無形資產不同,當一個品牌隨著時間的推移被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所認可時,其APP平臺價值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隨著其被訪問次數的提高而逐漸增長。這種前提下,按照準則規定一般不需要進行減值測試。但是該APP在使用過程中帶來的“商譽”增值需要在附注中加以披露。
四、提供服務的收入確認時點和金額問題
共享單車的使用屬于典型的分時租賃模式,該模式下的收入主要包括分次按時計算和包天(包月)使用并定額扣費兩種類型。在第一種模式下,根據用戶的使用騎行時間,平臺在收到來自第三方支付機構轉賬后即可確認收入;但是在實務操作中存在以下現象:1元購買原價20元的月卡,需在何時入賬?是按1元入賬還是按20元入賬?若按20元入賬,則19元作攬客成本計入銷售費用還是直接將其作為商業折扣,按1元凈額予以確認?此外對于充100元贈100元的行為,該100元是作為負債處理還是作為收入處理仍值得商榷。
對于1元購買月卡的會計處理,李佳琦[4]認為,不同經營產品種類存在收入時點確認的差異,對于不提供退換或者只提供特殊勞務的服務類商品,買家賣家達成不予退回的協議,所以根據收入的確認原則,買家在簽收商品或者勞務時,該商品或勞務控制權已被轉移,此時就可以確認收入。而中國移動2016年合并財務報表附注中將“向客戶收取的通常不會返還的預付服務費用以及客戶積分獎勵計劃中未兌換部分”作為遞延收入予以披露。所以對于1元月卡的處理,是在用戶購買月卡時直接確認收入還是將其先計入“遞延收益”,待月卡(1個月的使用期)到期時予以確認呢?
對于這1元何時入賬以及如何入賬的問題,可以結合商業折扣的定義“即企業為促進商品銷售而在商品標價上給予的價格扣除”進行核算,不高估企業的收入,遵循謹慎性原則;對于入賬時點的確認問題,可參照中國移動年報中的會計處理計入“遞延收益”,待其完成整個服務期時將其從“遞延收益”轉入“主營業務收入”,或于結算期按完工百分比法確認該部分收入,在滿足收入確認標準的基礎上遵循謹慎性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
而對于實務中存在的充100元贈100元的活動方式,《企業會計準則》及其應用指南中未給出明確的規定。2017年7月5日,財政部修訂發布了《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筆者認為,該業務可以參照收入確認中“授予客戶獎勵積分”的方式加以處理。但對于獎勵積分的處理在實務中也不統一,主要存在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一是將提供勞務或銷售商品的貨款或應收賬款全部確認為當期收入,對授予的獎勵積分不做處理;二是采用與國際會計準則相同的處理方式,將收入與費用進行配比,以“增量成本法”對獎勵積分進行核算,先將當期提供勞務取得的賬款確認為當期收入,而將獎勵積分確認為當期的“銷售費用”和“預計負債”,待實際兌換時沖減負債。2017年注冊會計師考試指導用書中對于授予客戶獎勵積分的處理與修訂后的收入準則保持一致,將銷售或提供勞務取得的貨款或應收款項在本次活動產生的收入與獎勵積分的公允價值之間進行分配,將取得的貨款在扣除獎勵積分公允價值的部分確認為收入、獎勵積分的公允價值確認為“遞延收益”;待獎勵積分兌換或失效時,授予企業將原計入遞延收益的與所兌換積分相關部分確認為收入。
對于這一問題,王峻錢[5]認為,移動公司的充話費送話費活動雖然類似于商場的打折活動,但是本質上兩者是有區別的。其一,打折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增加顧客數量,而充話費贈話費的目的更多地體現在增加顧客的轉換成本,保持現有顧客數量;其二,商場的打折活動具有即時性,而“充贈”業務具有分月返還的延時性。所以不同于一般商業折扣的“充贈”行為,將所贈送的話費金額做營業收入處理,這樣既符合業務實質,同時也體現了稅收的調節作用。
中國移動2016年報在合并財務報表附注中披露的主要會計政策選擇方式下,其收入確認中對于獎勵積分的處理原則是將分配至用戶積分的獎勵金額基于其公允價值而定,在贈予用戶時做遞延收入處理,當用戶兌換或者失效時確認為收入;中國電信2016年度財務報告中并未披露與客戶獎勵積分相關的內容,僅提到了銷售手機和電信服務的促銷套餐采用剩余價值法進行分配。中國聯通2016年度財務報告中則詳細披露了向用戶提供積分獎勵計劃的會計處理政策。對于授予用戶的積分獎勵,在向其提供通信服務的同時,將取得通信服務收入的款項或應收款在本次提供的通信服務收入與積分獎勵的公允價值之間進行分配。將取得的通信服務收入的款項或應收款扣除積分獎勵公允價值的部分確認為收入,積分獎勵的公允價值確認為遞延收益。當滿足積分兌換條件時,將原計入遞延收益的與所兌換積分相關的部分確認為收入,即與注冊會計師考試指導用書的處理方式保持一致。
綜上所述,對于所贈送的100元,可以歸集為企業為銷售本企業商品(服務)而發生的費用,滿足“銷售費用”定義,但是由于所贈送服務部分提供的勞務并不一定在當期發生,直接計入當期的銷售費用損益科目,不滿足當期收入費用的配比原則;此外,該部分雖然不是以獎勵積分的形式出現,但有其公允價值,可以類比具有相似業務的通訊行業的處理辦法,按一定的比例確認當期收入,將贈送部分對應的收入計入“遞延收益”,待該部分服務得以提供或失效時,再將遞延收益部分轉入確認當期的收入。
例1:艾瑞咨詢在《2017年中國共享單車行業研究報告》中統計發現,高頻用戶單次充值金額集中在100元以上,占比達到63.4%,而低頻用戶的單次充值金額集中在100元以內。在該樣本范圍內現假設截至2017年10月底有500人單次充值100元(充值100贈送100),2017年末,該贈與部分有20%被使用,則其當期的會計處理為:
500×100=50 000(元)
50 000/[(100+100)×500]=0.5
當期提供勞務以及遞延收益部分分別應確的收入為為100×500×0.5=25 000(元);遞延部分2017年因贈與部分使用確認的收入:25 000×20%=5 000(元)。所以2017年確認的收入為25 000+5 000=30 000(元)
借:銀行存款 50 000
貸:主營業務收入 25 000
遞延收益 25 000
借:遞延收益 5 000
貸:主營業務收入 5 000
五、結語
隨著資本的大量涌入以及用戶需求的提出,共享單車行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互聯網+”模式的推廣使得該行業的會計核算和會計確認等方面出現了缺口。通過分析得出,對于共享單車本身的確認問題,結合共享單車的特征以及實質,將其確認為“周轉材料”而非傳統模式下的“固定資產”,對于共享單車的后續計量采取簡單適用的一次攤銷法;在共享單車APP的性質界定方面,單獨將其確認為無形資產入賬,該APP在開發過程中發生的支出應全部予以資本化,計入其成本。由于使用壽命不確定,所以無需對其進行攤銷,但該APP在使用過程中帶來的“商譽”增值需要在附注中加以披露;而對于提供服務的收入確認時點問題,筆者更贊同權責發生制下通過“遞延收益”這一會計科目進行過渡,待控制權隨時間完全轉移時再予以確認,同時對于充贈的金額,按照公允價值的比例予以分攤確認,遵循謹慎性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
要想正確地呈現企業的財務狀況,就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會計核算體系,應對新形勢下會計工作內容的變化,規范單車行業的發展,實現新型共享經濟和“互聯網+”模式下精細化、可持續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李漫.共享單車會計核算問題及對策研究[J].商業會計,2017(13):25-26.
[2] 岳會玉,王朋艷,徐一民.共享單車會計核算研究[J].現代經濟信息,2017(3):239.
[3] 唐力力.淺析共享單車經營模式中的會計核算問題[J].中國鄉鎮企業會計,2017(5):98-99.
[4] 李佳琦.電子商務下B2C企業會計收入確認時點研究[D].長春:吉林財經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16.
[5] 王峻錢.移動公司充話費送話費業務核算[J].會計之友,2013(14):11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