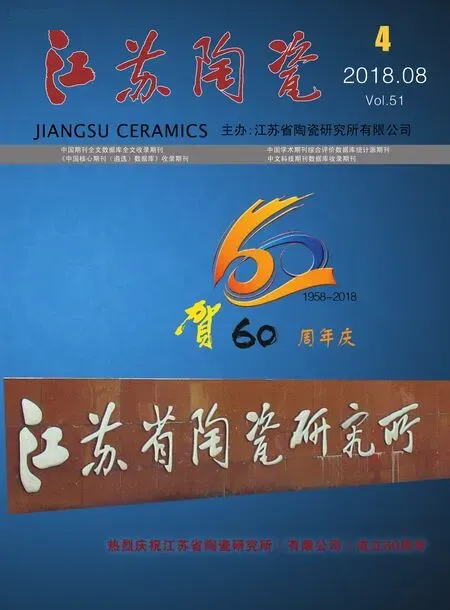刀筆砥礪 詩意棲居
——記青年陶藝家伉儷伯陶、云初

在當今書壇,夫妻皆為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的并不多見,僅憑這一點,伯陶和他的妻子云初就讓人多了幾分艷羨。他們夫妻沉潛陶都近十年,不務虛名、勤奮積累、相從砥礪,共攀藝術高峰,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在友人眼里,伯陶與云初這對神仙俠侶,一個是聊借書魂琢紫玉,清涼境里問陶人;一個是靈魂有香氣的女子,他們攜手過著散淡、快意、幸福的藝術生活。”
劉世濤,1978年出生于新疆,后隨父母回到祖籍滄州,他自幼即在詩書筆墨的熏染中成長,因而他的藝術敏感似乎與生俱來。祖輩的詩禮耕耘,家庭的熏陶,父母的教誨,注定了劉世濤一生的翰墨情緣。他的父親寫得一手好字,遠近聞名。但是父親對他的教育并不嚴厲。回憶起來,他覺得自己對藝術的熱愛是自然而然的,這種熱愛是從祖輩的血脈里流傳下來的。“對于傳統(tǒng)文化,不單單是熱愛,其實多少有一點的敬畏在里面。”他很小就看著父親在春節(jié)的時候為別人寫春聯(lián),在同齡人中他認字是最多的。從小就向往古人生活方式的他,心中也慢慢生長著一種古意。“之乎者也”在一瞬間也擁有了神奇的力量,幻化成無數(shù)美妙的意象,吸引著年少的劉世濤。大年初一,大家一起挨家挨戶拜年的時候,小伙伴們兜里鼓鼓的裝滿了花生糖果,劉世濤的腦海里卻牢記了十幾副春聯(lián)。走在路上,只要是有字的紙,他無一例外的都會撿起來看一眼。劉世濤先是在父親的指導下,研習書法。后又得到李德瑞、張之、韓煥峰、李大中等諸位先生指導,書畫篆刻技藝逐漸步入正軌,楷隸篆行,各體精熟。后來,又拜在金石傳拓名家馬國慶先生門下,并得到了徐湖平、何水法先生的教誨指點。名師的點撥加上自己的勤奮努力,劉世濤的“諸藝融通”之路慢慢鋪展開來。
2008年,劉世濤來到宜興,結緣紫砂,他取號“伯陶”,在漸漸適應了這里舒緩的生活節(jié)奏后,開始樂在其中了。在宜興當?shù)兀湛套髌肥亲仙皦貥I(yè)衍生出的副產(chǎn)品,大多是匠人之作,伯陶憑借專業(yè)的書畫篆刻功底,陶刻技藝很快得到業(yè)內認可,被譽為“詩、書、畫、印、紫砂、傳拓”六藝合一的青年陶刻家。他的陶刻作品章法、構圖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元素,充滿文人氣息。
“多少夢,文墨作生涯。聊借丹砂成豹變,閑持玄鐵刻風華,愿教筆生花。”一闕《憶江南》,是他在摶砂造器中成長的自畫像,從此丁蜀鎮(zhèn)成了他的第二故鄉(xiāng),南北兩地盤桓,苦心經(jīng)營這一方心靈的藝術空間。每每有書朋畫友、文人雅士聚集于此,有茶為伴,三五成趣,“壺上丹青同赴老,軒中魚鳥最通禪”。
2011年他偶得齋號“抱蜀軒”,這一切源于“此山似蜀”,出于對東坡居士的仰慕與崇敬,也是劉世濤心中古意匯聚的一個節(jié)點。東坡居士“買田陽羨吾將老,從來只為溪山好”,追慕先賢、承續(xù)文人紫砂余緒的信念在伯陶和云初的心中漸漸豐盈起來。他們注冊了“彧元”商標,創(chuàng)建了“彧元窯”品牌,開啟了文人紫砂的傳承之路。
伯陶認為,所謂“文人紫砂”不能只是炒作概念。不是請書畫家寫寫畫畫刻出來就是文人壺了。何為文人?“文人,我給他的定義是以文化知識安身立命、以文化理想為終極目標的人可以稱為文人”。他認為自己可以算是一個文人。他對文人紫砂的理解是這樣的:制壺的人首先是個文人或者要具備文人的素養(yǎng)和文人情懷,最起碼要能懂得文人情懷;然后刻壺的人也要首先是個文人或者要具備文人素養(yǎng)、懂得文人情懷。在這個基礎上,用心創(chuàng)作的作品,才有可能在文人紫砂中有一席之地。
在紫砂壺的歷史上,陳曼生和他的曼生壺可以說是一座高峰,在伯陶的心里,是要堅定地承續(xù)陳曼生文人壺的余緒的。這些年來,他原創(chuàng)了300多則紫砂壺銘,還有不少的紫砂硯銘及其它紫砂器物的銘文,他對紫砂和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和努力于此可見一斑。
祖籍湖北十堰的云初黃艷平,同樣出生在書香門第,祖上世代為官、從文。從小耳濡目染的皆是中國古典傳統(tǒng)文化。他們夫妻二人同為張之先生、馬國慶先生的弟子。是文學之緣,是藝術之緣讓云初和伯陶走到了一起。“時光剛好,我們走進彼此的世界,今生最浪漫的理由:活成一段詩畫”。在這個文化古鎮(zhèn),云初找到了理想中生活的樣子,“在丁蜀山頭,有間小小的房子,養(yǎng)兩只狗,寫寫畫畫,種很多很多的花,看每一天的日出日落。玩紫砂,做做壺,刻刻畫,有書看,有茶喝,有人作伴”。云初在藝術上是很有靈氣的,她所制《寒香壺》還在全手工比賽上獲過獎。制壺之余,更多的是做傳拓和陶刻。再有就是蒔花弄草,“食金石力、養(yǎng)草木心”,云初種植菖蒲的本領在友朋之間還是頗有名氣的。從小養(yǎng)成的愛讀書的習慣,讓云初的文字也常常有引人入勝的魅力。看到云初的文字,全國各地的朋友都會有馬上就來到宜興的沖動:“江南的天,柔軟的像一片海。我在這樣的日子里,接雨研墨,烹雪煮茶。”這大概就是幸福的樣子了。
2012年的秋葉已泛黃,伯陶和妻子云初走進宜興大覺寺,他靜靜坐在正殿前方的石階上,內心澄明,瞬間找到了藝術的另一片棲息地,不自覺地萌生出刻經(jīng)的念頭。從設計坯樣、布局位置、虔心刻制,歷時一年制作而成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缽盂,將書法、篆刻、陶刻藝術融于一爐。第二年的春節(jié),他沒有回家陪父母過年,一人關起門專心刻經(jīng),江南的冬,冷得徹骨,但他的內心充滿溫暖。缽盂上刻有5 400余字,有篆有楷,11方印章中有佛造像印,有文字印,各具匠心,這件原創(chuàng)作品獲得了2015年米蘭世博會金獎。
2016年8月,伯陶開始了和何水法老師的合作。何老師畫了二十幅G20國花的扇面,伯陶把他的國花扇面作品刻在二十把紫砂壺上。何老師的畫風格獨特,色彩艷麗豐富,在紫砂壺上純用刻刀展現(xiàn)難度非常大。但最終伯陶還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把它呈現(xiàn)出來,做了二十張拓片,又創(chuàng)作了二十首國花詩贊。時間緊任務重,這批作品在布展的那天凌晨才全部完成。G20期間在浙江美術館展出了一個月,迎接了眾多國內外觀眾,反響強烈。多種技藝的整體展示讓伯陶很有成就感,也使得他贏得了更多的肯定和贊譽。
從2011年開始,伯陶開始在丁蜀成校講課,教授書法、篆刻及陶瓷裝飾課程。數(shù)年來也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追摹傳統(tǒng)、踐行自己的藝術理念,銳意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陶刻作品本身所蘊涵的藝術價值和藝術魅力是毋庸置疑的,2016年底,伯陶創(chuàng)建了《中國陶刻網(wǎng)》并擔任主編,他希望能夠給紫砂陶刻提供一個專門的平臺,提升人們對于陶刻的認知和重視、熱愛。獨行快,眾行遠!我們的陶刻從業(yè)者也應該有更大的擔當,為繁榮陶刻事業(yè)做出自己的貢獻。
很多藝術門類雖然載體不同,但其中蘊涵的“道”是相通的。伯陶和云初的愛好,將他們的藝術空間分割成多個區(qū)域,而這并沒有分散他們的注意力,摶砂玩泥是書法之余的休閑,畫畫又是制壺造器之余的調劑。同樣,刻印、傳拓、作詩、陶刻都是互為補益、互相滋養(yǎng)的。學識、修養(yǎng)、功力、閱歷、審美取向使他們的創(chuàng)作日漸穩(wěn)健起來。
紫砂承載了詩書畫印的文化價值,除了陶刻茶壺、花盆、掛盤、筆筒雜件等,作為傳拓技藝省級非遺傳承人,劉世濤和妻子云初還做了大量的拓片作品。“彧元堂傳拓古今紫砂器物款識裝飾”系列工程也已成品近200件。
伯陶是非常勤奮的,這些年,他所刻的印章將近3 000方,鈐蓋在了一卷長25米的長卷上。而且,他堅持了每天留一件自己的書法作品。他希望自己的勤奮和執(zhí)著、努力和堅持能夠給學生們以榜樣。從事陶刻事業(yè),除了要在書法、繪畫包括篆刻上打牢夯實基礎,還要在用刀方面形成自己獨有的表達方式。更重要的,是不斷提升自己的文化素養(yǎng)和審美境界。要根據(jù)自己的喜好做一門學問,慢慢熏陶,一點一滴地涵養(yǎng)自己的心性。所有的藝術門類,要想達到高度,最終還是要靠學養(yǎng)的積累和文化的支撐。
這些年來,伯陶和云初沉浸在自己的藝術世界里,默默地做著堅實的積累。他們志在融通諸藝,以不斷接近于“道”。在他們看來,藝術是一生的事業(yè),是一生的修為。“一切努力所得的回報都是因為厚積薄發(fā)而水到渠成”,他們的作品多次入展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主辦的展覽并獲獎。兩人雙雙榮獲中國收藏家協(xié)會“2014年最具收藏價值陶藝家”稱號。他們的紫砂作品也深受壺友、藏家喜愛并入藏多家博物館,出版了多部作品集。伯陶在2010年隨中國書協(xié)刻字藝術代表團出訪日本,2011年又被中國書協(xié)授予“中國現(xiàn)代刻字藝術優(yōu)秀工作者”稱號。
伯陶認為:第一,好的陶刻作品要通過拓片來檢驗。拓片能把作品的兩個面甚至三、五個面的刻繪匯集到一個平面當中,能夠把一件陶刻作品的章法布局、刀法、格調統(tǒng)一觀照。不管在拓片上是兩個面還是三五個面,它們應該都是統(tǒng)一的。如果陶刻作品這幾個面之間沒有呼應也沒有變化,達不到高度統(tǒng)一,這件作品是不成功的。第二:真正的陶刻高手,不是僅僅限于自書自畫自刻,而是要能把別的書畫家的作品刻好。這個刻好是首先不能有陶刻者自己的風格影子,否則就“刻走形了”,這是不行的。陶刻應該是屬于二度或者三度創(chuàng)作,要具備這種能力:在尊重原作的基礎上能夠把書畫家不太滿意或是不太好的地方進行“微調”,達到最佳效果。
對于陶刻,伯陶有著自己深刻的思考。他經(jīng)常跟學生們說要讓自己的“手段”多一些:“比如創(chuàng)作一件作品需要五個手段,而你具備了八個手段,在創(chuàng)作時自然能達到一種‘松’的狀態(tài),因為你不怕出問題,出了問題你還有解決問題的辦法。而這種‘松’的狀態(tài)足以讓你的作品超越平常!”他游刃有余地將古代碑刻、篆刻、木刻及現(xiàn)代刻字的技法融入了陶刻當中。還提出了“處處見刀、處處不見刀”的概念,所有的技法都是為作品服務的,最終還要把技法“藏”起來,而不是流于“炫技”這種表象的層面。
今年8月初,一場“紫韻心造”——伯陶、云初紫砂傳拓作品展在宜興市美術館開幕。此次展覽共展出他們夫妻二人作品120余件,涵蓋了紫砂制壺、陶刻、書畫篆刻及傳拓作品,為宜興奉上了一場藝術盛宴。這次展覽,使他們的作品贏得了普遍的贊譽,很多業(yè)界權威人士表示,這個展覽代表了宜興陶刻非常高的水平。伯陶、云初在作品中踐行著自己“不為材質、形式、技法所囿”、“努力深入傳統(tǒng)、汲古出新”的藝術理念。
“詩茶淡淡遠喧塵”,伯陶、云初以詩書為友,與紫砂相伴。幾年來,丁蜀鎮(zhèn)的一方水土滋養(yǎng)著這對異鄉(xiāng)人,他們雖心隱桃源,卻并不沉寂,讀書臨帖、刻壺治印、論藝談文,會群妙于一心。摒除浮氣、俗氣、匠氣,靜靜棲居,體會四時之變化,詩、書、壺、茶多味人生漸漸氤氳成一幅美麗的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