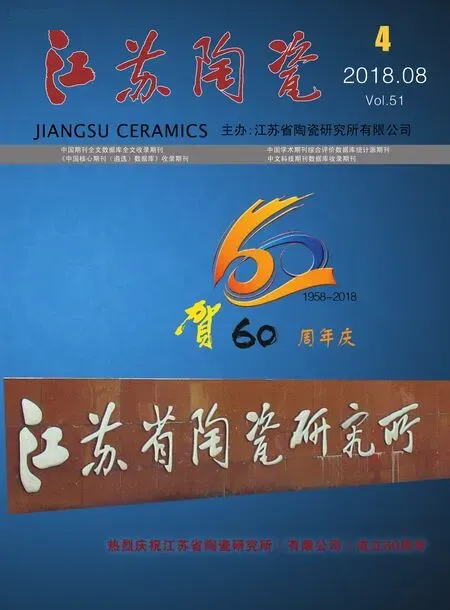“三人行,必有我師”組壺創作談
查元康
(宜興 214221)
“三人行,必有我師”,語出《論語·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意思就是說:“與三人或三人以上的人交往,其中必然有學有所長的人,與這樣的人交往,就能學到人家的長處。”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傳承中,先祖們的聰明、智慧逐步得到進一步發展。在歷史的長河中,儒、釋、道三家,最能代表中華文化的精華。人民日報社社長楊振武在《從中華文化中汲取力量》一文中論述到:“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為了使中華文化進一步的發揚廣大,我設計創作了“三人行,必有我師”組壺(見圖 1)。

圖1 三人行,必有我師組壺
“三人行,必有我師”組壺由三壺、三杯、三碟組成。聚則可放置成寶塔形的組裝式樣,散則可單用其一壺泡茶,這一設計增添了“組壺”的趣味性和可賞、可玩性。壺和杯、碟都設計成三角形,“三”這個字在中文中有著廣泛的含義。《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意思為“道”是獨一無二的,它可以化生出陰陽(一生二),有了陰陽就有了千變萬化(二生三),衍變出天下萬物。在先秦時,“三”是多數的意思,“三人行,必有我師”組壺的三角形造型就蘊含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含義。
“三人行,必有我師”組壺下層的兩壺設計成平蓋,蓋的中間部分為凹形,邊緣部分有一凸線,可用一手指伸下去提拿壺蓋,使三壺可以組裝,上層的壺為嵌蓋,三角形鈕,與壺體的造型相協調。“三人行,必有我師”組壺的泥料為精選的黃龍山烏泥。潘春芳在 《宜興紫砂》一書中談到烏泥:“紫砂歷史上的烏泥,實際上包括兩種不同的品種,一種是含錳、鐵量較高的真正的烏泥,燒成后成烏黑色。另一種是采用特殊的裝燒方法產生黑色的,稱為‘捂灰’”。“三人行,必有我師”組壺采用的泥料屬于前者,黃龍山烏泥燒成后顯得黑而潤澤,看上去特別莊重、渾厚。
“三人行,必有我師”組壺在設計及制作上處處體現了方圓結合、方圓和諧的設計理念。壺、杯、碟都呈三角形,每一個三角形向外伸展的都是圓的弧線,這是方中寓圓的優美造型。我在三壺的組合上,在它們之間整體的連貫與協調上下了功夫。楊永善在《陶瓷造型藝術》一書中論述到:“任何一種藝術創作或設計都強調整體。把各種構成因素有機地組合在一起,使其發生聯系和統調,無論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都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整體效應,使人感到流暢、舒展、渾然一體,沒有拼湊感,不會相互抵消,表現著和諧的美。”“三人行,必有我師”組壺從大壺到中壺,到小壺,其體積按比例遞減,上壺的三角形壺鈕的造型與整體相呼應,組合后成寶塔形,它們之間是有機的組合,使人聯想到了中國古建筑的造型美。
從每一個單壺的設計上來說,每一個三角體,它的弧線向外伸展的幅度要適中,過則肥,減則瘦,在畫圖紙時進行反復的比較,從最后選定的尺度及燒成后的實體來看,其選中的比例是適中的,是賞心悅目的。壺嘴的設計,因口面是平面的,故嘴的上部也選擇了平面造型,下部呈三棱形,按二彎嘴的造型向下略有伸展,以保證出水的爽利。壺把設計成古文字中的“人”字形,中國的象形文字形簡而寓意深刻,“三人行,必有我師”組壺在組裝后,三個壺把的造型就如自行車比賽中的一組運動員的造型,其形態生動而傳神。而放在小碟中的杯把之形,又如賽艇中的運動員形象,可謂是物移而景變,生動有趣,顯示出中國古文字的文化魅力。
“三人行,必有我師”組壺的“三人行”代表了中國古代文化的三家代表儒、釋、道,為了進一步表達作者的設計理念,在每一壺的下部進行了陶刻裝飾。選擇下部是為了體現壺體上中部烏泥燒成后的肌理之美。陶刻采用的是章草書體,章草的出現源于漢代,它是由隸書演變而來,從快捷這一角度來考慮,當時的文人大多使用章草文字往來、書寫奏章,章草逐步形成一種獨立的書體,它局部保留了隸書的一些特點,而加快了書寫速度,與現代的草書又有明顯的區別而顯得古味盎然。下壺的陶刻表達的是道家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厚德載物”,“上善若水”,“清靜為天下正”,“處無為之事,行無言之道”,“寵辱不驚,去留無意”。此乃道家思想之精髓也。中壺的陶刻表達的是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之成者天之道也”,“己所不欲,不施于人”,“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上壺陶刻表達的是釋家思想:“五倫五常”,“四經八德”,“三綱八目”,“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
以上三家的精粹語錄是中華文化的精華,有著深刻的哲理,它們對人們的行為處世有深刻的指導意義,對社會的和諧也有重大的促進作用。“三人行,必有我師”組壺的設計創作,在努力宣揚中華文化上盡到了作者應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