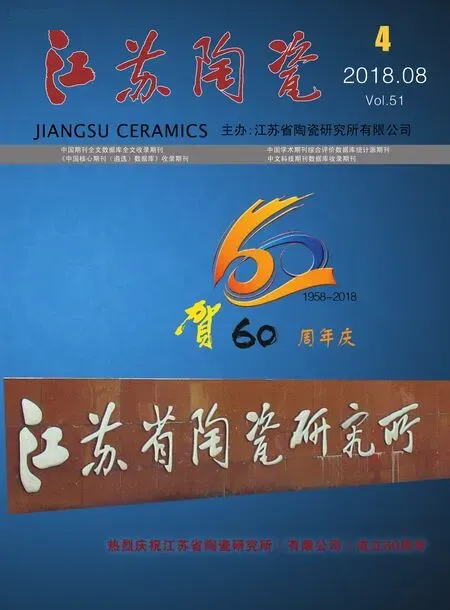魚游同為樂 紫甌聚風華
——淺述紫砂壺“魚樂”的文化屬性
吳幼波
(宜興 214221)
紫砂壺的文化屬性歷來便備受壺人和文人的廣泛關注,自古以來,無數紫砂藝人進行了豐富的嘗試。明代制壺巨匠時大彬應文人需求,改進了壺型的體態特征,從而使紫砂壺具有偏小的容量特性;清代文人陳曼生與制壺名人楊彭年、楊鳳年兄妹共同合作的一系列“曼生壺”,更是將紫砂壺的文化屬性推向了巔峰,對后世壺藝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時至今日,文化屬性已經成為壺藝創作的重要目標之一,形神兼備更是成為了人們衡量一把壺綜合價值的重要標準。紫砂壺“魚樂”(見圖1)就是在傳統紫砂壺形態的基礎上,進一步汲取中華文化深厚的底蘊和內涵元素,通過富于創意的造型結構、裝飾點綴,呼應主旨,表達其獨特的人文個性,從而實現人與壺的共鳴。現以此壺為例,談一談其具體的藝術形象,以期共勉。

圖1 魚樂壺
“魚樂壺”整體造型簡約而不簡單,壺身上下略壓扁,形成一種橫向張力,直流、飛把,結構平衡,圓平蓋壓于壺口,底部為矮圈足,營造出視覺上的安定感。整體而言,點、線、面三者在作品中得以綜合運用,且虛實相濟,與此同時,壺肩一圈則充分運用線條元素,裝飾出起起伏伏的波浪形態,明暗交接,仿佛隨風而動的波紋,具有動態感,增強了壺的藝術效果。不僅如此,在波浪處,此壺獨辟蹊徑地采用了鋪砂裝飾技法。鋪砂工藝是指紫砂坯體在制作過程中,將處理好的不同色澤的缸砂或紫砂泥礦砂粒 (一般指直徑1mm左右的碎塊熟砂)采用鋪、點、撒等方法,施于尚有一定濕度的坯體表面,再借助工具將砂粒嵌入坯體表層,經燒成后,摻入的砂粒與坯體會形成不同的顏色和肌理效果,增強作品的裝飾美感,此處均勻地鋪飾點點金砂,給人以“珠粒隱現,光閃奪目”之美,巧妙形成“大浪淘砂”的圖案,對應了“魚樂”這一主題需要。這把壺在主體造型上,通過線條的運用加上鋪砂形成的色調搭配效果,構成了相對統一的視覺審美效果。
壺鈕的造型設計是“魚樂壺”的畫龍點睛之筆,以一條抽象的魚構成一只半圈鈕,鈕中間又扣一圓環,圓環可活動,十分玲瓏可愛。整體刻畫了一條魚躍出水面又躍入水中的場景,頗具創意,平蓋恰似水面,渾然天成,惟妙惟肖,達到靜中寓動的效果,以線條雕刻出魚的表情神態、魚鱗細節等,突出了畫面感和趣味感,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屬性。
“魚樂壺”在造型和裝飾上實現了整體和局部的有機結合、協調統一,滿足了紫砂壺的實用功能,又立意于壺的文化與精神價值。自古以來,中國人對魚充滿了一種圖騰崇拜,類似“魚”字口彩有很多,例如:如魚得水、金玉(魚)同賀、年年有余(魚),富于吉祥美好的祝愿。“魚樂壺”在表達“魚樂”這一哲學內涵時,也同時賦予了作品更豐富的人文意蘊,以文化品位衡量其創作目標,從而更進一步實現其藝術、文化價值的輸出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超越物象的實際內涵,而達到一種更高的精神格局。
“魚樂”一詞出于《莊子·秋水》“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比喻像魚一樣逍遙游樂,引申出一種超脫自在的生活狀態。自古以來,“魚樂”二字一直包含著一種樸素的東方哲學意味,中國人更于其中體味高深而理想的思想境界,并進一步將其具象化、生動化,而藝術創作就是對其進行詮釋的實際演繹。
“魚樂壺”便是從《莊子》典籍中獲取的創作靈感。紫砂壺具備與文化結緣的優越性,但作為一把合格的紫砂壺,除了展示其藝術價值和實用功能外,必定承載著文化脈絡,并以此拓展其壺藝形象和藝術生命。然而紫砂壺不同于瓷器,其表面無釉,往往需通過外在造型的變化、裝飾設計的鋪墊來延伸其有限的美感空間,從而提升藝術境界、拓寬藝術范疇,帶給人美好的藝術享受。“魚樂壺”一方面以富于線形變化的流暢壺型來賦予作品動態的藝術個性,另一方面則通過魚形塑雕裝飾,在寓具象于抽象中,刻畫其主旨內涵,同時適當地融入鋪砂裝飾,增強整件作品的藝術魅力,拓展其所承載的藝術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