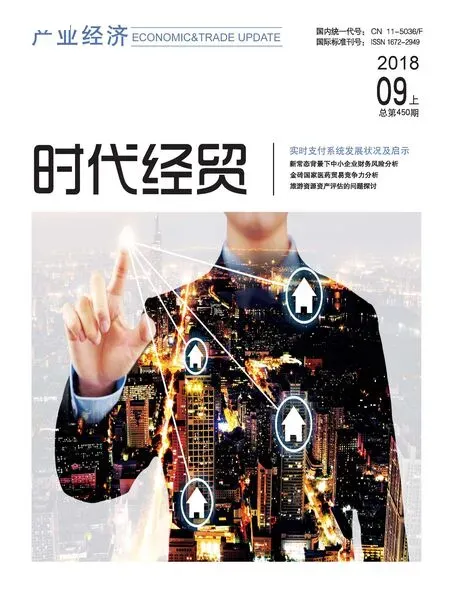江蘇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研究
——基于經濟增長動力演變的視角
曹冬艷 王 榮,2
一、引言
從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許多國家通過發揮資源優勢,完成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但是在向高收入國家攀升的過程中卻出現了重重困難。甚至有一些國家曾經一度進入到高收入階段,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又退化到中等收入階段。在總結相關國家經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世界銀行指出一些從低收入階段上升到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由于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鎖定,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停滯徘徊期,最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不能自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擺在轉型國家面前的戰略難題。
江蘇省處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具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但是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基本還屬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層次。2012年以來,受宏觀經濟大背景影響,江蘇省經濟增長呈現明顯放緩態勢。2012年江蘇省GDP增速為10.1%,比2011年回落0.9個百分點。2013年至2017年期間,江蘇省GDP增速持續回落。江蘇省十三五規劃指出,江蘇省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仍然存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創新能力還不夠強,新增長點支撐作用不足,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仍然存在。經濟增長乏力將延緩江蘇省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攀升的進程,帶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隱患。所以,必須尋找切實可行的方法,尋求支撐經濟發展的有效動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Barry Eichengreen et al.(2012)指出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制造業就業人數所占份額達到高點,服務業生產率提高有限,資本存量導致的折舊增多以及經濟接近技術前沿,以上任一情況出現,都將引起增長率下滑。Vandenberg &Zhuang(2011) 指出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可能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Jankowska et al.(2012)認為產業結構不能適應過度人口城市化是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楊淑華、朱彥振(2013)指出勞動力及生產要素價格上升,消費拉動不足,技術進步還沒有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這些問題使中國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和挑戰。周文、趙方(2013)指出一個滿足庫茨涅茲假說的國家要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通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政策措施來促進經濟增長。張德榮(2013)認為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很可能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階段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在中等收入階段很可能會失效。余永澤(2015)的研究表明,中國屬于典型的投資主導型經濟,資本投入是中國經濟增長持續穩定的最主要來源,而TFP貢獻率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
縱觀現有的研究成果,國內外眾多學者從“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形成原因、跨越路徑等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是規范研究偏多,而基于實證研究尋找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路徑相對偏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解決經濟持續增長的問題,因此深入研究江蘇省經濟增長的動力,明確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增長動力的變化,將有助于實現江蘇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二、模型構建
基于經濟增長動力演變的視角研究江蘇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需要深入研究江蘇省經濟增長的動力,明確各種動力對江蘇省經濟增長的影響。美國數學家柯布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在研究投入和產出的關系時,認為產出主要是資本和勞動要素貢獻的結果,將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簡化成以下C-D生產函數形式:
其中,Y為產出水平,A為綜合技術水平,K 為資本投入,L為勞動投入,α為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β為勞動投入的產出彈性,0<α<1, 0<β<1。假設存在“希克斯中性”技術進步,即經濟增長的規模報酬不變,則α+β=1。
以C-D生產函數為基礎構建如下模型
進而將β= 1- α代入式(2),對方程兩邊取對數,可得:

三、指標選取和數據來源
產出指標采用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來衡量,并根據地區生產總值定基指數調整為實際地區生產總值,數據來源于1990-2016年江蘇省統計年鑒。資本投入指標采用固定資本存量來衡量,但目前統計年鑒中沒有提供相應的固定資本存量數據,本文采用永續盤存法,根據公式Kt=Kt-1(1-δ)+It,Kt為t年的固定資本存量,It為t年的新增投資,δ為折舊率。本文借鑒單豪杰(2008)的研究成果,折舊率設為10.96%,對江蘇省固定資本存量重新估算,相關數據來源于1990-2016年江蘇省統計年鑒。勞動投入采用當年就業人數衡量,數據來源于1990-2016年江蘇省統計年鑒。
四、實證過程
(一)數據平穩性檢驗
為了避免實證過程中出現“偽回歸”,首先對模型涉及的時間序列變量Ln(Y/L)和Ln(K/L)進行單位根建議,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1 變量平穩性檢驗結果
變量平穩性檢驗結果顯示,變量Ln(Y/L)的ADF值為-4.407865,小于1%~10%顯著性水平下的ADF臨界值,因此拒絕原假設,認為時間序列變量Ln(Y/L)平穩。同樣,變量Ln(K/L)的ADF值為-6.823363,小于1%~10%顯著性水平下的ADF臨界值,因此拒絕原假設,認為時間序列變量Ln(K/L)平穩。
(二)序列相關檢驗
對(3)式進行OLS回歸,得回歸方程:

對模型的隨機誤差項進行一階序列相關LM檢驗,(3)式隨機誤差項一階序列相關LM檢驗的輔助回歸方程為:

輔助方程的拉格朗日乘子LM=(27-1)0.6089=15.8314,大于臨界值3.8425,所以拒絕原假設,因此可以判定(3)式隨機誤差項存在一階序列相關。
(三)參數估計
運用廣義差分法,采用科克倫-奧克特迭代法估算自回歸系數。最終得出回歸方程為:

回歸方程中各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經過調整的可決系數為0.9998,擬合效果良好,DW值為1.7671,可以判定不存在一階自相關。
由此可以估算生產函數的形式為:

(四)全要素生產率估算
美國經濟學家索洛于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概念。全要素生產率是指各生產要素(如資本和勞動等) 投入之外的技術進步等導致的產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貢獻后所得到的殘差,又稱索洛余值。對生產函數求導,經過變換可得:

ΔY/Y代表經濟增長率,ΔA/A代表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ΔK/K代表資本增長率,ΔL/L代表勞動增長率。將具體數據代入計算可得下表數據。

表2 1991-2016年江蘇省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五)研究結論
從相關數據可以看出,整體而言,自1991-2016年期間,資本要素的投入為江蘇省經濟增長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而勞動要素投入的貢獻相對較弱,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偏低。
從不同時間段來看,在1991-2016年期間,江蘇省經濟發展經歷了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2008年金融危機等重大事件。借助于以上重要時間節點,將1991-2016年的26年時間劃分為如下三個階段:
(1)1991-2000年,這一期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極大調動了市場經濟主體的積極性,江蘇省要素投入達到階段最高水平,全要素生產率也達到了相對較高水平。這一階段驅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于改革紅利。
(2)2001-2008年,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快了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進程。一方面江蘇省積極把握入世機遇出口規模持續增長;另一方面大量外資企業來華投資,帶來了大量資本,也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對外開放度提高加強了對外技術交流與合作,拓展了技術引進和創新的空間,提高了生產效率。這一階段資本、勞動以及全要素生產率都為江蘇省經濟增長做出了顯著貢獻,驅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全球化紅利。
(3)2009-2016 年,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一方面,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外需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江蘇省出口面臨一定的阻力,導致需求不足,投資下降。另一方面,江蘇省人口紅利逐步減弱,老齡化比例位于全國各省之首,勞動力成本優勢減弱,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下降。此外,與發達國家相比,現階段江蘇省科技創新成果轉化能力還不足,科技創新成果還沒有完全轉化成生產力;人才供給結構性矛盾突出,科技創新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從測算結果來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研究結果顯示,當前階段在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有限的情況下,全要素生產率并沒有成長為推動江蘇省經濟增長的中堅力量。所以在經濟增長的新舊動能轉換時期,迫切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聚力創新,發揮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實現地區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五、對策建議
從人均GDP來看,江蘇省已經達到中上等收入水平,經濟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在江蘇省經濟發展中也面臨著地區發展不平衡、人口紅利減弱、資源環境約束加強等問題。
隨著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下降,而全要素生產率尚未充分發揮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江蘇省經濟增長將存在一定的壓力,有可能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擾。因此,未雨綢繆,進一步深化改革,聚力創新,以全要素生產率為重要突破口,充分發揮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將是江蘇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路徑。具體對策如下:
第一,注重人才培養,優化人力資本結構。受人口老齡化影響,江蘇省人口紅利正不斷減弱,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日益有限。在勞動投入日益受限的情況下,提高勞動者素質,優化人力資本結構,將是應對人口紅利減弱所帶來負面影響的重要途徑。江蘇省作為教育大省,有著豐富的教育資源。一方面,要加大教育經費投入,進一步完善教育條件,提升高等教育入學率,延長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勞動者素質,滿足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對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大高素質人才培養力度,各類高校應該與企業密切聯系,了解各行業最緊缺的人才需求情況,產學結合,致力于培養相關行業的頂尖人才。
第二,加大研發投入,提高科技創新能力。近年來,江蘇省研究與發展經費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不斷提高,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江蘇省科技創新能力仍然有待提高。江蘇省一方面需要繼續加大在R &D 活動上投入的力度,另一方面需要加強對R&D經費支出的審核和審計,完善評估機制,進一步提升R&D 活動效率,同時注重對外學習與交流,全面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此外,還應理順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渠道,促進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成生產力。
第三,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可以使生產要素從生產率低的部門向生產率高的部門移動,從而提高全社會生產率,推進經濟穩步增長。在農業領域,江蘇省需要積極發展生態循環農業,同時注重提高農產品品質,促進農業向高端化、安全化、特色化發展。在工業領域,江蘇省應積極建立以智能制造為主導的現代化產業,推進各種先進技術與第二產業融合。在服務業領域,應該大力發展高端服務業,提高傳統服務業的現代化水平。江蘇省內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使大量的資金和人才向蘇南地區集中,制約了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江蘇省應該創造有利條件,引導資源向蘇中、蘇北合理流動,發展當地特色產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