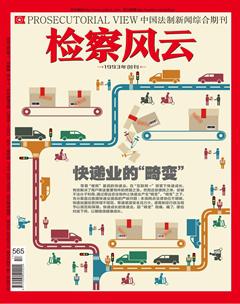葉淺予的民族美學
徐悅

自1999年,中央美術學院接受葉淺予家屬捐贈的6000余件作品以來,學院美術館即有計劃、分階段、分重點地對這批涉及速寫、草圖、畫稿、創作等涵蓋葉淺予不同藝術時期的藏品,除了開展一系列長期的基礎性整理,也逐步完成了信息采集和數據化工作。由此,除兄弟館協商外借葉淺予個別藏品參與全國重大美術展覽之外,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也依托這批館藏,或聚焦葉淺予直面生活的速寫藝術,或側重葉淺予不同題材的繪畫創作,先后舉辦葉淺予藏品個展。
敦煌寶庫
上世紀50年代,因建立中國畫系培養后備人才之需,葉淺予及其所率幾名業務尖子生赴敦煌臨摹學習的藏品,以呈現葉淺予對民族藝術瑰寶的目識心記。據史料記錄: 1955年,美協上海分會曾在陜西南路文化廣場為之主辦“敦煌壁畫臨本展覽會”;1957年,北京朝華美術出版社為之出版《敦煌壁畫臨本選集》,皆收錄本單元陳列的這批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藏品。
1954年,為了學習敦煌藝術遺產,中央美術學院指派彩墨畫系主任葉淺予作為“敦煌文物考察隊”之領隊,率幾名業務尖子生和金浪、鄧白等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師生一道,赴敦煌莫高窟臨摹壁畫。他們在莫高窟進行了三個月的考察和臨摹。從臨摹中體會民族繪畫的優點和特點,學習古代藝術家的創作經驗,借以提高我們對民族繪畫傳統的認識。葉淺予先生認為臨本盡可能做到忠實于壁畫的現狀,個別臨本由于原畫過分殘破,必須有所加工才能顯示原畫的精神,我們會適當加工。至于臨摹的對象,是根據個人的認識和愛好,自行選擇的。
敦煌壁畫的內容,包含面極為廣泛。如經變故事中的打糧、行舟、打獵等場面,統治者的顯赫排場,以及音樂百戲等文化生活,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的各方面,具有豐富的現實性。佛本生傳和經變故事都來自印度,但壁畫中的故事形象,卻翻譯成了中國人。“未生怨”連環畫的情節是原來的,人物和背景卻是唐代的現實,這些形象是從印度的形制中滲入了自己的想象,逐漸成為自己的宗教形象,使他們更加符合人民性。
民族贊歌
《民族大團結》(中國美術館藏)是葉淺予1951創作的第一張反映新中國政治主題的中國畫代表作。畫面以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與各民族代表歡聚一堂的祝酒場面,謳歌“全國各民族大團結萬歲”。我們可以從葉先生的草圖、畫稿來看他創作的完整過程。葉淺予創作的《民族大團結》,意在通過這一過程,揭示葉淺予為譜寫新中國民族團結主旋律在視覺美學建構上篳路藍縷的藝術實踐。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藏有該作的另外兩個版本,以及多幅構思畫稿與人物形象速寫,比較完整地呈現了葉淺予在當時構思和表達民族團結主題時的創作思考與調整過程,從中可以明顯感受到畫家積極調動藝術想象,數易其稿,認真完成創作的態度和熱情。
誠如葉淺予在多年后所言,面對分配的創作任務,“事先有個思想,想用具體形象表達中國革命的勝利,構思結果”,“的確下了很大功夫,表達了我的政治熱情”,為同類政治主題的形象化表達和運用中國畫技法表現方面,收獲了篳路藍縷的創作經驗和圖式經驗。因此1963年張仃為《葉淺予作品選集》撰寫前言時說:“葉淺予的《民族大團結》對于國畫的推陳出新,有它的重要意義,而且也是作者在創作上的一個里程碑。”
其實推陳出新也罷,里程碑也罷,均源于葉淺予在當時富有挑戰性地從解讀民族革命和國家政治訴求入手以及從創造人物形象出發,在中國畫藝術創作上對民族主題與題材的率先破題和立意。
曼妙舞步
葉淺予第一個畫舞高潮出現在1961至1964年,之后他以擅畫民族舞蹈而享譽畫壇。“淺予畫舞”并非出于他早年的藝術立志或自我規劃,而是由他的藝術人生道路決定的,這自然也就有了他對于舞蹈人物形象生產的方法和特點。
從生活源泉上講,葉淺予自上世紀40年代后有在西南采風和印度訪問的速寫和創作經驗,不過正如他多次談到的,他“愛看戲看舞,戲和舞成了我發掘美的典型的生活寶庫”,“我把舞蹈家所創造的形象,通過畫筆記錄下來,進行再創造,成了人們另一種美的享受” 。這里,如果我們將舞蹈家創造的形象看成是一連串有機運動的舞步結果,那么葉淺予在二十世紀中國畫壇上的人物形象再創造,又何嘗不是尋找自己舞步的過程呢?當然,這種“再創造”是艱苦的,綜合的,它集中了葉淺予在生活寶庫的浸潤積累,汲取了在藝術寶庫的經驗習得,參鑒了藝術同道的教研啟發,又加以“目識”、“心記”、“意測”的速寫硬功夫錘煉,終于在“再創造”的舞步上跳出了自己的風姿和品格,并在中國人物畫基本功問題上整理出“八寫、八練、四臨、四通”這一套全面的教學要求,他的“民族學”關注和實踐也因此而別具一格。
我不禁會問,怎樣從接觸民族生活到聚焦民族歌舞,并“刷新”中國人物畫題材與筆墨的舞步。更直白一些說,重要的不是看畫中人的舞步,而是看作畫者葉淺予的舞步如何起舞。由此而言,葉先生的民族美學,其實是一個相互之間有動作聯系的有機整體,而我閱讀了葉先生的兩本書,一是他的藝術人生自傳《細敘滄桑記流年》,一是他的藝術問題思考《畫余論畫》,葉淺予在書中對人生的交代和解剖、對藝術的總結和反思,讓人感慨和難忘。當然,他在其中勾勒的民族學圖景也更為豐富多彩、引人入勝。
編輯:沈海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