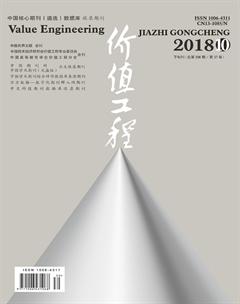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研究
任海靜



摘要:首先,從綜合發(fā)展度、資源環(huán)境承載度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三個(gè)方面構(gòu)建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其次,運(yùn)用主成分分析法,對(duì)青海省以及各州市的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進(jìn)行測(cè)算;測(cè)算結(jié)果表明,青海省2000-2016年綠色發(fā)展水平呈現(xiàn)平穩(wěn)上升的態(tài)勢(shì),綜合得分由2000年的-0.9732提高到2016年的1.2965,2009年綜合得分由負(fù)轉(zhuǎn)正,實(shí)現(xiàn)一個(gè)突破;各市州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有所差距,綠色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是由經(jīng)濟(jì)規(guī)模起決定性作用。最后,從政府作用、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科技創(chuàng)新等方面提出促進(jìn)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對(duì)策建議。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Qinghai Province's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from three aspec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degre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Then, this paper use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level of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various cities.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of Qingha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6 showed a steady upward trend and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increased from -0.9732 in 2000 to 1.2965 in 2016. In 2009,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turn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achieving a breakthrough.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re is a gap in the level of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between cities and stat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is decisive by the scale of the economy.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in Qinghai Province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 ro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關(guān)鍵詞: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主成分分析
Key words: Qinghai Province;green economy;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中圖分類號(hào):F29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6-4311(2018)30-0271-05
0 引言
21世紀(jì)以來,全球經(jīng)濟(jì)正在綠色經(jīng)濟(jì)的引領(lǐng)下逐步轉(zhuǎn)型。發(fā)達(dá)國(guó)家普遍由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轉(zhuǎn)向綠色經(jīng)濟(jì),并從這一結(jié)構(gòu)性轉(zhuǎn)型中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1]。而一些處于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快速發(fā)展階段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正面臨著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向綠色經(jīng)濟(jì)過渡的艱巨任務(wù)[2]。習(xí)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視察青海時(shí)指出:青海省作為國(guó)家生態(tài)安全的屏障,具有及其重要而特殊的生態(tài)地位,必須要承擔(dān)起保護(hù)“中華水塔”和三江源的重任。要從實(shí)際出發(fā),堅(jiān)持保護(hù)優(yōu)先、堅(jiān)持以節(jié)能減排和環(huán)境整治為導(dǎo)向,全面推進(jìn)生態(tài)建設(shè)、美麗城鄉(xiāng)建設(shè)以及自然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加強(qiáng)生態(tài)保護(hù)、沙漠化防治和退牧退耕還林還草,扎扎實(shí)實(shí)推進(jìn)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shè),確保“一江春水向東流”。習(xí)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為青海省更好地處理好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hù)的關(guān)系,指明了新方向[3]。
我國(guó)學(xué)者在綠色經(jīng)濟(jì)方面進(jìn)行了較為廣泛的探討。部分學(xué)者對(duì)于綠色經(jīng)濟(jì)作了理論方面的研究:唐嘯(2014)通過對(duì)國(guó)外已有的關(guān)于綠色經(jīng)濟(jì)理論的分析,得出綠色經(jīng)濟(jì)在不同時(shí)期,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變化有著不同的涵義,具體可分為單一的生態(tài)系統(tǒng)目標(biāo)階段、經(jīng)濟(jì)—生態(tài)系統(tǒng)目標(biāo)階段和經(jīng)濟(jì)—生態(tài)—社會(huì)復(fù)合系統(tǒng)階段[4];丁剛,陳奇玲(2014)通過梳理綠色經(jīng)濟(jì)的五種內(nèi)涵,重新界定了綠色經(jīng)濟(jì)的涵義,認(rèn)為綠色經(jīng)濟(jì)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資源節(jié)約、保護(hù)環(huán)境三者相結(jié)合的經(jīng)濟(jì)[5]。更多的學(xué)者對(duì)區(qū)域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進(jìn)行了評(píng)價(jià)分析:何新安(2014)借鑒了趙彥云等的研究[6],構(gòu)建了由綜合發(fā)展度、資源承載力、環(huán)境容量組成的三維度指標(biāo)體系,并用熵值法對(duì)廣東省河源市2005-2011年的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fàn)顩r進(jìn)行綜合評(píng)價(jià)[7];紀(jì)山山,徐天祥(2016)從規(guī)模性指標(biāo)、激勵(lì)性指標(biāo)、約束性指標(biāo)、保障性指標(biāo)等構(gòu)建了四個(gè)大項(xiàng),十九個(gè)小項(xiàng)的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并采用熵值法和聚類分析法對(duì)江蘇省十三個(gè)省市的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進(jìn)行了實(shí)證分析[8];蔡紹洪,魏媛等(2017)建立了綠色經(jīng)濟(jì)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根據(jù)西部12省綠色發(fā)展的相關(guān)指標(biāo),運(yùn)用計(jì)量方法和GIS記數(shù)法對(duì)2014年西部地區(qū)綠色發(fā)展水平及空間分析進(jìn)行研究[9]。
青海省位于中國(guó)西北部,處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東北部,作為長(zhǎng)江、黃河、瀾滄江的發(fā)源地,承擔(dān)著保護(hù)“中華水塔的重任”,因此,本文運(yùn)用主成分分析法對(duì)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進(jìn)行動(dòng)態(tài)評(píng)價(jià),分析其制約因素并提出相應(yīng)對(duì)策。
1 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和數(shù)據(jù)來源
一般而言,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設(shè)計(jì)應(yīng)遵循全面性、動(dòng)態(tài)性、科學(xué)性、可比性、可行性、結(jié)構(gòu)層次性等基本原則。但是,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目的是發(fā)展環(huán)境友好型產(chǎn)業(yè)、發(fā)展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和低碳經(jīng)濟(jì)、使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自然環(huán)境相協(xié)調(diào)。因此,本文除了遵循上述基本原則外,還以科學(xué)發(fā)展觀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為依據(jù),以注重人民的生活質(zhì)量、注重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水平和環(huán)境效益相結(jié)合、注重教育與科技水平以及注重政府政策支持為指導(dǎo)思路,并借鑒學(xué)術(shù)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構(gòu)建了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見表1),相關(guān)原始數(shù)據(jù)主要來源于《青海省統(tǒng)計(jì)年鑒》(2001-2007)。
2 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水平實(shí)證分析
2.1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一種降維分析,在數(shù)據(jù)信息損失最小的情況下,將多個(gè)維度的數(shù)據(jù)簡(jiǎn)化降維,濃縮指標(biāo)信息,突出主要成分,將復(fù)雜的問題簡(jiǎn)單化,從而使問題分析更加直觀有效[10]。
2.2 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評(píng)價(jià)分析
2.2.1 提取主成分并命名
首先對(duì)4個(gè)逆向指標(biāo)進(jìn)行正向化處理并對(duì)原始數(shù)據(jù)進(jìn)行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運(yùn)用SPSS18.0軟件的分析,根據(jù)特征值>1且累積方差貢獻(xiàn)率大于85%的原則選取3個(gè)主成分(見表2)。
由表2可知,前三個(gè)主成分的累計(jì)貢獻(xiàn)率已達(dá)到91.492%,即用這三個(gè)主成分就能反映22個(gè)原始變量91.492%的信息,分別稱為主成分F1、主成分F2、主成分F3。
從表3的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和第一主成分F1密切相關(guān)的是X1、X3、X5、X6、X8、X20、X21、X22、X10、X11、X12、X13,這些指標(biāo)與經(jīng)濟(jì)規(guī)模、基礎(chǔ)設(shè)施和環(huán)境資源有關(guān),因此F1命名為經(jīng)濟(jì)總量因子。和第二主成分F2密切相關(guān)的是X2、X4、X7、X9、X14、X15、X16,這些與地區(qū)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有關(guān),因此F2命名為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因子。和第三主成分F3密切相關(guān)的是X17、X18、X19,這些指標(biāo)與政府對(duì)綠色經(jīng)濟(jì)的投資有關(guān),因此F3命名為政府政策支持因子。
為更好反映地反映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根據(jù)表4繪制出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時(shí)間序列圖(見圖1)。
圖1直觀反映出自2000年國(guó)家實(shí)施西部大開發(fā)以來,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總體發(fā)展處于平穩(wěn)上升的狀態(tài)。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綜合得分從2000的-0.9732提高到2016年的1.2965,整個(gè)發(fā)展水平呈現(xiàn)出逐年上升的趨勢(shì)。尤其是2009年以后,青海省的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綜合得分由負(fù)值轉(zhuǎn)向了正值,且增長(zhǎng)幅度較大,充分體現(xiàn)出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通過調(diào)整優(yōu)化工業(yè)結(jié)構(gòu)、加快加速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對(duì)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起到了關(guān)鍵性的推動(dòng)作用;也充分體現(xiàn)了我省進(jìn)一步深入貫徹落實(shí)科學(xué)發(fā)展觀,堅(jiān)持走保民生、保增長(zhǎng)、保穩(wěn)定的“三保”路線,積極應(yīng)對(duì)全球金融危機(jī),并取得了經(jīng)濟(jì)回升、社會(huì)穩(wěn)定、人民生活改善的新成績(jī)。
從圖中也可以看出,經(jīng)濟(jì)總量因子F1在2000-2009年發(fā)展規(guī)模較小且波動(dòng)較小,從2010年呈上升趨勢(shì),這與我省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總趨勢(shì)基本吻合,說明經(jīng)濟(jì)總量因子對(duì)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起決定性作用,而經(jīng)濟(jì)總量提高的主要因素是經(jīng)濟(jì)規(guī)模擴(kuò)大、基礎(chǔ)設(shè)施不斷完善和資源環(huán)境問題得到改善,人均GDP和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城市化率和森林覆蓋率的提高、單位GDP能耗和電耗的降低都對(duì)經(jīng)濟(jì)總量的提高有很大的促進(jìn)作用。其他2個(gè)主因子的貢獻(xiàn)要小得多,主要是因?yàn)榻?jīng)濟(jì)總量的發(fā)展速度超出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優(yōu)化速度及政府對(duì)綠色投資的力度。在2012年后,在國(guó)家“五位一體”總布局思想下指導(dǎo)下,政府加大對(duì)綠色經(jīng)濟(jì)的投資力度,政府政策支持因子F3得分迅速提高,說明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離不開政府宏觀調(diào)控。
圖1還表明,雖然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綜合發(fā)展呈現(xiàn)較快的發(fā)展趨勢(shì),但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不合理,政府對(duì)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投資力度較小等因素依然制約著綠色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說明未來青海省的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要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由過去的依靠總量規(guī)模增加轉(zhuǎn)向依靠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來實(shí)現(xiàn)。
2.3 青海省各州市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評(píng)價(jià)分析
2.3.1 提取主成分并命名
對(duì)原始數(shù)據(jù)進(jìn)行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運(yùn)用SPSS18.0軟件的分析,根據(jù)特征值>1且累積方差貢獻(xiàn)率大于85%的原則選取4個(gè)主成分(見表5)。
由表5可知,前四個(gè)主成分的累計(jì)貢獻(xiàn)率以達(dá)到89.518%,即用這四個(gè)主成分就能反映22個(gè)原始變量89.518%的信息,分別稱為主成分P1、P2、P3、P4。
從表6可以看出,和第一個(gè)主成分P1密切相關(guān)的是X1、X3、X8、X21、X22,這些指標(biāo)與經(jīng)濟(jì)規(guī)模有關(guān),因此P1命名為經(jīng)濟(jì)規(guī)模因子;和第二主成分P2密切相關(guān)的是X5、X6、X12、X13、X20,這些指標(biāo)與社會(huì)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有關(guān),因此P2命名為基礎(chǔ)設(shè)施因子;和第三主成分密切相關(guān)的是X17、X18、X19,這些指標(biāo)與政府對(duì)綠色經(jīng)濟(jì)的投資有關(guān),因此P3命名為政府政策支持因子;與第四主成分P4密切相關(guān)的是X14、X15、X16,這些指標(biāo)反映的是區(qū)域能源消耗和環(huán)境污染情況,因此P4命名為環(huán)境壓力因子。
2.3.2 構(gòu)建綜合評(píng)價(jià)模型
由表7可知,在青海省8個(gè)州市中,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綜合得分西寧市排名第一,其他排名依次為海西州、海東市、海北州、黃南州、海南州、果洛州、玉樹州。其中,經(jīng)濟(jì)規(guī)模因子海西州排名第一,基礎(chǔ)設(shè)施因子和環(huán)境承載力因子西寧市排名第一,政策支持度因子果洛州排名第一。
從表7可以看出,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存在嚴(yán)重的區(qū)域差異,但各州市綠色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還是由經(jīng)濟(jì)規(guī)模起決定性作用,這和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總趨勢(shì)基本吻合。P1經(jīng)濟(jì)規(guī)模因子海西州表現(xiàn)最為突出,主要是因?yàn)槲沂〈蟛糠仲Y源型工業(yè)都集中在海西州,工業(yè)的發(fā)展帶動(dòng)經(jīng)濟(jì)規(guī)模的增長(zhǎng);P2基礎(chǔ)設(shè)施因子表現(xiàn)最為突出的是西寧市,西寧市憑借“省會(huì)城市”優(yōu)勢(shì),在醫(yī)療、教育、綠化等方面的發(fā)展水平都比較高;P3政府政策支持因子表現(xiàn)最為突出的是果洛州,近幾年國(guó)家和省內(nèi)出臺(tái)的許多政策措施都傾向于果洛州;P4環(huán)境壓力因子表現(xiàn)最為突出的是西寧市、其次是海西州,這兩個(gè)地區(qū)經(jīng)濟(jì)規(guī)模因子都比較突出,說明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方式不當(dāng)是造成環(huán)境問題的重要原因。
3 結(jié)論與對(duì)策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西部大開發(fā)以來,青海省綠色發(fā)展水平平穩(wěn)上升,主要是因?yàn)榻?jīng)濟(jì)總量的上升,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和政府對(duì)綠色經(jīng)濟(jì)的支持度對(duì)綠色經(jīng)濟(jì)的貢獻(xiàn)率不大,區(qū)域間各因素發(fā)展不平衡,這些因素制約著綠色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為了進(jìn)一步提高青海省綠色發(fā)展水平,同時(shí)平衡區(qū)域間的發(fā)展,提出以下對(duì)策建議。
3.1 充分發(fā)揮政府的宏觀調(diào)控能力
首先,國(guó)家要給予制度和政策支持,為青海省各地區(qū)制定有針對(duì)性的、傾斜的政策,通過轉(zhuǎn)移支付幫助完善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給予技術(shù)和資金的援助,為青海省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提供優(yōu)越的發(fā)展環(huán)境。其次,發(fā)揮政府的調(diào)節(jié)作用,推進(jìn)形成主體功能區(qū),明確不同區(qū)域的主體功能,實(shí)行“區(qū)域限批”項(xiàng)目。加大對(duì)環(huán)保科技的投入比重,大力支持節(jié)能產(chǎn)品、環(huán)保產(chǎn)品、綠色食品等綠色產(chǎn)品的研發(fā)和生產(chǎn),調(diào)動(dòng)企業(yè)和社會(huì)各階層發(fā)展綠色經(jīng)濟(jì)的積極性。對(duì)未按規(guī)定完成節(jié)能減排和和降耗去污的企業(yè)依法進(jìn)行處罰,如吊銷生產(chǎn)許可證、吊銷排污許可證等。盡快完善稅收、財(cái)政、信貸等配套設(shè)施的建設(shè)。最后,政府應(yīng)建立專項(xiàng)基金,開展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試點(diǎn)。
3.2 加快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優(yōu)化升級(jí),發(fā)展綠色產(chǎn)業(yè)
調(diào)整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通過高新技術(shù)和先進(jìn)實(shí)用技術(shù)對(duì)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進(jìn)行升級(jí)改造。推動(dòng)石油、電力、有色金屬和鹽化工等四大支柱產(chǎn)業(yè)在升級(jí)改造中實(shí)現(xiàn)新一輪擴(kuò)張。加強(qiáng)對(duì)支柱產(chǎn)業(yè)在研發(fā)、生產(chǎn)過程中薄弱環(huán)節(jié)的扶持力度,提高生產(chǎn)效率,促進(jìn)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的綠色改造。發(fā)展壯大龍頭企業(yè),促進(jìn)產(chǎn)業(yè)集群發(fā)展,提升市場(chǎng)占有率。
培育發(fā)展新型綠色產(chǎn)業(yè)。一是依托資源優(yōu)勢(shì),發(fā)展新能源、新材料等節(jié)能環(huán)保產(chǎn)業(yè),建立高效的綠色循環(huán)工業(yè)體系。二是發(fā)展特色旅游業(yè),青海省擁有涉及自然、地理、民族、宗教、歷史等眾多鄰域的世界極品旅游資源,吸引著海內(nèi)外眾多旅游者。這些都是青海省發(fā)展旅游業(yè)的優(yōu)勢(shì),只要青海的旅游設(shè)施改善和宣傳促銷得力,這些需求就會(huì)變成現(xiàn)實(shí)的消費(fèi)市場(chǎng)。三是大力發(fā)展綠色農(nóng)牧業(yè),構(gòu)建集約型綠色生態(tài)農(nóng)牧業(yè)體系。加快綠色農(nóng)牧產(chǎn)業(yè)基地建設(shè),建立示范園區(qū),健全綠色農(nóng)牧業(yè)推廣體系,做好農(nóng)牧業(yè)技術(shù)推廣工作。
3.3 建立綠色科技創(chuàng)新體系
科學(xué)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發(fā)展綠色經(jīng)濟(jì),科技支撐、人才是關(guān)鍵。加大綠色科技研發(fā)的財(cái)政投入力度和政府政策傾斜力度,積極與青海省各大高校聯(lián)合,為發(fā)展綠色經(jīng)濟(jì)培育高科技人才。積極建立以企業(yè)為主體、以市場(chǎng)為導(dǎo)向、產(chǎn)學(xué)研相結(jié)合的創(chuàng)新體系,加快對(duì)新能源、環(huán)保節(jié)能等綠色產(chǎn)業(yè)的投資、培養(yǎng)。把青海高新科技開發(fā)區(qū)作為發(fā)展綠色經(jīng)濟(jì)的創(chuàng)新示范區(qū),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等節(jié)能環(huán)保產(chǎn)業(yè),提高資源利用率。鼓勵(lì)企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對(duì)能自主研發(fā)新技術(shù)的企業(yè),國(guó)家要給予政策支持和實(shí)物獎(jiǎng)勵(lì)。
參考文獻(xiàn):
[1]綠色經(jīng)濟(jì)編輯.綠色經(jīng)濟(jì)[J].吉林經(jīng)濟(jì),2012(3):46.
[2]喻清卿.2012年聯(lián)合國(guó)可持續(xù)發(fā)展大會(huì)中方立場(chǎng)文件[OL].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外交部,2012-06-14.
[3]趙靜.青海“十三五”規(guī)劃建議:生態(tài)文明獲得突出[OL].中國(guó)證券網(wǎng),2015-11-24.
[4]唐嘯.綠色經(jīng)濟(jì)理論最新發(fā)展評(píng)述[J].國(guó)外理論動(dòng)態(tài),2014(1):125-132.
[5]丁剛,陳奇玲.綠色經(jīng)濟(jì)的涵義及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的構(gòu)建[J].太原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2014,32(1):1-4.
[6]趙彥云,林寅,陳昊.發(fā)達(dá)國(guó)家建立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測(cè)度體系的經(jīng)驗(yàn)及借鑒[J].經(jīng)濟(jì)縱橫,2011(1):11-34.
[7]何新安.粵東北山區(qū)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實(shí)證分析[J].南方農(nóng)村2014(3):36-39.
[8]紀(jì)山山,徐天祥.江蘇省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評(píng)價(jià)[J].中國(guó)環(huán)境管理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6,26(5):33-36,74.
[9]蔡紹洪,魏媛,劉顯明.西部地區(qū)綠色發(fā)展水平測(cè)度及空間分異研究[J].管理世界,2017(6):174-175.
[10]甘佩娟,丁生喜,霍海勇,李仁帥.柴達(dá)木盆地經(jīng)濟(jì)可持續(xù)發(fā)展綜合評(píng)價(jià)[J].中國(guó)農(nóng)業(yè)資源與區(qū)劃,2014,35(03):5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