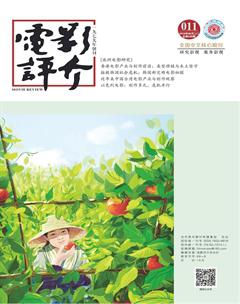譜系建構與歷史再現:電影《無問西東》中的知識分子敘事
朱洋洋
為慶賀清華大學百年校慶而籌拍的電影《無問西東》(編劇、導演:李芳芳)于2011年啟動拍攝,時隔7年之后得以正式公映。作為一部有宣傳色彩和紀念意義的命題作品,其內容與形式必然受到某種程度的約定限制。片名取自清華大學1923年征選而來的中文校歌歌詞,實為“交換灌輸”東西文化,“觀其會通”之意[1],故事架構擺脫不了清華大學的百年歷程,角色人物亦離不開清華大學百年歷程中的紛紛學人。作為一部投資達1億之多,云集了眾多明星的商業化制作,該片也裹挾著巨大的市場野心。從上映之后的觀眾反饋和票房狀況來看,該片成為一部既引起了共鳴也激起了爭議的話題性作品,可謂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因于獨特的時空、人物和結構設定,影片濃縮呈現了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軌跡、心路歷程,構建了一條獨特的知識分子形象譜系,重新伸張了知識分子所負載的價值追求。那么,影片如何拿捏宣講與敘事之間的矛盾碰撞,平衡商業策略與藝術表達之間的關系,達成歷史和現實之間的有效對話,便成為審視其話語構成方式的關鍵路徑。本文將從時空結構、歷史敘述、類型話語等角度,勾勒影片所呈現的知識分子形象脈絡,剖析影片運用的敘事技巧、表達策略,進而解讀其知識分子話語表達背后所蘊含的文化意圖。
一、結構與譜系
影片《無問西東》采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敘事方式,主要圍繞四個時空展開敘述,它從現實時空展開敘事,進而鋪陳了另外三個歷史時空:分別為20世紀20年代、三四十年代以及60年代,實現了四個時空的交織穿插。這種獨特的結構方式,將四個不同時代進行了歷時性的陳述。現實時空以廣告精英/新型文化媒介人①張果果為核心,講述了他的一段商場起伏;20世紀20年代主要圍繞青年學子吳嶺瀾的專業選擇展開;三四十年代講述了粵籍學子沈光耀棄文從戎、英勇報國的故事;60年代則講述了陳鵬、王佳梅、李想三人之間的愛情故事。平行蒙太奇的結構方式可追溯至《黨同伐異》《兩生花》《時時刻刻》《云圖》等片,該片結構在同類敘述邏輯之上則又呈現出獨特之處。影片四個時空、四組人物看似區隔分明,卻又有隱秘的聯系,20年代的主人公吳嶺瀾是三四十年代故事中沈光耀的精神引導者,沈光耀駕駛飛機、空頭物品救助過的云南鄉村恰是60年代的主人公陳鵬的家鄉,而60年代的另_人物李想則是現實時空中張果果父親的救命恩人。由此,影片搭建了一個明晰而又復雜、封閉而又開放的敘事結構。
片中展現的人物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組鮮活群像。按照許紀霖的劃分,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經歷了代際演變,可粗略地劃分為六代:晚清一代(1865-1880年)、五四一代(1880-1895年)、后五四一代(1895-1930年)、十七年一代(1930 -1945年)、文革一代(1945-1960年)、后文革一代(1960年以后出生)。[2]對照來看,影片四個時空的四位主人公吳嶺瀾、沈光耀屬于后五四一代,陳鵬、張果果分屬十七年一代、后文革一代。除卻青年知識分子沈光耀之外,吳嶺瀾、陳鵬、張果果分別在大學、國家科研機構、文化產業中任職,可被統稱為“技術專家治國型知識分子”。[3]除此四人之外,影片將眾多知識分子穿插、點綴進來,如晚清一代的梁啟超、王國維,五四一代的梅貽琦、馮友蘭、錢穆等,后五四一代的粱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錢鐘書、沈從文等。可以發現,影片對文革一代的知識分子形象著墨甚少,依據年齡判斷的話,片中韓童生飾演的張果果的上司Robert,尚可歸于此一代。作為中國的知名高校,清華大學云集而起的命運變遷、歷史波瀾可以堪稱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發展軌跡的縮影,影片的敘事框架正是為了濃縮呈現這種縮影而建立,且進行了有選擇性的調適取舍。
影片獨特的敘事結構實現了不同代際、不同人物之間的隱秘關系,在呈現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代際演變過程中,勾勒出了一條具有內在傳承性質的譜系脈絡。這條譜系的建構,一方面通過精神的引領實現,一方面通過生命的救助體現。前者如梅貽琦之于吳嶺瀾,吳嶺瀾之于沈光耀;后者如沈光耀之于陳鵬,陳鵬之于張果果(陳鵬的言語刺痛并影響了挽救張父、張母性命的李想)。精神的啟發引領主人公邁出新的人生步伐;救命的恩情不僅給予了主人公的肉體生命,同樣也作用于主人公的內心,影響他們的行為方式。這種譜系的構建,內在于時空轉換結構之中,兩者一顯一隱,緊密契合,共同完成了對百年中國知識分子形象的回眸,也描畫出他們延續、更迭、演變的基本脈絡。
二、還原與重構
該片依托四個相對真實的時空背景,直接呈現了四個不同時期清華學人的命運,猶如展現了百年中國知識分子形象的四個鮮活生動的橫切面。在展現歷史時空時,影片十分注重歷史真實感的營造。在進行不同時空的首次切換時,影片用字幕直接標示出相應年代,引導敘事流程的轉換。在敘事過程中,則有針對性地選取標志性的歷史事件、文化事件加以展開。譬如,20年代重點展現了1924年印度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訪華,在清華進行演講的文化盛事;30年代戰火紛飛之際,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知名高校遷至昆明,重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隨之而來的是升級的戰事;60年代的故事中,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到原子彈爆炸成功,成為主人公陳鵬重要的人生歷程。這些事件跳躍式組接了百年中國的社會歷程,既呼應了真實的歷史,也讓歷史的真實呼應了影片中人物的命運,增強了影片的藝術真實。
值得注意的是,在還原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影片又整合進了別致的虛構技巧,體現出獨特的敘述策略。四段時空、四個故事中的四個主要人物分別是吳嶺瀾、沈光耀、陳鵬和張果果,除沈光耀有人物原型參照之外,其余三位則以虛構為主,他們皆可謂是歷史上的無名者。與此對應的則是,影片在每個時空中別有深意的穿插進實有其人的學者名流,他們或作為角色陪襯,或淡化為背景。20年代的故事中,清華校園內有梅貽琦對吳嶺瀾的精神引領,有泰戈爾訪華時一同閃耀在聚光燈下的梁啟超、徐志摩等文化名人;30年代末40年代初,西南聯合大學中有陳寅恪、沈從文、聞一多、朱自清等大家身影的襯托,60年代初,則有蔣南翔、鄧稼先;現實時空中,能被觀眾明確對號的人物則是保送入讀清華大學、曾紅遍網絡的“奶茶妹妹”章澤天。有了這些真實,人、物的映襯參照,影片故事有了歷史和現實的可靠依托,流露出濃厚的歷史色彩和真實感。影片將主要,^、物的虛構故事與次要人物的真實經歷嵌合在一起,無形中完成了對歷史的重構,在印證歷史的同時也解構了歷史。
為了追求真實效果,影片創作者做了大量的文獻考據工作,盡可能從情節和細節上體現每個時代的風貌,呈現人物的品性。①但在這個過程中,創作者也在試圖對歷史話語進行改寫和加工,可從兩點予以說明。首先,就20年代的主要人物沈光耀來說,該人物的原型為畢業于清華大學、祖籍江蘇的抗日英雄沈崇誨(1911-1937)。[4]但到了影片中,沈光耀被重新包裝,改換為廣東人。再者,在60年代的故事中,影片大量啟用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宣傳畫,其中最為關鍵的一幅名為《好兒女志在四方》。追溯其來源的話,會發現同名宣傳畫由當代著名畫家吳性清(1933-2005)所創作,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于1964年9月,一度風靡全國。[5]影片將畫作置入1962年北京市第九人民醫院的走廊,且所呈現的內容與原畫有了較大分別,原畫中的人物本是一男兩女的形象配置,影片中的畫作卻已被修改為兩男一女,貌似經由現代圖像處理技術實現了天衣無縫的技術性重置。類似這種有意為之的處理,一方面服膺了創作者的表達訴求,另一方面也銜接了影片的敘事要求。也正是這種隱秘性的歷史書寫方式,進一步消解了影片指涉的歷史話語的真實性。
三、類型與觀念
本片四段故事的疊加,意在呈現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表達對生命價值的思索,借人物之口反復提及的“真實”“真心”進一步流露出對真切性情的肯定和追求。四段故事看似不同,但其實都在講述知識分子的成長這一統一命題。根據不同的社會情境,作者將人物拋入各自的命運軌跡之中,表達他們的困惑,呈現他們的選擇,見證他們的生命起伏。在呈現這種價值傾向的過程中,影片帶有濃郁的文藝色彩和理想氣息。
不過,影片也十分注重對類型意識的建構。20年代吳嶺瀾的人生困惑,帶有青春片講述個體成長故事的色彩;沈光耀的故事帶有戰爭片的外殼,英勇獻身的抉擇、動人心魄的空戰場面、大無畏的奉獻犧牲精神,都是構成這則故事的關鍵所在,更為重要的是,創作者將他重新設定為廣東籍人士,更是富有深意之筆觸。這一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異常活躍于中國銀幕的黃飛鴻、葉問等粵籍英雄形象,他們既有高超的功夫身手,也有強烈的民族情結①,可謂該片段與這些現代功夫電影巧妙實現了聯結,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現代功夫片的敘事套路;60年代的故事外殼是愛情片,一段三角戀愛引發了人物的命運糾葛、人性博弈;而現實時空的故事則如同演繹了一部商戰片,讓張果果在商海中沉浮掙扎。這些段落性故事的矛盾沖突都較為凸顯,民族大義、愛情使命、利益誘惑的遭遇之中,沈光耀、陳鵬、張果果必須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讓影片增強了敘事的張力和吸引力。
四個不盡相同的類型拼貼在一起,可以都歸結到“成長”這一命題之下。四個不同時期內,四位青年知識分子分別遭遇自身的選擇困境,關乎志趣與潮流、抱負與孝道、愛情與事業、私欲與正念,前兩者有了前輩直接的精神引領,實現了自我的轉化和確認,后兩者雖沒有直接的指引,卻也受益于知識分子的情懷傳統,自覺體認了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當陳鵬拒絕了校方的工作指派之后,校長蔣南翔給予他理解同情;當陳鵬放下愛情再次領受工作之時,門路依然為其開敞;當張果果陷入工作困境之時,他超越世俗觀念,秉持了自己的內心信念,并選擇無私幫助生育了四胞胎女兒的河南農民家庭。影片建構的知識分子群像意圖在茫茫社會洪流中召喚和確認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前兩個階段的故事設定重點體現的知識分子的啟蒙價值,后兩個階段則用越趨世俗化的書寫傳達知識分子的心聲。而這一充滿斷裂和縫隙的敘事脈絡正映射著百年中國知識分子整體的命運變遷軌跡,呼應著中國社會形態格局的發展變化;同時,這一脈絡也逐漸弱化了知識分子理應承擔的公共角色和批判職責,將其應擔負的社會責任意識置換為個體層面的“真心”和“真情”,賦予遵從內心、個性追求以天然的合法性,而這正與借用但悖離了原旨的影片片名“無問西東”所要展現的感性呼吁一致。
整體而言,影片采用巧妙獨特的敘事結構,將近代以來百年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了縮影式展現。影片虛實相間,既回溯了一眾文化精英的風姿,描摹了他們的精神氣度,也用想象和加工對知識分子話語進行了重新整合。影片運用類型策略將故事演繹得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進而傾訴了鼓舞人心的精神訴求。在其完整的敘事體系之下,影片粗略勾勒了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譜系結構,但對知識分子的話語指涉仍遺留了巨大的縫隙。它的跳躍式敘述凸顯了百年知識分子復雜流動的生存狀態、精神氣度、心理意識,同樣也簡化了知識分子群體的跌宕命運,并在某種程度上逐漸抽離了知識分子理應負載的思想內涵和文化價值。
參考文獻:
[1]汪鸞翔.清華中文校歌之真義[J].清華周刊,1925,24(4):8.
[2]許紀霖.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M]∥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82-86.
[3](美)卡爾·博格斯.知識分子與現代性的危機[M].李俊,蔡海榕,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5.
[4]王凱.歷史上真實的沈崇誨[N].新華日報,2018-02-02(13).
[5]吳性清,新中國第一代新年畫開拓者[N].泰州日報,2012-09-07(A09).
①本片導演李芳芳曾說,為了拍攝電影《無問西東》,她翻閱了上百萬字的歷史文獻和十幾萬張歷史圖片、影像。參見宋贊《<無問西東>為什么這么火?》, 《都市快報》,2018年1月16日,第A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