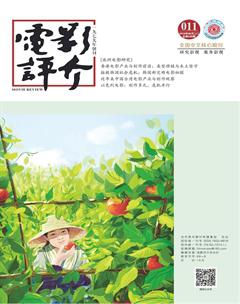《嘉年華》中的符號世界與背后意涵
羅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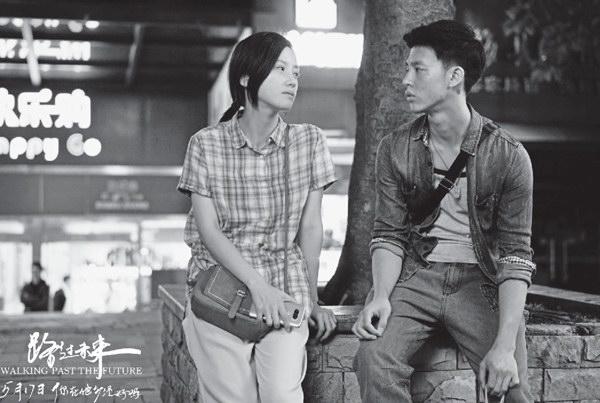
榮獲54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的藝術電影《嘉年華》,上映后獲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績和極高的話題度。電影講述了一個并不復雜的故事:12歲的小學生孟小文(周美君飾)和同學新新遭遇熟人劉會長性侵。事后,劉會長通過各種金錢與權力的運作,試圖掩蓋事實真相。女律師郝潔(史可飾)調查后發現,旅館清潔工小米(文琪飾)有關鍵的視頻證據。小米12歲時離家出走,沒有身份證。為了能夠湊到辦假身份證的錢,小米訛詐劉會長,反被流氓報復。最后小米將視頻證據交給了女律師,劉會長所勾結的各種勢力被依法懲冶。
作為一部藝術電影,《嘉年華》在表現上摒棄了類型片浮夸的表現手法與刻意的矛盾沖突,體現安德烈·巴贊所贊賞的“電影的本性就是對現實的自然反映”[1]的電影美學。冷靜克制的鏡頭背后,導演擷取了各種符號,精心構建了各種隱喻與轉喻,拓展了電影的表意范圍,實現了對現實更為深刻的關照。
在索緒爾看來,不論是語言符號還是非語言符號,都具有“能指”和“所指”雙重屬性,而當人們在交流中,將其所屬的組合軸( syntagrnatic)和聚合軸( paradigmatic)進行重新匹配,就產生了“轉喻”和“隱喻”[2]。電影學中,創作者已經非常熟悉利用各種手段,切割開我們日常生活中非語言符號的所指與能指,通過鏡頭的蒙太奇,有意識地將各種符號經過隱喻和轉喻,傳遞創作者的意圖。
一、電影中的非語言符號隱喻
在《嘉年華》中,大量圖像符號替代了語言,大量的動作替代了文字,通過符號的組合軸展示,極大拓展了符號在本片中的意涵,通過一個又一個的隱喻,帶領觀眾進入符號背后的意義世界。
(一)頭發的隱喻
頭發,在電影中被處理成女性最鮮明的性征符號。《嘉年華》中所有女性角色都是長發。小文的女老師以及新新的媽媽等配角,都一絲不茍地留著各式各樣的長發。在這個有長發的女性世界里,小文的母親暴怒中剪掉了小文的長發,這讓小文成為影片中唯一短發的女性。長發的削除,意味著小文被剝奪掉了女性特征和女性身份。
清潔工小米的長發一直束在腦后。在影片最后,小米被小流氓健哥所控制,成為要在一棟破舊的房屋里“等待客人的暗娼。小米解開了頭發,穿著潔白的無袖紗裙,涂了口紅,戴上了耳環。她一直隱藏的女性魅力在此刻被全部暴露出來。披散的長發標志著她從一個安全的“無性別”身份進入到了一個危險的“女性”身份。
電影里還出現了夢露同款的金色假發套。在電影中,金發套這一符號標志著的是強大的女性魅力:小文帶著金發套,同學新新點評:“你好看我不好看,你有發套。”小米藏起來發套也是因為她喜歡這個金色的發套,而不是因為發套也是潛在的重要證據。
在電影里,頭發作為符號,有著多重的意指:它寄托了女性強烈的自我意識,是女性身體的延伸,也是女性被規訓和被期待的標志。不同的發型、不同的長短、不同的顏色都是女性對自我身體認知的體現。這種符號的體現,既融合了女性的個體意識,又混雜了復雜的社會性別認知。它既可以是女性反抗的無聲吶喊,又可以是社會意識戰勝個體的象征。
(二)夢露雕像的隱喻
巨大的夢露塑像,則是整部電影意涵上最重要的視覺符號。夢露雕像在影片中反復出現六次。這種反復程度,足以看出導演對這一符號的用心刻畫。
夢露的雕像反復出現,但是夢露的臉從來沒有完整地出現在畫面里,只是露出標志性的飛揚裙擺,觀眾就明白那是誰。這是導演利用“夢露”這一性感符號的意義進行意義的平面組合。
事實上,為人們所熟知的夢露,正是奇觀化女性的體現,是“女性的身體形象被夸張為某種異己性的物象,成為審美觀看或者欲望觀看的客體”[3]。在電影中,夢露雕像既是成熟美麗有性誘惑力的象征,同時也被動的、被觀望的、被損害的,無主體性的象征。它是女性身體被物化的典型符號,它的命運也象征著大部分女性,即女性永遠處在被觀看、被損害、被遷移的命運。在這個意義上,夢露雕像面目被刻意截去,正是夢露主體性泛化的表現。
在影片最后,夢露雕像即將迎接新的命運,這鼓舞著同樣踏上新的生命歷程的小米,她勇敢地和夢露一起上路。在那一刻,他們不僅僅在外形上達到一致——同樣的白色連衣裙、同樣飛揚的頭發——而且他們在精神上也同樣勇往直前。
(三)服飾的隱喻
在電影中,和頭發一樣重要的另一個象征物則是女性的服飾。在社會生活中,服飾是個人所具有的社會屬性的重要體現。作為社會符號的它,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透露出大量的訊息,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衣著,判斷對方的職業、性格、社會地位、審美偏好等。在電影中,風格化的服飾更是視聽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典名片《發條橙》中,服飾儀容甚至反映出角色的內心情緒、潛意識想法等。
在電影中,小文的母親、莉莉只穿裙子,不穿褲子。與之相對的,郝律師、新新的媽媽包括電影中一閃而過的女醫生專家都穿著褲子。褲子,是女性靠攏男性世界,抹去自己性征的符號。在西方,褲子只是男性的專屬,經過幾百年的演進,女性才爭取到穿褲裝的自由。[4]電影里,有著正當職業的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為了凸顯自己的“主流”與“正經”,極力地壓抑自己的女性性征,去掉自己的性魅力,模糊自己的性別,彰顯自己女性身份之外的其他社會屬性。相對的,裙子則是極度女性化的象征,不強調穿著者的職業屬性、社會屬性。依附在男性社會中強勢男性的女性,不由自主地在穿著上凸顯自己的女性魅力。
面對圖像符號的平面組合,觀眾在日常的視覺經驗的引導之下,能輕松地對電影中的符號進行新的意義解釋。女性的長發、夢露的形象以及日常的服飾莫不如此。正是這種能指與所指的割裂,電影中意味深長的隱喻由此而生,引入深思。
二、電影中的女性生命與歷程的轉喻
另一種非語言符號新意義的重要產生方式,是利用非語言符號的組合段落,也就是通過某個直線的不可逆的平面展開不同指項的聯想[5],這是符號學中“轉喻”的重要來源。在符號學的研究中,隱喻的研究大大多于轉喻,按照羅蘭·巴特的觀點,這是因為建立在隱喻秩序上的文學相當豐富,而轉喻則少得多。在克里斯蒂安-麥茨將符號學引入電影研究之后,不斷探索如何用語言學的元研究對位電影中的各種組合段和基礎性結構,并且試圖建立一套涵蓋所有蒙太奇敘事結構的組合段。雖然這一提法在學界有爭議,但是麥茨的努力大大拓展了電影符號的囊括性,又由于電影本身依賴聲畫表現的藝術特性,轉喻在電影藝術中獲得新的表現空間。
在《嘉年華》電影中,個體女性成為群體女性的轉喻。不同年齡、不同身份女性的群像,既可以看做是某個因年齡劃分的不同女性群體的轉喻,也可構成時間組合軸上女性整體命運的轉喻。通過轉喻,在電影中實現時間的跨域,從而照見“女性”如何渡過完整生命歷程。角色本身轉化成符號后,彼此獨立又彼此延伸,借由轉喻,進一步擴大了影片的意涵。這樣,電影通過角色不斷推進敘事,完成了轉喻的建構。
(一1小文與幼女的轉喻
幼女小文年僅12歲,在導演的鏡頭下,她的生活只有孤獨與疏離,生活中缺少應有的溫暖與關懷。她是經常遲到的“差生”,老師歧視冷落她,同班男生欺負她,她的好朋友也會出賣她。除了來自家庭和學校的壓力,小文還要面對其他的社會壓力。她被劉會長性侵。報案后,被刑警隊王隊長—再恐嚇。
為了表現小文的內心,導演精心設計了兩個鏡頭,隱喻出人物的內心情感。第一個鏡頭是在游泳池中,小文仰視王隊長的主觀鏡頭,展現王隊長的威勢壓迫、小文的恐懼。第二個鏡頭是小文被婦產專家鑒定為“下體無性行為痕跡”時,小文坐在檢查床上。鏡頭從下往上拍攝小文,畫面中,在床上的小文看起來卻像站在高樓的邊緣,岌岌可危。
在影片中,小文幾乎沒有說過話,在面對各種權威人士的時候,她連話語權都被剝奪,成為一個沉默而倔強的淡薄身影。小文的“無言”即構成了她本人的個性,也更好地轉喻了被剝奪了話語權的“無聲幼女“這一群體形象。這個角色的塑造、其背后的轉喻,寄托了導演對弱小幼女的深切同情與關照。
(二)小文、小米、莉莉和少女的轉喻
電影中,小文、小米和莉莉構成了一種復調隱喻。他們三個人有著截然不同的性格和人生經歷,但是他們面對的困境和未來的選擇卻呈現出一種內在的相似性。
旅館清潔工小米還未滿16歲,而她12歲時就離家出走,在到達這個旅館前流浪過15個地方。“離家出走”與“12歲”這兩個關鍵節點將兩名少女的人生歷程重疊起來。這是后來小米愿意幫助小文的重要心理動機,是兩個未成年女性生命中相似陛的體現。
小文被性侵后,逃離學校,在海灘上無所事事,與世界格格不入。小米則是沒有身份證的黑戶,同樣被社會隔離。小文和小米都弱小而孤獨且無助,被各種精心編制的誘惑所蠱惑,一旦接受了誘惑,就要承受更大的傷害。
電影中的少女莉莉,承擔了小米同事、姐姐和朋友的三重身份。她作為小米生活上的引導者,保護小米教導小米。但是莉莉也不能逃開生活中男性帶來的傷害。她被男友介紹給別的嫖客,她遭受性虐待,還為男友墮胎。
在電影里,少女成長比幼女更有力量,但也無法逃離傷害。在失去公正的世界里,少女群體所渴望的愛情、親情、友情和社會幫助,不是虛偽就是無力。電影最后,少女們互相幫助才走出困境:小米幫助了小文交出證據;小米幫助莉莉打胎,完成了對小健的離別;莉莉幫助了小米找回發套,并且送她能夠逃走的摩托車。
作為角色的少女個性鮮明,但是作為“少女”符號的她們,也同樣有各種符號性的標志。導演所刻畫的少女特質,讓角色本身的符號化更加鮮明。最后,少女們對彼此的幫助,可以視為導演對女性困境的破解之道。
(三)律師、母親與成年女性的轉喻
電影中一共出現了三個戲份較重的成年女性:小文媽媽、新新媽和律師郝潔。小文媽媽是一個在家庭和社會中苦苦掙扎的女性,在處理自己的情緒、家庭、社會生活的時候經常破綻百出。新新媽代表著另一類冷漠精明、自私涼薄的女性。雖然她的鏡頭非常的少,但是幾個鏡頭里,她的語言和肢體動作都非常傳神地體現了她的性格。
律師郝潔是少有的“正面”形象。她是專業、公正、堅毅的象征,同時也是溫暖、善良、真誠的象征。她堅毅不折,面對王隊長壓力毫不退讓。她敏感善良,她最早在廁所工具間找到瑟縮的小文,安撫幫助她。她機智變通,小米向她求救的時候,她不計前嫌拔刀相助。作為女性,她是電影里“拯救者”與“地母”。最終,女性在女性的幫助下,獲得新的救贖。
幼女、少女、成年女性代表著不同的女性生命形態,完整了女性生命蛻變的歷史,只有將他們的存在從結構上作為符號理解,才能更好地把握電影中所蘊含的女性意涵。
結語
電影《嘉年華》被人們當成一次對性侵幼女的重視與呼喚,但是這部電影眾多女性角色勾勒出的是女性作為整體的命運與困境。正如采訪中文晏所言:“有的男性自己很善良,沒想到社會還存在這樣巨大的偏見。更多的男性下意識享受了這種偏見,也沒有意識到,很多女性不得不經受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嘉年華》無非是讓更多的人意識到這一點。”[6]通過對影片《嘉年華》的細讀,我們會發現這部贏得藝術口碑和大眾票房的電影的確是國產影片中的佼佼者,它的藝術成就和現實關懷都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平,其嫻熟豐富的符號運用就是例證。
參考文獻:
[1]楊遠嬰.電影概論(第二版)[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2017: 637.
[2][5]羅蘭·巴特.符號學原理[M].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44.
[3]戴錦華.電影批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109.
[4]史晶晶.褲子的性別一一淺析西方女式褲裝發展史[J]山東紡織經濟,2009(4): 103.
[6]強明萌,粱婷.文晏.我就沒見過哪個女性活得特別灑脫痛快[EBIOL].(2017-12-08)[2018-06-01]http://www.sohu.com/a/209274583 12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