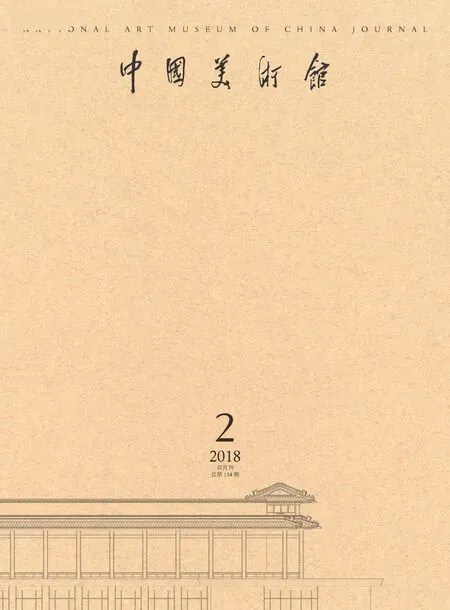論袁江繪畫中的西方因素
王 漢
本文在清初中西文化藝術交流的背景下來討論袁江繪畫的西方因素。文章考察了袁江繪畫中向遠處消失的大路、有明暗的房屋、烏云以及向后收攏的樓閣側面線條這四種對象,并將這四個方面與大致同時期的西方繪畫作比較,指出袁江繪畫曾受到西畫的影響,但袁江對西畫的吸收是“潤物細無聲”式的。
一、引言
公元17世紀和18世紀,西方基督教傳教士陸續來到中國,他們也帶來了許多繪畫作品和繪畫技巧,形成了中國美術歷史上又一波的中西文化交流之潮。在這波文化交流之潮下,許多西方繪畫的因素流入中國。
袁江的山水畫以工細嚴謹著稱,至今仍為人所稱道。“袁江,字文濤,江都人,善山水、樓閣,中年得無名氏所臨古人畫稿,遂大進。憲廟召入祗候。”這是史書記載中年代較早、比較詳備的一種,見于張庚的《國朝畫征續錄》,后來的記載均承此說,大同小異。我們今天贊嘆于袁江精湛的畫藝,按張庚的說法因得古人之法,但按當時的社會情境來看,袁江繪畫應該與西洋畫有一定的關系。換句話說,袁江繪畫風格的形成不僅得益于中國古代傳統,還得益于一些西洋畫的養分滋潤。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在1916年即指出:“袁派參考西洋畫的寫生手法,在山水畫中形成了新的寫實畫派。”近年,王春立在《永遠開放的中國美術》一文亦提到袁江之畫受西畫影響。可惜的是他們的敘述極略,不知據何以立論,直觀感覺為多。因此本文試用形式分析的方法,將袁江山水與西洋繪畫相比較,找出其中的相似之處,并將這種相似之處放在當時特定的時代空間中去考察。由于有關袁江文獻資料非常稀少,我們無法從文字材料上對袁江繪畫受西洋畫法影響這一觀點加以明確闡述,因此我們只能說袁江繪畫中具有西洋繪畫的因素。
二、袁江山水畫中的西畫因素
(一)向遠處消失的大路
作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的《東園圖》卷(見圖1),現藏上海博物館。圖卷長370.8厘米,高59.8厘米,絹本設色。這是一幅極其寫實的畫卷。此寫實有兩層含義:其一,畫面上的景物形象、空間刻畫逼真,使人身臨其境。其二,對照張云章的《揚州東園記》,畫中園林建筑布景與實際幾無差異。卞孝萱在《袁江〈東園圖〉考》一文中所引的詩文是為了進一步說,文獻上所記載的清揚州府江都縣東郊甪里村喬氏東園,與袁江所繪《東園圖》,景物完全相同。再將袁圖與《重修揚州府志》卷首《輿圖》《江都甘泉四境圖》對照一下,還可以看出,袁江《東園圖》上環繞的流水,就是《江都四境圖》上回環曲折的河渠,袁圖上聳立的兩塔,就是《江都四境圖》上的文峰塔和三汊河塔。地理環境也是完全符合的。
這種高度的寫實性本身就異于中國傳統山水畫的理念。明初王履《華山圖》提出“庶免馬首之絡”,指出了以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缺限——中國山水畫在五代宋初盡管帶有明顯的地域特征,但很少有對某一特定山水進行寫實性描寫的作品。王履本人努力踐行自己的觀念,寫出了形象上肖似的華山,然而他卻并沒有因此受到后世畫家們的重視。
畫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畫卷右段的河邊的一條大路。從畫面的下方開始到畫面上方結束,劃出一個大大的“3”字形,幾乎貫穿整個上下畫幅。大路“自近而遠,由大及小”,漸漸消失在遠處的地平線上,具有強烈的縱深感以及真實存在于地平面上的空間延續感。翻檢以往中國山水畫,除去晚明以來,這樣的“路”是從未見過的。
畫面縱深感大致是通過這樣幾個方法形成的:1.大路自身的造型。大路前寬后窄,到了遠處路寬急劇變小;同時“3”字形路的兩個弧,下方的弧跨度極大,弧度極小,而上方的弧跨度極小,弧度極大,對比強烈;大路坡石的大小和繁簡程度也對前后空間距離的形成起著重要作用。2.大路上的人馬車。在大路上出現三組人車馬,近景、中景、遠景中各一組,各組大小呈現為前大后小,變化明顯,這樣前后變化明顯的行旅之人在宋元中國畫中很難見到。3.房屋樹木。中景房屋樹木與遠景房屋樹木的大小對比強烈,形成前后的空間感,特別是遠景樹木,從肉眼可辨的有形樹木至莫可分辨的墨點,營造出特別深遠的空間。這種方法在宋元傳統的中國畫中經常見到,然而對比如此鮮明且創造出極深遠的空間形式卻沒有。4.田畦。大路左側被分割的塊塊田畦隨著路的伸展近大而遠小,也對大路的空間縱深感的營造起著輔助作用。田畦的母題在中國畫比較常見,然而明中期的傳統與此不同。
這些方法在焦秉貞的《耕織圖》(見圖18)中有比較明顯的應用痕跡。圖中的田間小路,雖然與前述“3”字有一點兒差距,但是其空間縱深感極強,與袁江《東園圖》效果非常相似。前景樹木與遠景樹木或農具等物體大小的強烈對比加深了這種縱深感。最重要的是兩幅畫都出現了對田畦的描述,焦秉貞的田畦,其大小在空間中依次變小,直至遠方,袁江與焦氏的處理方式類似。應該說袁江技法中對透視法的理解不像焦氏那樣深,也沒有焦氏那樣嚴謹。然而有差別的是《耕織圖》的視點低,而《東園圖》的視點高。在這一點上,《東園圖》更接近西方年代略早的《法蘭克堡景觀》圖。
蘇立文在《明清時期中國人對西方藝術的反應》一文指出,1610年利瑪竇去世以前,南京與南昌的傳教士們向中國參觀者展示了他們圖書館中的許多優秀圖書。例如,納達爾關于基督生平的《福音歷史圖集》(安特衛普,1593年),上邊的插圖是根據威廉克斯與德·澳斯作品復制的,利氏寫道,由于這部書產生的巨大影響,使他覺得有必要為北京傳教團再要一部。他給著名的出版家與印刷家程大約4幅版畫,程大約將這些畫編入他的設計概述書中,用以裝飾造型墨塊。勿庸置疑,吸引程氏的是新穎的藝術形式,它們遠勝于適合主題的需要。他還將奧特利烏斯十分精致的對褶地圖集《世界輿圖集》的一個復本以及布朗與霍根堡的《世界城鎮圖集》的最初幾卷帶到北京,當他收到普朗坦的多卷本《皇家圣經》(1568—1572)已是1604年了。在傳教團圖書館至少有5種關于歐洲建筑學方面的圖書,包括兩本維特魯威與一本帕拉第奧的書,中國的學者與畫家們在17世紀初的20年里可能看到過。
高居翰在《氣勢撼人—— 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一書中將張宏、吳彬的繪畫與《世界城鎮圖集》(在高氏的書中此書名《全球城色》)中的版畫相互對照,其中有許多驚人的相似點,高居翰認為晚明繪畫中有許多西方繪畫的因素。

圖2 袁江 《東園圖》 局部

圖3 《法蘭克堡景觀》 銅版畫

圖4 《法蘭克堡景觀》 局部

圖5 《堪本西斯城景觀》 銅版畫
我們循著高居翰的目光來審視袁江與《世界城鎮圖集》中的版畫,也會得出相似的結論。首先看《法蘭克堡景觀》(圖3、圖4),畫中的大河與《東園圖》(圖2)中路的形狀有驚人的相似性,都呈“3”字形,在畫面中的位置相似,制造的景深錯覺相似,利用河里(袁江畫中則是路)中景與遠景中物體的大小對比暗示了空間伸展的方法相似。
再來比較《堪本西斯城景觀》(圖5)與《東園圖》(圖1、圖2),漸遠漸窄的橋梁與隨之而變小的人馬車,制造空間錯覺的方法與《東園圖》無異。另外值得一說的是,《堪本西斯城景觀》畫中遠處地平線上的教堂尖塔堪比于《東園圖》遠處突出于地平線上的寺塔。
所不同的是袁江在遠景處理上更多運用中國的方法,用云霧來虛化遠景,使得地平線附近的景物看上去若有若無,不像西方畫家那樣明晰。

圖6 《landshut城景觀》 銅版畫
附帶說明的是,袁江的繪畫,特別是在他的后期繪畫中,有一個重要的要素——連續一貫的視平線的存在,這個特征在《東園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東園圖》長370.8厘米,高59.8厘米,在這樣長卷式的繪畫中呈現左右一貫連續的地平線,這在傳統山水畫中,難得一見。
總體而言,袁江《東園圖》的空間縱深感與兩幅西方版畫是非常類似的,但卻在中國傳統繪畫中難覓其蹤——除了同樣受西方繪畫影響的晚明部分畫家。
(二)有明暗的房屋
西方繪畫相對于中國繪畫來說,一個最主要的區別性特征是用明暗來造型。利瑪竇指出,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吾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也。
此處說的是肖像,在山水畫中,山石也用明暗來表現立體感,表現受光與背光,然而這些明暗的施用,有時只是區別前后的石塊。在建筑繪畫中,中國的傳統繪畫基本不施明暗,更多是使用線條來表明建筑的結構和空間。
在袁江的繪畫中出現幾處用明暗來表現的建筑,而且明暗的施用均按建筑的轉折結構。例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山水樓閣圖》之六《山莊秋稔》(圖7)。
《山水樓閣圖》,十二條屏,絹本設色,每幅高188.7厘米,寬46.4厘米,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其中第6幅為《山莊秋稔》,圖中部的房屋左側墻壁暗而右側墻壁明,明暗分別處正是左右墻壁的轉折線。這樣的明暗布局,使得這座房屋極具立體感和光影感。
另一個明顯的例子在《阿房宮圖》(圖8)中。阿房宮圖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條屏,絹本,設色,縱193.5厘米,橫658厘米。其中有一個主要樓閣臺基明顯與傳統畫法不同。臺基潔白無瑕,然而左側臺基則顯陰暗,且陰暗轉折處恰是正側面的結構轉折線,不知袁江在此處為何這樣處理轉折線左右的臺基,其中有一點不可忽視——西方繪畫的影響。

圖7 袁江 《山水樓閣圖》局部 中國畫188.7cm×46.4cm 1723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8 袁江 《阿房宮圖》 中國畫193.5cm×658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9 袁江 《山水人物圖》局部 中國畫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10 袁江 《關山夜月圖》局部 中國畫126.5cm×160.4cm 1720 上海博物館藏
其他如:中國國家博物院藏《山水人物圖》(圖9)其中一幅,右下門邊墻的轉折非常明顯,正面白,側面則略施陰影,立體感強。上海博物館藏《關山夜月圖》中關隘上的房屋大約也是如此(圖10)。需要多提一點兒的是,關隘左上與右下的山石有來自右上方的光照射的感覺,山石的右上方有些被提亮的感覺。
具有明暗法西洋繪畫傳入較早,1519年,利瑪竇來華攜來宗教題材的銅版畫,即“寶象圖”“圣母懷抱圣嬰”等圖4幅,贈與當時的制墨大師程大約。后來程氏將四幅銅版畫以木版摹刻收入《程氏墨苑》,其雕刻技法已能表現出富有明暗凹凸、形象生動逼真的西洋銅版畫風格。
1713年,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在北京受康熙指派主持銅版雕版印刷《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圖11),這是一部具有明暗和西方透視法的作品。在《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的第1幅《西嶺晨霞》中,水面上的建筑基座,有明顯的明暗效果,有明顯的明暗交界,左側的臺基暗,而右側的臺基更亮一些。圖9是其中的《延薰山館》圖。房屋使用明暗法繪制,效果特別明顯,光感極強。

圖11 馬國賢(意大利) 《御制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圖之二》 銅版畫
袁江是否曾經看到過《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現在沒有非常直接的文獻證據。但是袁江是進入過宮廷的,這在張庚的《國朝畫征續錄》中有明確記載。因此袁江有很大可能接觸到這批畫作。
(三)山水畫中的烏云
在袁江的《春雷起蟄圖》(圖12)、《春雷起蟄龍圖》(圖14)和《山水樓閣圖》十二屏之二《山雨欲來風滿樓》(圖13)中,袁江都非常寫實地描繪了遠方空中的烏云。
就我個人的視野來看,這樣的母題在以前的山水畫中很少見過。傳統中的云基本為白云,多用墨色烘染或用線勾勒。在描繪“風雨如晦”主題的山水畫中,清之前的畫家多用墨色烘染出風雨中昏暗的氛圍,再加上斜側的線來表現風雨的動感。袁江也曾在幾個圖畫中展示這樣的技法(見圖15《重陽風雨圖》)。

圖12 袁江 《春雷起蟄圖》中國畫 153cm×51cm天津美術學院藏

圖13 袁江 《山水樓閣圖十二屏之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國畫 188.7cm×46.4cm 1723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袁江 《春雷起蟄龍圖》中國畫 134cm×50cm 1723中國美術館藏

圖15 袁江 《重陽風雨圖》中國畫 63cm×28cm中國美術館藏

圖16 《春雷起蟄龍圖》局部與《landshut城景觀》圖對比

圖17 《沉香亭圖》局部
如果看看明末西方傳教士帶來的銅版畫——《landshut城景觀》,圖中上方云層密布,作者應該描繪的是白云,然而由于其使用了明暗法來描繪云層的立體感,云層下方色彩陰暗。我們似乎也可以理解為烏云。當然袁江更有可能接觸的是上面提到的馬國賢的《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還是剛才那幅《西嶺晨霞》圖中,畫面左上方飄著白云,當然被讀解為烏云亦無不可。袁江可能見過這幅畫,激發了他的靈感,在山水畫中去表現烏云翻滾的場景。
另外,對比《春雷起蟄龍圖》,烏云的大體形態與《landshut城景觀》 (圖16)相似——呈大開口的“U”形,云層下方明亮的天空。甚至整個遠景布置似乎都來自該銅版畫——左邊的山坡,坡后的房屋和高聳的尖塔,向遠處伸展的地面,最遠處的山峰。
(四)向后收攏的樓閣側面線條
大約在康熙庚子年(公元1720年)后,袁江繪畫中的樓閣出現一個并不顯著的變化——建筑側面的結構線呈向后方收攏的趨勢。在我所收集到的有具體紀年在康熙庚子后且有方形樓閣的繪畫中幾乎都有此特征。參見圖17《沉香亭圖》分析圖。A4—A6線條呈向右上方聚合之勢,但A1-A4間依然相互平行,A6與A7兩線向屋前方收攏,與透視法恰恰相反。這是袁江大多數有透視現象樓閣的特征。
盡管這種前大后小的收縮畫法在唐代的墓室壁畫就已經出現,在經過宋元的繼承和發展后,到明代很少見到這樣的處理方式。例如,史載袁江早年學仇英,仇英的很多界畫作品以及更加大眾通俗的書本插圖版畫中,許多建筑側面的結構線都是平行的。是什么原因促使袁江對建筑側面的線條做出這樣的處理?此處當然會有兩種解釋,一是受傳統影響,歷史文獻記載中的袁江“中年得無名氏所臨古人畫稿,遂大進”。另一個解釋則是袁江很可能受到西方繪畫的影響或啟發。高居翰和蘇立文已經證實晚明繪畫是受到了西方繪畫的影響。到了清初,這樣的影響有更多的例證。
焦秉貞,山東濟寧人,康熙時官欽天監五官正。善繪事,祗候內廷。所畫花卉精妙絕倫,其山水、人物、樓觀之位置,自近而遠,自大而小,不爽毫發,系采西洋畫法。“其位置之自近而遠,由大及小,不爽毫毛,蓋西洋法也”,康熙中祗候內廷。焦秉貞奉詔繪畫制《耕織圖》46幅,初印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這是宮廷版畫中影響較大,流傳較廣的本子。自康熙三十五年本后,《耕織圖》出現了多種版本,本刻本、繪本、石刻本、墨本、石印本均行于世。在《耕織圖》中(圖18),房屋的側面線條明顯地向地平線消失,造成比較強烈的空間感和真實感。嘉慶《揚州府志》載: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圣祖仁皇帝巡游江南,過揚州,御賜《耕織圖》一部。”可見其時在揚州應該可以見到《耕織圖》。
馬國賢的《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也是一個西方透視法的學習范本,銅版畫中很多建筑,都采用了西方透視法。
年希堯分別在公元1729年和1735年兩次出版《視學》,圖解說明西方透視法。他在1735年的序中說:“予究心于此者三十年矣。”這說明,大約在1705年,他就已經開始這方面學問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說,在1705年左右,有關西洋透視的方法已經在社會上傳播,并引起年希堯的關注。

圖18 焦秉貞繪,朱圭刻 《耕織圖》 木刻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
除此而外,上文所引蘇立文的論文中提到:“在傳教團圖書館至少有五種關于歐洲建筑學方面的圖書,包括兩本維特魯威與一本帕拉第奧的書,中國的學者與畫家們在17世紀初的二十年里可能看到過。”
三、結論
我們通過上面四個因素來推測袁江的畫作應該受到西洋畫法的影響。1710年的《東園圖》顯示,袁江已經接觸并運用西洋畫法,但是他在樓閣描繪法上依然沿襲過去形成的習慣。利用明暗制造的光影效果可能曾經引起袁江的興趣,他將這種方法應用在部分建筑的繪畫中。在山水畫的天空中描繪烏云似乎是袁江的獨創,但是這一創造靈感應該來自于西方繪畫,特別是各種版畫中對天空云彩的處理。大約在1720年左右,袁江畫樓閣時故意將樓閣檐口線與臺基線向后收攏,不再如前面所繪的那樣平行,因此我們推測袁江此時決定在樓閣畫中加入一些透視法的因素,來改進他的樓閣畫。
當然,袁江在態度上是審慎且穩健的,并沒有過多地或過明顯地采用西洋技法,而是潤物細無聲地讓西洋技法融入其原本的傳統技法之中,保持其前后風格的大致統一。這種學習和應用外來技術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