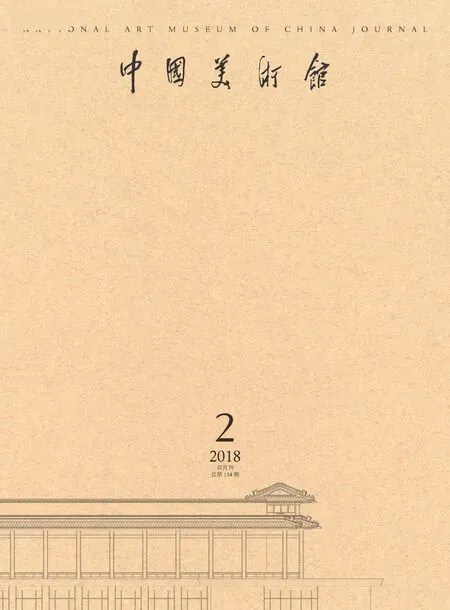涅槃?與生死
——以慶山寺地宮為例看唐代地宮與墓葬的關系問題
熊 雯
荀子曰:“禮者,謹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死生亦大矣。
佛陀涅槃后,身體經荼毗而成舍利,作為佛真身的象征而被崇拜供養。地宮,作為佛陀入滅后舍利東傳中土的最終棲居之地,其與中國傳統人死后“入土為安”墓葬藝術的雜糅,喚起的是一種別樣的曖昧。舍利在塔基地宮中的安置被稱作舍利瘞埋,所謂“瘞埋”,即埋葬的意思,指埋尸土中。《南史》卷七十八《夷貊傳上·海南諸國傳》:“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可見,舍利瘞埋的稱呼已含墓葬之意。
地宮也可以說是一個由多種藝術形式構建而成的佛的“死后世界”。然而,佛陀之“死”畢竟不同于凡俗之“死”。對于一個通達佛教義理的地宮設計者,擺在他面前最大的困境也許就在于,如何借助中土業已成熟的墓葬視覺語匯表達佛陀涅槃的境界而又不致產生混淆?
一、唐代舍利瘞埋制度墓葬化的典型個案——慶山寺地宮
(一)唐代橫穴式地宮的出現
印度舍利安置于窣堵坡地面上的覆缽中。在印度巽加王朝及沙多婆訶那朝所修建的桑奇大塔的覆缽中發現安置舍利的舍利盒、舍利罐等。北印度比布拉瓦、南印度帕丁普羅、中印度包尼窣堵坡舍利函、舍利容器安排在窣堵坡的中心軸上或者靠近中心軸的地方,管狀孔洞內部深處安置舍利。正如白法祖本涅槃經所云:“舍利金甕,正著中央,興塔樹剎。”舍利容器通常都是埋藏在靠近覆缽中心軸的位置。可見在印度并沒有出現塔基地宮。
從目前考古發掘的中國塔基地宮遺址來看,北朝至隋的地宮多為豎穴式地宮,用護石、護磚等包圍石函的方式埋藏。而唐代開始出現類橫穴式墓的橫穴式地宮。著名的法門寺地宮即為橫穴式地宮。
陜西臨潼慶山寺地宮北面渭水,南枕驪山,西距漢新豐故城1.5公里,東與鴻門坂約0.5公里的距離。慶山寺地宮建筑為距地表六米的券頂磚室,正南北方向,平面呈甲字形,整體為磚砌,由斜坡道、甬道和主室三部分構成,甬道和主室之間有石門。地宮形制為典型的橫穴式地宮。
(二)金棺銀槨的開創
慶山寺地宮中的金棺銀槨是唐代具有代表意義的金棺銀槨。銀槨放置在鎏金工字須彌座的棺床上,金棺放置在銀槨內。此套金棺銀槨具體情況如下:
銀槨長21厘米、大頭高14.5厘米、寬12厘米;小頭高10厘米,寬7厘米。從下到上依此為長方形鏤空座-前高后低的梯形槨身-弧形槨蓋。銀槨放置在須彌座上工字須彌座棺床上,棺床呈長方形,長23.4厘米,寬17厘米,高12厘米。四周飾鏤空欄桿。金棺長14厘米,大頭高9.5厘米,寬7.4厘米,小頭高6.5厘米,寬4.5厘米。下有長方形鏤空座,上面蓋為弧形。
可見,橫穴式地宮和類似中原葬具的金棺銀槨作為舍利容器是唐代舍利瘞埋制度墓葬化的最重要表現。慶山寺地宮正是在這樣的風尚和環境下興建,并體現了這兩大特征。

慶山寺地宮銀槨

慶山寺金棺
(三)慶山寺地宮作為武周之開元年間的重要地宮
慶山寺地宮出土的一塊刊有“開元二十九年題記”的石碑及碑文成為對慶山寺地宮斷代的基本依據。因此,慶山寺地宮始建年代應該武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重建年代應該是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慶山寺地宮體現了武周至開元盛世的佛教藝術情況,又是武則天以來唐代舍利瘞埋制度發生巨變后的產物,值得高度關注和研究。
慶山寺地宮保存相對完整,具體情形見模型圖。遺存的石門線刻和地宮壁畫都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石門門楣、門框、門檻一應俱全,其上遍布精美的線刻, 是唐代線刻藝術的珍品,可與唐代豐富的石刻藝術作一對比研究;尤其是慶山寺地宮出土的壁畫,是唐代地宮中唯一出土的地宮壁畫(法門寺與之相較,也沒有保留下來的壁畫)。鑒于畫史上記載的諸多長安盛唐佛教寺院壁畫已湮沒無聞,慶山寺地宮壁畫“使我們得以窺視長安盛唐寺院佛教藝術的風采”。此外,正如崔善娥女士所注意到的,慶山寺地宮出土的刻有“釋迦如來舍利寶帳”是慶山寺地宮最大的特征。目前國內唐代地宮出土的舍利寶帳實物僅兩座,一座為法門寺地宮景龍二年的“舍利靈帳”,另外一座即慶山寺地宮刊有“釋迦如來舍利寶帳”。
二、慶山寺地宮兼具的佛教與墓葬元素
(一)慶山寺地宮建筑形制、裝飾與唐墓對比
1.建筑形制
關于慶山寺地宮,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地宮地面(包括甬道和主室)地面都被涂成了紅色;二是地宮內環東西北壁的三面須彌座磚臺。
(1) 地面涂成紅丹色。根據《清理記》記載:“主室、甬道地面全用35厘米×35厘米青磚漫鋪。磚間幾乎無縫可尋,磚面遍刷紅丹。”關于地宮地面涂成紅色,在世俗墓葬中尚未見到應該與地宮本身作為舍利瘞埋空間的神圣性有關,可能與佛教中結界灑凈等儀軌亦有關聯。
(2)關于緊挨東西北壁的三個須彌座磚臺的問題。根據《清理記》記載“慶山寺主室的情況寶帳棺床是一工字形須彌座,束腰間雕磚為壺門以作裝飾,座正面施黑色。南北長1.17米,北至北壁。東西至兩壁,寬1.47、高0.30米。座前挨東西兩壁各有一南北長0.90、寬0.25、高0.23米的工字須彌座。座面刷紅丹,座正面涂黑色。”這三個須彌座的磚臺,冉萬里先生認為是對唐代棺床的模仿。不過,在敦煌盛唐石窟中也有很多這樣的凹字形三面臺,如初唐莫205窟。筆者認為慶山寺地宮三壁設須彌座并非模仿唐代墓葬中的棺床,而是對洞窟中安置三世佛的三面環壇的凹字型窟的借鑒。
2.地宮裝飾
從地宮莊嚴(裝飾)來看,慶山寺地宮中的圖像題材和布局顯示了與世俗墓葬的相似性。
首先,在地宮北壁正中出現了“山”的圖像題材,這是以往地宮都沒有出現過的。2014年陜西省考古工作者新近發掘的西安南郊少陵原上的唐朝宰相韓休之墓,北壁出土有一幅獨屏的山水圖。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壁放置山水圖的壁畫布局形式。韓這種在北壁繪制山的做法,似乎有特別的意義。因為中國人自古以北為尊、為上,值得注意的是,五代王處直墓也是北壁繪制有獨立的山水圖,應該是對唐代墓室中流行在北壁繪制山圖的一種延續。因此,慶山寺地宮在北壁正中繪制的山除了有前文所述的特殊象征意義之外,也有可能融合了世俗墓葬的做法。
其次,關于慶山寺地宮東西壁的樂舞題材,也在唐代墓室壁畫中非常流行。韓休墓東壁就繪制有一幅樂舞圖,一對男女舞者在中間對舞,兩側是男女樂師陣容。這種舞者和奏樂者的布局模式與慶山寺地宮有一定類似之處,慶山寺地宮東西壁樂舞圖中兩壁朝北均有一個舞蹈的天宮伎樂。關于在東西壁繪制樂舞圖在很多唐墓壁畫中均可被發現如蘇思勗墓,還有李憲墓都是兩邊對稱畫在東西壁。
佛教凈土圖中兩側的樂舞也為常見的構圖,除了敦煌壁畫,在塔楣中也有樂舞的圖像。關于以樂舞供養佛涅槃在經典中有記載,早在印度就有這樣的圖像先例。可見,樂舞圖也是唐代佛教與墓葬通用的一種的圖像。
(二)慶山寺地宮金棺銀槨與傳統葬具對比
1.金棺銀槨與佛骨真身的象征
這種棺槨形制舍利容器中盛裝的舍利的形式是對舍利即佛真身的一種象征。因為一看到棺槨的形制,中國人心目中浮現的就是尸身藏在其中的場景。在唐代,佛舍利被稱作真身。法門寺塔被稱作“大圣真身寶塔”。金棺銀槨形制是佛真身的象征。正如印度現存有一早期的舍利容器銘文把其所藏的舍利稱為“這是釋迦如來活生生的身體。”可見,棺槨的形制首先在于我們對于佛身體的具象化的概念。換個方式說,金棺銀槨的形制就是佛的身體的具象化,與身體的具體形象連結,象征佛的真身就在其中。所以這種棺槨的形制也可稱作佛身體的象征,或者佛真身的象征。
2.慶山寺金棺銀槨形制的佛教依據
金棺銀槨在唐代作為舍利容器體現了中國傳統葬俗對尸身的重視,也是將佛舍利就視作佛的真身的重要表現,體現了中土傳統的喪葬觀念。然而具體觀察慶山寺的金棺銀槨在與世俗棺槨趨同的基礎上,還有很多佛教的形制特征:
第一,根據前文所述,慶山寺金棺銀槨上的裝飾題材均為佛教的。包括銀槨上的悲慟的弟子、香爐和金棺上的獅子等。
第二,金棺銀槨的形制除了和世俗的棺槨的類同外,還體現了佛教特征——蓋頂的窣堵坡造型和棺底的高須彌座。筆者認為銀絲的螺旋形是類似窣堵坡的累盤和剎頂,瑪瑙珠和寶石類似窣堵坡的覆缽體,這應是對佛教窣堵坡造型的模仿,體現了銀槨盛莊舍利的神圣性。
(三)釋迦如來舍利寶帳及帳前器物與墓葬的關聯
慶山寺舍利寶帳中有很多明顯是佛帳的造型特征。日本學者八木春生在《中國南北朝時代的摩尼寶珠表現諸相》一文中進行了簡要歸納,并認為摩尼寶珠是舍利的化身;此外帳頂菩提樹有佛教意象來源,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記錄 “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缽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干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因此,舍利寶帳的設計者在舍利寶帳上插四枝菩提樹,應該就是畢缽羅樹,其凋零之狀是因為佛陀涅槃之故。
雖然很多特征體現舍利寶帳與佛教的關聯,然而中國傳統形制的帳與傳統墓葬的“下帳”有關系,我們要充分考慮帳這個形制與墓葬之間的關系。
1.唐代殯送之儀中的“帳”

慶山寺舍利寶帳
根據《廣弘明集》卷十七《舍利感應記》記載,隋文帝仁壽時期將舍利分送各州的過程中,“四部大眾威儀齋肅,共以寶蓋、旌幢、華臺、像輦、佛帳、經輿、香山、香缽、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花,或燒或散,圍繞贊唄,梵音和雅。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文中明確到了佛帳,且根據《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是按照轉輪圣王的葬法,因此“帳”在此處已是送葬之用。帳在唐代佛舍利的送殯圖常常見到。如初唐332窟和盛唐148窟壁畫,還有藍田舍利石函上和山西涅槃經變碑中都使用了帳,而且固定的程式應該是寶帳張于棺槨之上,作為對棺槨的裝飾和掩映之用途。
2.“死后世界”的舍宅化
唐代地宮中的舍利石帳,除了迎送舍利的功用以外,其在地宮內放置又轉化為佛的居室空間。根據前文分析,法門寺舍利靈帳和慶山寺舍利寶帳都屬于幄帳形制,幄帳其式原是仿自宮室建筑,即所謂“四合以象宮室,王所居之帷也。”《釋名·釋牀帳》:“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可見幄帳的外形當與宮室房屋相似。“帳上四下而覆,形如屋也。”“四合以象宮室的幄帳,一面成為可以移動的其居所,一面可以用它在室內特設一方象征尊貴的空間。”像宮室的幄帳,在地宮內特設一方象征尊貴的空間。兩個舍利石帳均做成幄帳形制,就是在地宮內有室宅化的功能,類似現實中的佛龕在地宮內特設一方象征佛的尊貴。
石槨是隋唐墓葬中常見的模仿宅室的高級葬具,石槨一般從內到外都有線刻圖案且有仿木結構,如李靜訓墓石槨。石帳和石槨都是地下空間的中心焦點,在墓室里,借由石槨這個模仿死者生前的宅室化建筑,死者得以實體性的存在。
3.舍利寶帳的佛說法圖與帳中墓主像

慶山寺地宮東壁賞樂僧侶
慶山寺地宮釋迦如來舍利寶帳正面的“佛說法圖”,正面向觀者,為所謂“偶像式構圖”。其處于地宮視覺焦點的中心,從刻畫和位置上來說類似于墓葬中的墓主坐帳圖。從墓葬考古來看。從漢代到魏晉南北朝的墓室壁畫中,墓主坐帳圖是一種常見的圖像。東漢劉勝墓,葬于東晉永和十三年(應為升平元年)的冬壽墓,壁畫中男女墓主人分別坐在帳中,帳前置一矮幾。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壁畫所繪平頂帳,帳中墓主端坐,帳的兩側有手持扇、蓋的侍從。此外, 朝鮮安岳375年冬壽墓,朝鮮德興里409年鎮墓,山西太原北齊徐顯秀墓墓室壁畫中都有墓主坐帳圖。
4.舍利寶帳帳前器物與“帳前設奠”
《隋書》云: “又造下帳,令五皇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于前。” “根據《漢舊儀》記載,東漢首都洛陽的皇室宗廟中設有象征著主要受祭者漢高祖的空位,覆以錦繡帷帳,輔以幾案和錯金器物。每逢重要祭祀場合,酒食被奠于座前,當朝皇帝率領百官在座前跪拜,向漢代的創始人致敬。”而在墓室前堂設奠的習俗,已初見于洛陽燒溝漢墓東漢時墓葬中,燒溝墓帳前陳放漆案,上置祭奠之物,包括酒肉等,此外還有劉勝墓中帷帳和帳前的祭祀器物。其次,類似的例子還有敦煌佛爺廟灣西晉133號墓的情況,墓內壁龕內設一空座,空座以磚砌臺子及后面繪的幄帳表達。座前設有器物和燈盞,應該也是供祭祀用的。
筆者發現,將帳前器物根據“帳前設奠”的概念和功能來加以區分則更加清晰。帳前設奠一般包括以下幾類物品:一類是祭奠亡人的酒食,供其享用(祭器);一類是亡人生前喜愛或常用之物(生器);還有一類是所謂“貌而不用”的明器,非常粗糙,象征生活中比較高級的用品。

慶山寺地宮人面青銅壺
以祭器、明器和生器的概念來看待慶山寺地宮寶帳前的器物,慶山寺地宮帳前一些器物在地宮出現的的意義似乎更加明晰:慶山寺地宮出土了錫杖和比丘應該隨身攜帶的器物。“與唐代不同的是,在已經發掘的隋代塔基地宮中,未發現佛具(如錫杖、缽等),這一點更接近印度、巴基斯坦所發現的供養方式。”錫杖,又名聲杖、鳴杖、智杖、德杖。屬于佛教法器,實用品一般為木制,高度齊肩,僧人外出化緣,振搖作響,以替扣門呼喚,并作防身之用。地宮出土的錫杖為銀首金錫杖,長32厘米,杖首用四條粗銀絲焊成桃形輪杖首。每條銀絲上穿三個銀質小環。銀首中央高13厘米、口徑13厘米。金杖作九棱圓首。銀首中央有一單檐四面方塔,有基座和寶珠頂。此錫杖為四股十二镮,應該是釋迦佛制。此外還有些僧人隨身攜帶的剪刀和漉水網還有見到出現在地宮也是作為“生器”供奉在佛前。《南海寄歸內法傳》也記載有域外僧人用的蹀躞十二事。“隨物者,三衣:尼師檀、覆瘡衣、雨浴衣,體:大揵镃、小揵镃、缽囊,絡囊、漉水囊、二種腰帶,刀子、銅匙、缽支、針筒,軍持、澡罐、盛油支瓶,錫杖、革履、傘蓋扇,及余種種所應蓄物,是名隨物。”印度僧人出于護生的目的是要將水用漉水囊過濾一下的,這樣浮在水表面的蟲子就可以被放生,這就是漉水囊出現在地宮供養器物中的原因。
不過,整個地宮的藝術體系絕非只是簡單地吸收世俗墓葬的元素,有其佛教經典依據和禮儀制度;而地宮墓葬化和中國化自有其制度背后的邏輯和根深蒂固觀念之影響。唐代舍利瘞埋與墓葬的互動乃是對佛教外來文明最大程度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