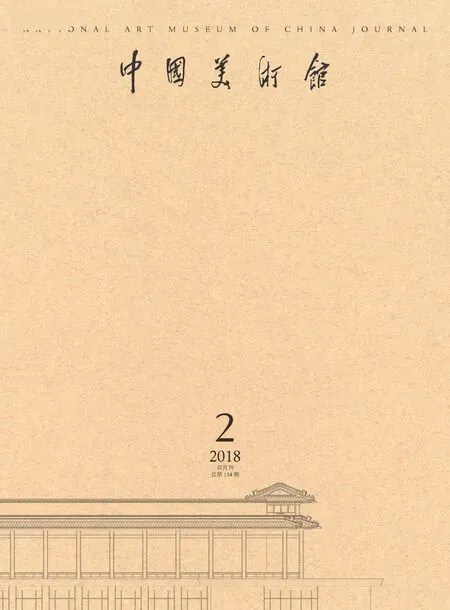關于工藝品“仿制”繪畫原作的文化反思— 以揚州刺繡《雪景寒林圖》為例
李成 趙芳
工藝美術“仿”繪畫由來已久。自明清肇始,工藝直接或間接挪用文人或宮廷趣味圖式,并將之轉化為其他載體作品。“非遺”時代,“仿”繪畫之風幾乎滲透絕大部分民間美術類項目,尤以刺繡為甚。非遺時代,放眼當代文化史,有一個問題變得錯綜復雜,即:手工藝品“仿制”繪畫的文化意義何在?
一、繡品《雪景寒林圖》“仿制”繪畫的技藝和視覺美感
揚州仿古山水繡以摹仿傳統山水畫著稱,仿制《雪景寒林圖》工藝技巧多元,手法精湛完美,被業界公認為國家級項目“揚州刺繡”的代表作品之一。繡成品長1.9米,寬1.6米,創作始于2009年,歷經6年而成(圖1)。
《雪景寒林圖》原作出自范寬之手,畫面氣勢磅礴,生動地描繪了雪后山川如詩景象。畫家勾畫山間村居,一排房屋,隱約可見一人張門而望,仿佛在欣賞山腰寺前雪景;與村居寒林相連,有溪徑木橋,橋下水淺沙平,溪水從遠處縈回而下,匯成一片,雄闊的山河冰封雪裹,寒氣逼人1(圖2)。
根據對繡品創作的實地調研,《雪景寒林圖》的繡制幾經易稿,無數推敲,全面綜合考慮了用線、針法、絲理等諸多“語言”。繡師靈活地運用難以數計的品類絲線,再采取散套、虛針、長短針等數10種針法,用了近五十種墨色繡線,耗費絲線總長達7萬多米。
“仿”古山水刺繡對絲線顏色要求很高,畫中景致的遠近關系、構成元素,均通過絲線粗細加以呈現。繡制分線即劈線,往往將一根花線分成若干份,一般64絲或128絲。繡品《雪景寒林圖》多用普通蠶絲線的1/32,遠處的背景或者水流漸細,為絲線的1/64。線的粗細即為“仿”的基本語言。各種粗細規格絲線,被植入繡品《雪景寒林圖》,既還原了原作的氣勢,也充分體現了揚繡的精妙。
在這幅作品中,繡制者打破仿古山水繡不繡背景的慣例,首先為《雪景寒林圖》整幅畫“打底”,突出灰黑色調,渲染了古畫的風霜。根據訪談,創作者僅為了打底,就耗時一年多。最難以處理的是,《雪景寒林圖》為水墨山水畫,黑白層次分明,為此,繡師們幾乎找來了所有與黑灰色相近的絲線。

圖1 佚名 《雪景寒林圖》 刺繡 2015揚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區精品館

圖2 北宋·范寬 《雪景寒林圖》 絹本設色 193.5cm×160.1cm天津省博物館藏
在“仿”《雪景寒林圖》過程中,繡師們推敲了絲線的絲理“語言”,并強化起針、落針、藏針以及劈線工藝。“絲理”即“絲縷”,是對線條排列方向的處理。“絲光”即線跡的排列方向和角度變化光澤。“起針”為運用繡針的動作,即運針過程中針自下而上的穿引。“落針”,與起針的運動方向相反。“藏針”,繡制放射狀或曲折絲理的花樣,在曲折處滲入短針。
繡品《雪景寒林圖》“仿制”的工藝繁多而豐富,如選稿、絲線色、質感等,但最重要的還是運針所形成的絲線結構,即針法。繡師們認為,繡品《雪景寒林圖》所用針法都有獨特的視覺效果。為了表現原作物體質感,他們深思熟慮,煞費苦心,按照不同針法再現原作,達到異曲同工之妙。
散套針為繡品《雪景寒林圖》使用頻率最高的針法之一。揚繡創作者嘗試了新的絲線排列法,它們參差交織,針針相嵌。“虛實針”,由虛虛實實線條組成,長短不一,由粗到細。“游針”,也是《雪景寒林圖》的輔助針法,特點是針腳長短一致。“長短套針”在《雪景寒林圖》亦多見,針里外出邊齊,第一層先用稀針打底,等長線條之間的距離為兩針。接針,在畫面中多用于繡單線條,一針接著一針,第二針的頭刺入第一針的針尾。2

圖3 佚名 《雪景寒林圖》(局部) 刺繡

圖4 佚名 《雪景寒林圖》(局部) 刺繡
原作《雪景寒林圖》主體為皚皚白雪中一座山勢陡峻的山峰,為整幅畫面的重心所在。3刺繡仿作運用散套針、施針、虛實針、嵌針等針法繡制,力圖還原畫作中山石的巍峨挺秀,重點再現繪畫的立體感(圖3)。繡師們根據山體的走勢確定絲理,山石的明部色彩淡,暗部色彩深;先打底,而后逐漸以細線條密繡;先以黑線及不同色階的黑灰色線繡暗部山石,再用淡赭、黑色線還原亮部山石;過渡處用較暗部淡一些的黑色線繡制,并間加少許影響色。
原作遠景雪山巍峨層疊,重重壁立,氣勢蒼茫,畫家并用了雨點皴與渲染法,極好呈現了山石質地,畫面縱深感亦躍然紙上。大雪初止,遠處的群山籠罩在雪景云霧之中,越遠越顯得模糊。刺繡作品中群山的輪廓皆用淡墨線繡制,絲理方向與山石相同,近處略傾斜,以區別于雪景云霧;雪景云霧絲理垂直,均為虛實針,設色為墨赭色,也略加白色絲線,使之有明顯的大雪覆蓋之感。畫面右側的輔山中,有淡淡霧氣在回旋,寧靜而神秘。幾層溪谷顯得雪后的山林更加的幽靜,此處的針法,越虛越朦朧,越遠越模糊,輪廓用淡墨線繡制,山頭略用白色,使雪山質感及空間感俱佳(圖4)。
原畫作的左面山腰處,有一座寺廟掩映,神秘而又寂寥,似為仙人居處。宋代的界畫和山水畫發展同步,范寬不斷探索新的構圖形式,更加注重對客觀景物的細致描寫。在繡制時,繡師們對《雪景寒林圖》中兩處建筑物的處理也頗費心思。如果線條傾斜,房子肯定也跟著傾斜,繡制出來效果必然欠佳。因此,他們在實際處理時發現,遠處建筑物的用線必須線條挺直,這樣輪廓透視才能極為準確。畫面左下方的茅草房的絲理也應順著草木的覆蓋層次繡制,直斜交叉,線條粗壯,但絕不凌亂,用基本色打底,然后再施出層次(圖5)。

圖5 佚名 《雪景寒林圖》(局部) 刺繡
原作畫面前方有片寬闊的水域,溪流從遠方山中迂回而來,潺潺若響,上有小橋連接兩岸。繡師們采用淡墨色線和虛實針模仿原畫蕩漾水流和波紋的筆意。近處的岸坡,用黑色線繡出暗處,按直絲理、虛實針繡,因為它處在畫面的前方,所以繡得相對實在。范寬原作多用皴擦烘染,刻意留出坡石、山頂處的空白。因此,在繡制此處,繡師亦極力控制留白,以強調雪意(圖6)。
在村落和水域之間,有一片生長茂盛的樹林,為寒冷蕭瑟的秦隴山川平添幾許生氣。仿作畫面的前景樹叢分為明部、暗部、中間三層,明處用淺灰色絲線繡制,暗處用黑色絲線繡制。由于樹葉用點筆畫成,繡制時,線條方向作不同程度的多方向傾斜,或者直繡,針法用纏針。山頭的小樹按照直絲理、虛實針繡制。遠方背景的小樹用淺色絲線、虛針繡制。
《雪景寒林圖》原作筆墨濃重潤澤,層次分明,范寬通過交相錯落的構圖和對墨色的把握,使整個畫面布局嚴整,主次分明,渾然一體。而揚州刺繡者,則“以針代筆、以線代墨”,用特殊刺繡手法再現繪畫,給觀者呈現出了另一種陌生卻似曾相識的視覺效果。因為繡作大量運用散套針與虛實針結合的手法,恰如其分地“仿”繡了原作所表達的蒼茫雪山和北方山岳渾厚峻拔之氣勢,細看則有刺繡嫻熟高超的技術。在刺繡創作過程中,刺繡者將精湛技藝與對中國畫的理解融會貫通,著力“模仿”繪畫的筆法風格和高雅意境。我們認為,“仿”的意義,是創造性地運用粗細不同的絲線,處理繪畫的虛實空間關系及枯筆、濕筆、濃墨、淡彩所表現出來的筆墨意蘊。
眾所周知,在中國畫傳統美學中,筆墨即語言和品位,是中國畫歷經千余年形成的審美精神。在揚州仿古山水繡的筆墨表達上,繡師們“以線代墨”,力圖用另一種介質“仿制”原作,從而達到原有的皴法和暈染筆意。在繡品《雪景寒林圖》中,繡師們運用針線,再融合畫理和繡理,從而在視覺上具備了繪畫意趣。
通過解讀繡品《雪景寒林圖》,刺繡“仿制”的技術和視覺,達到了與繪畫幾乎不相上下的效果,但是,在媒材處理上,因為采用了另一種介質,所以較繪畫增添了絲線光澤,具備了“繡畫難分”和“不是繪畫,勝似繪畫”的美學意義。

圖6 佚名 《雪景寒林圖》(局部) 刺繡
二、“仿制”繪畫現象的思考
刺繡“仿制”繪畫名作的現象為復制抄襲?還是新工藝語言對繪畫進行的二次創作?
孫佩蘭在《吳地蘇繡》一書中認為:“無論從歷史上摹畫的傳統,還是繡畫同理來看,繪畫作品是可以作為繡稿來源之一的。”4
根據筆者實地調研,繡師工作室所有的刺繡作品均為歷代名家畫作,極少有自創畫稿繡作。通過《雪景寒林圖》創作過程的田野考察,筆者認為,刺繡“仿制”繪畫為社會發展的必然。
首先,揚州刺繡傳統功能弱化,同時社會不斷催生新的需求,伴隨現代文化的滲透,三者之間的矛盾不斷彌合。20世紀的社會變革直接引發了刺繡民俗功能的衰退,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和社會審美文化的不斷演化,使得刺繡向藝術欣賞品的方向發展。
其次,刺繡從業者身份發生了變化,即從生活刺繡目的的全民女性技術業余化向商業欣賞的謀生技術專業化方向演進。20世紀50年代,由于我國發展大工業的需要,傳統工藝被作為原始資本積累。51959 年,揚州繡品廠建立。為了彰顯地方文化特色,在傳統刺繡的基礎上,刺繡作品主要以古代山水畫、花鳥畫以及揚州八怪作品為底稿。
再次,“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的提出,給予了揚州刺繡“仿”繪畫復活的契機。2003年,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走上全面、整體保護階段。6自20世紀50年代末,揚州開始繡制繪畫作品,至今僅數十年,遠不足遺產所必須的百年歷史。7必須注意的一點是,2014年揚州刺繡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美術類擴展項目,成為繡畫的藝術欣賞品。也就是說“仿”成就了揚州刺繡的當代榮耀。
田自秉先生認為:“繪畫和工藝美術的分家,人們重視純藝術的繪畫,而忽視與生活實用結合的工藝美術;特別宋代以后,提高了文人畫的地位,以至其他美術落入次要地位,工藝美術更只算是雕蟲小技。”8在《工藝文化譯叢》總序論中,徐藝乙指出:“從歷史上看,文人士子對于傳統物質文化及其研究多不屑一顧,他們依照中國古代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之說行事,崇‘上’而鄙‘下’,能夠心平氣和地‘坐而論道’,卻不愿意以正眼看待器物以及制作器物的工匠,這樣的意識作為文人的傳統一直影響到近代。”9對于這種矛盾,杭間先生認為:“受中國傳統重道輕器,重美術輕工藝觀念影響,工藝美術事實上一直在力圖擺脫低等的地位,自覺地向具有更高地位的美術靠攏,此為常理。而超越實用的‘工藝美術’不是一般的人工制造物,是傳統精神的凝聚物,可供品鑒的‘工藝美術’自會與中國人如影隨形。”10
必須承認,揚州刺繡在集體自覺性“仿制”的過程中,仍需技術和工藝的創造。柳宗悅一再強調:“美術是看的,工藝是用的,美術拋離了生活,單純談美的意義就不大了。他認為,美術的蘇醒便是向工藝性靠攏,只有接觸平民,普及大眾,美的價值才能找到歸宿。”11因此,揚州刺繡對于繪畫的“仿制”附和了刺繡與繪畫圖式趨同的走向。為達到繡成品無限度接近原作的目的,針法持續變化調整,在這種手工技術“再創作”的過程中,針法得到了豐富,繡法也相應得到了提升。正如上述繡品《雪景寒林圖》所示,針法縝密,物體質感突出,粗細結合,疏密相間,針針相嵌,絲理自然,鋒向綺麗,平整有序,所繡畫面以原作視覺規律為依據,技術靈活多變,達到通透流暢、雅俗共賞之境界。正是這些不斷在“仿制”過程中磨礪的極限技術,既豐富了傳統手工藝史,也承載了重大的文化價值。
根據訪談,繡師們一再強調,用針線還原《雪景寒林圖》即為創作。繡師們歷經選稿、讀畫、上稿、配色等前期準備,對繪畫作品進行了二次創作,甚至要對原畫作必要的修改,重新繪制出適應刺繡特點的畫稿。與此同時,她們更要充分理解畫面的空間關系,將經過自己解讀的畫面轉化為立體形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揚州刺繡“仿制”繪畫的工藝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種藝術“再創作”現象。
呂品田指出:“全面轉向審美方面的中國民間美術,是適應現代文化要求而重建其美學形式的現代形態。”12當社會更傾向于開放的、多元的文化品格時,傳統工藝原有的優點往往可能蛻變為致命的弊端而必然不斷地被抖露出來。尤其是當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手工藝類民間美術,意欲應對而不是回避現時社會環境時,它就無可避免地面臨著文化身份轉變的問題。這樣,若在工藝上固守所謂“文化本真性”就顯得不合時宜。當今,工藝也面臨著適者生存的境遇,是一種不斷變化的活態發展過程,固守工藝的本真性,工藝必將失去適應潮流發展的動力和活力。最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也必將成為一種禁錮,工藝更必將會淪落為無人問津的博物館收藏,僅僅剩下人們心頭那落滿塵埃的懷舊情愫。
基于此,如繡品《雪景寒林圖》所承載的那些不斷精進“仿制”繪畫的技藝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時,雖然失去了傳統本真,卻被放置于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之中,這種變遷正因為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而時刻在藝人與市場的互動中不斷生成,于倫理上并不與本真相悖。延伸《雪景寒林圖》個案的探討,其他相關民間手工藝,如剪紙、木雕、雕版印刷手工藝等也都逐漸在“仿制”繪畫的道路上漸行漸遠,正不斷褪去傳統工藝的文化意義。
揚州刺繡“仿制”繪畫的歷史,亦是傳統刺繡工藝的原生性被不斷磨滅的歷史,它變成一種次生性的工藝,或是一種在被磨滅原生基礎上創造出來的新型手工藝。從實質上看,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仿制”繪畫的歷史,弱化了揚州刺繡的傳統真實價值之影響因素——狀態上的原生度、信息上的承載度、時間上的跨越度。正如《雪景寒林圖》所呈現的那樣,當代揚州刺繡“仿制”繪畫的現象一方面失去了傳統的“本真性”,但是反過來,從另一方面亦質疑了理論上所強調的“本真性”,這也正是當代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論研究必須正視的現實悖論。
三、余論
縱觀工藝美術史,不同品類之間的“仿制”司空見慣,如陶瓷或者漆器“仿制”金銀器、青銅器等不勝枚舉。然而,必須注意,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仿制”是低級者對高級者的一種模擬或敬意,絕少有高級者向低級者模仿。工藝美術對于繪畫的“仿制”亦為常見,而繪畫卻鮮有“仿制”工藝者。
“仿制”所包含的動因主要有二:一是以故意或強制性的再創造為目的,通過復制,拓展、探索新技術的可能性。二是為了投機取巧的利益追逐,在未獲得對方允許情況下,剽竊圖像或者成果,其目的在于以較低快捷門檻獲得高額利潤。
從這個意義上看,仿制方式有四種類型:一是簡單的圖式抄襲,即漠視“仿制”過程的再創造,而僅僅為了達到與原品的視覺近似,在文化價值上通常低于原品;二是部分仿制在圖式或者技術上參考原品,但經過了主動的原創性改進,與原品有明顯差異;三是深度再創造,即在對原品全然消化基礎上,注入新的原創理念,使得仿制品轉化為另一種新作品,并通常超越原品;四是挪用式仿制,即刻意將對象元素在新作品中予以錯位,經加工而生成獨立意義的作品。
“仿制”繪畫正如刺繡《雪景寒林圖》那樣,跳過了圖像本體的獨立性和唯一性,將已經獲得公眾認可的熟悉圖像占為己有,僅通過材料和技術的改換及后期加工,獲得可信、可靠的作品。在這個過程中,原初圖像包含最為珍貴的創造性被最大程度地稀釋了,“仿制”既促成了工藝技術精進,同時也篡改了藝術史本體彌足珍貴的獨立性,使得技術和藝術在“仿制”的過程中變得含混不清。并且,不斷刻意細致化的技術極限性探索,使得手工技藝的原生美必然出現異化倪端,亦可能促使技藝本身的脆弱化和精英化。這也是我們在審視繡品《雪景寒林圖》時驚嘆其“仿制”技術和巧奪天工意境的同時所引發的憂思!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導師顧浩先生的悉心指導,在此深表感謝!)
注釋:
1.袁有根《〈溪山行旅圖〉〈雪景寒林圖〉絕非偽作》,《天津美術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第66頁。
2.丹菲《天堂之繡——蘇繡》,華語教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頁。
3.程紹君《品范寬——雪景寒林圖》,《文化學刊》,2016年第7期,第72頁。
4.孫佩蘭《中華錦繡——吳地蘇繡》,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頁。
5.杭間《手藝的思想》,山東畫報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頁。
6.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頁。
7.苑利、顧軍《非物質文化遺產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頁。
8.田自秉《工藝美術概論》,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頁。
9.〔日〕柳宗悅《工藝文化》,徐藝乙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10.11.杭間《“工藝美術”在中國的五次誤讀》,《文藝研究》,2014年第6期,第122頁。
12.呂品田《中國民間美術觀念》,湖南美術出版社, 2007年版,第4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