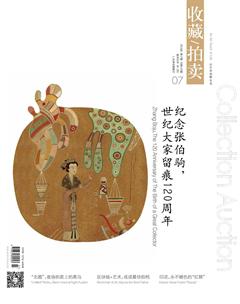不格物不進(jìn)步
近段時(shí)日剛好到京津兩地出差,參觀博物館美術(shù)館也是工作的課目之一。
隔著玻璃,長久注視那些跨越時(shí)空的文物時(shí),會(huì)想,這些文物有何魅力,為何令全世界的人為之傾倒?即使隔著國家、地域、文化、種族、性別等因素,文物上的信息為何會(huì)被很容易讀取?我們?cè)谟^物時(shí)僅僅是只在觀物?
后來發(fā)現(xiàn)“格物致知”有可能是一個(gè)答案。
格物致知是中國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個(gè)重要概念,也是儒家專門研究事物道理的一個(gè)理論,但有趣的是“格物致知”的真正意義卻是儒學(xué)思想的難解之謎。
“格物致知”一詞源于《禮記·大學(xué)》八目——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論述的“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此段。但《大學(xué)》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卻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釋,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過“格物”與“致知”這兩個(gè)詞匯而可供參照意涵。我們當(dāng)今對(duì)這個(gè)詞意的解釋基本還停留在《現(xiàn)代漢語詞典》2012年第六版,將“格物致知”解釋為:“推究事物的原理,從而獲得知識(shí)。”
明末哲學(xué)大家王陽明在他的學(xué)說里非常重視“格物”,曾經(jīng)將此作為一個(gè)修行手段,見物就“格”,也算是不瘋魔不成活,為他的“心學(xué)”著述提供了實(shí)踐基礎(chǔ)。事實(shí)上也證明了中國古人重視物謂之為“厚德載物”。也就是說在實(shí)體的物質(zhì)背后承載著不可見的精神力量。
而西方哲學(xué)普遍會(huì)認(rèn)為物是有其獨(dú)立性的,既存在于認(rèn)知,又獨(dú)立于認(rèn)知。比如列寧指出:“物質(zhì)是標(biāo)志客觀實(shí)在的哲學(xué)范疇,這種客觀實(shí)在是人通過感覺感知的,它不依賴于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為我們的感覺所復(fù)寫、攝影、反映。”
這樣的說法更是說明了“格物”的重要,這是我們獲取認(rèn)知的一個(gè)很重要的途徑。
回過頭來想想為什么以《無題》命名的諸多作品都會(huì)持續(xù)走紅,其實(shí)也就是創(chuàng)作者與觀者之間玩的一個(gè)格物游戲。由“無”而生“無限”的開放性思考空間,讓觀者去探索空間與邊界的關(guān)系。觀者的認(rèn)知就是他自我思想的投射。雖然看到的物,從另外一個(gè)角度看是自由無束縛的自我意識(shí)。畢竟當(dāng)有一個(gè)明確的命名時(shí)也是指向明確的引導(dǎo),少了探索發(fā)現(xiàn)的樂趣。
“格物”的認(rèn)知過程往往就是這樣的樂趣,在一方繡屏或者一盒印泥里,所能捕捉的綜合信息,就是一個(gè)知識(shí)系統(tǒng)的建立。
而博物館正好是這樣認(rèn)知集成的高地。
博物館最多的就是文物,文物的考古價(jià)值是其他一般事物不可比擬的,畢竟涉及制造技術(shù)、造型技術(shù)、意識(shí)形態(tài)、審美標(biāo)準(zhǔn)等一個(gè)綜合性考量,是否體現(xiàn)出當(dāng)時(shí)的最高水平。而在博物館倫理中博物館的收藏則是收縮的,務(wù)必把最高審美的物呈現(xiàn)于世人面前。
認(rèn)知提高,就是“格物”水平的進(jìn)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