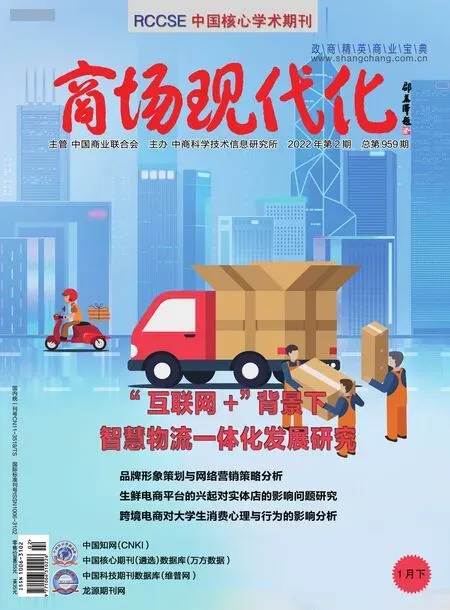已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
支瑤
摘 要:在傳統(tǒng)理論中,基于屬地主義裁決作出地國享有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撤銷權,被撤銷的裁決不具有域外效力。而在新近發(fā)展的“非內(nèi)國化”理論中,被申請承認與執(zhí)行國享有撤銷權,裁決作出地國的司法監(jiān)督權需要予以限制。該理論雖然未被廣泛接受,但已經(jīng)應用于司法實踐中,對傳統(tǒng)理論造成一定的影響。對此問題,我國以《紐約公約》第5條為依據(jù)決定是否拒絕承認與執(zhí)行,但并未對第5條與第7條的關系予以說明。隨著實踐發(fā)展,被申請承認與執(zhí)行國家是否享有自由裁量權成為爭議之一,我國的做法可能將不再符合國際商事仲裁的發(fā)展,應當予以適當改變來適應其趨向。
關鍵詞:撤銷權;承認與執(zhí)行;國際商事仲裁
對于已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能否被其他國家承認與執(zhí)行的問題目前一直沒有普遍定論。不同學者對《關于承認與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為《紐約公約》)第5條屬于授權性規(guī)定還是強制性規(guī)定各執(zhí)己見。此外,“非內(nèi)國化”理論也對傳統(tǒng)觀點產(chǎn)生了一定的沖擊。在探討能否被其他國家承認與執(zhí)行的問題上,首先需要了解撤銷權的歸屬。
一、撤銷權的歸屬
撤銷權的歸屬就是確定哪個國家享有管轄權。
1.仲裁裁決的撤銷權
司法機構(gòu)受理當事人的撤銷之訴或主動啟動撤銷程序,體現(xiàn)了一國司法機構(gòu)對事的管轄權,即撤銷權實際上是司法機構(gòu)的一種管轄權。各國根據(jù)屬人、屬地,對人、對事等標準通過各自的立法行使對具有國際因素的民商事案件的管轄權,與之相同,各國立法也設定了一定的連結(jié)因素,行使對仲裁程序等事項的管轄權。各國根據(jù)不同的因素及不同的標準,規(guī)定了各國司法機構(gòu)對仲裁程序行使管轄權的條件和依據(jù)。
由于各國法律背景、司法實踐等不同,仲裁撤銷制度在各國的規(guī)定各異。同一撤銷之訴在不同國家可能由于其規(guī)定不一樣而得到不同的結(jié)果。以可仲裁事項為例,美國對此規(guī)定較為廣泛,而在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對于可撤銷事項的規(guī)定更為嚴格,同一案件可能在這些國家就面臨著被撤銷的后果。
2.撤銷權歸屬的實踐
要撤銷一項合法的商事仲裁裁決,也就是要撤銷該仲裁裁決的效力。仲裁裁決的效力來源于裁決作出地國或程序準據(jù)法國。當前,仲裁地國享有專屬的撤銷權是國際社會普遍的做法。大部分國家仍期望以這一聯(lián)系實施對仲裁的控制。例如,根據(jù)《聯(lián)合國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第6條、第34條的規(guī)定,法院依法對在其國家境內(nèi)作出的仲裁裁決行使撤銷的權力。而仲裁程序準據(jù)法國的撤銷權主要體現(xiàn)在《紐約公約》第5條。根據(jù)該條規(guī)定,仲裁程序準據(jù)法國家的法院也享有撤銷權。法、德兩國采用該模式,《紐約公約》為協(xié)調(diào)各國的立法實踐,擴大公約的適用范圍,依照法德等國的實踐在仲裁作出地之外加入仲裁程序國作為行使撤銷權的主體之一。雖然《紐約公約》及有些國家的規(guī)定給準據(jù)法國法院行使撤銷權提供了法律依據(jù),但實際上這只具有理論意義。與仲裁地法院行使撤銷權的立法模式相比,仍不具備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二、仲裁裁決撤銷后的域外效力
在被申請承認與執(zhí)行的過程中,各國一般都以國內(nèi)法為依據(jù)進行審查,但是各國法律規(guī)定并不一樣,所以同一項裁決在一國即使被撤銷,在另一國卻未必。
1.裁決撤銷后仍具有域外效力
在平等主權的基礎上,適用具體的法律關系時他國的承認是一國的國內(nèi)法發(fā)生域外效力的前提條件。在此,即能否得到“承認”與“執(zhí)行”的問題。各國家程序法不同,同一案件審查結(jié)果也可能不同。有些國家認為外國仲裁裁決在其國內(nèi)被撤銷即喪失了法律效力,不能予以承認與執(zhí)行;有些國家認為雖然已被撤銷,但本國享有自由裁量權認定是否有效;還有些國家認為即使被撤銷,但只要符合一定的條件其他國家依然可以對其承認與執(zhí)行。
2.具有域外效力的依據(jù)
國際商事仲裁裁決被撤銷后仍具有域外效力,這一認定理由有如下依據(jù):
(1)不具有域外效力的學說具有滯后性
傳統(tǒng)觀點在屬地主義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其認為一旦仲裁裁決被擁有管轄權的法院撤銷,則在該國內(nèi)自然失去法律效力,同時,在他國內(nèi)該裁決亦無法得到承認與執(zhí)行。從理論以及相關司法實踐來看,傳統(tǒng)觀點依然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國際商事仲裁一直在發(fā)展,傳統(tǒng)觀點并不能面面俱到。例如,當事人選擇仲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意思自治原則以及仲裁中立性等,如果認定已撤銷裁決不具有域外效力,則可能會與當事人最初目的相違背。撤銷制度是為了保證仲裁的中立性和公正性,為了約束仲裁員的過分的自由裁量權。同時,每個國家對于撤銷權的行使條件不一,如果一項裁決被撤銷是由于某些不公正的理由(比如利益關系)而被撤銷的,那么當事人如何尋求救助?若按照傳統(tǒng)的觀點,說明一國的撤銷權有最終的法律效力,那么在國際視野中的公正如何得到平衡,此公正非彼公正,這也與國際私法尋求國際社會的普遍公正不符。
(2)“非內(nèi)國化”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
“非內(nèi)國化”理論認為,承認與執(zhí)行地國在審查的過程中對仲裁有適當?shù)谋O(jiān)督權。仲裁裁決在申請執(zhí)行前是不受任何國家法律監(jiān)督的,任何國家的法院都沒有權力撤銷該仲裁裁決。即使仲裁地國法院撤銷仲裁裁決,執(zhí)行地法院仍可以繼續(xù)依據(jù)其本國的法律承認與執(zhí)行該裁決。該理論中要求盡量減少仲裁地國的司法監(jiān)督的部分主張得到了大部分國家的認可。
“非內(nèi)國化”賦予當事人高度的意思自治權,在解決爭議糾紛時使當事人盡可能地避免有關國家的法律干預。這并非是說不受所有國家的法律控制,至少被申請承認與執(zhí)行國家能夠?qū)υ摬脹Q進行司法監(jiān)督,說明了其司法監(jiān)督權轉(zhuǎn)移至了承認與執(zhí)行國。這一理論體現(xiàn)了非地域化的發(fā)展趨向。“非內(nèi)國化”暫時還不能被廣泛接受,因為各國不可能放棄對其境內(nèi)進行的國際商事仲裁的司法監(jiān)督,但該理論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促使著國際商事仲裁更自由化,各國立法需不斷適應調(diào)整促使仲裁自由化發(fā)展。
(3)具有域外效力的法律依據(jù)
《紐約公約》是被撤銷的仲裁裁決具有域外效力的重要法律依據(jù)之一。有學者認為第5條若為強制性規(guī)定那么不該使用“may”而應用“must”或“should”,但也有專家認為在公約起早之時“may”即是“shall”的意思。該詞的含義已經(jīng)無法考量,即使證明這是強制性之意,隨著國際商事仲裁的不斷發(fā)展,原本的含義也許早已不能滿足現(xiàn)實中仲裁發(fā)展的需要。在當前的國際商事仲裁實踐下,“may”的含義以授權性理解更容易被接受,含義更為廣泛,這也更有利于裁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
另一方面,公約第7條表述為承認與執(zhí)行仲裁裁決提供了更優(yōu)惠權利條款。該表述表明除了該公約,當事人還可以選擇以承認和執(zhí)行地國的國內(nèi)法作為請求的依據(jù);也可以選擇以申請承認和執(zhí)行地國締結(jié)的有關其他條約作為請求的依據(jù)。如果被選擇法律或者公約允許該項裁決,并且更有利或有效,那么就可排除第5條的適用。
三、被申請承認與執(zhí)行國的司法監(jiān)督
傳統(tǒng)理論中國際商事仲裁裁決作出地國法院有司法監(jiān)督權。在實踐中,除了裁決來源地享有對撤裁之訴的排他管轄權,裁決請求執(zhí)行地也想有監(jiān)督的權利,其也須對是否承認與執(zhí)行某項來自國外的仲裁裁決進行審查。據(jù)此可見被申請承認與執(zhí)行國的法院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實踐中,承認與執(zhí)行已經(jīng)被撤銷的仲裁案例鮮少,但表明了各國的態(tài)度導向。目前,這一類案例主要發(fā)生法國法院、美國法院、奧地利法院和比利時法院等國。目前我國依據(jù)《紐約公約》第5條持拒絕態(tài)度,排除了自由裁量權。同時我國沒有關于《紐約公約》第7條更優(yōu)權利條款的規(guī)定,所以對于這兩條的直接關系依然沒有明確。若發(fā)生國內(nèi)法存在比公約更有利的執(zhí)行情況,兩者中哪一規(guī)定作為依據(jù)仍是一個爭議。因此我國應對其關系作出明確的解釋,嘗試采用更優(yōu)惠權利條款的規(guī)定,賦予我國作為被申請國的自由裁量權。
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撤銷權歸屬是一種特殊的司法管轄權在各國間進行劃分的問題,正如對司法管轄權的規(guī)定一樣,各國對撤銷權的歸屬也采取了不同的標準,例如仲裁地應享有專屬的撤銷權,或是仲裁程序地法院才是撤銷權的行使主體。不同的立法模式均有其優(yōu)劣,加之各國實際情況不一、主權國家司法權力平等,撤銷權歸屬的沖突無法避免。所以必須依靠各國的協(xié)調(diào)促使域外效力的問題進一步解決。我國在此問題上需要考慮是否嘗試以第7條為依據(jù)而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參考文獻:
[1]趙健.《國際商事仲裁的司法監(jiān)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林琳.撤銷國際商事仲裁裁決制度研究.大連海事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
[3]楊楠.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撤銷權歸屬問題探析.中國政法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
[4]張美紅.論國際商事仲裁程序“非內(nèi)國化”.蘭州學刊,2014年第7期.
[5]宋連斌,董海洲.國際商會仲裁裁決國籍研究--從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復函談起.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6]傅攀峰.未竟的爭鳴:被撤銷的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zhí)行.現(xiàn)代法學,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