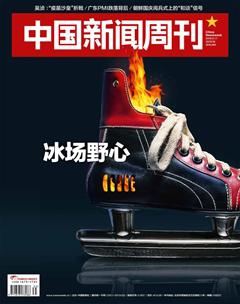高考改革:有效性與公平性之爭
2018-09-27 02:26:02徐天
中國新聞周刊 2018年35期
徐天
高考,既是高校選人,又是一次學生依靠自身努力完成的階級流動。前者講究有效性,后者被期望有公平性。這兩個特性可以共存,但在某些情況下,又隱隱相斥。
招生的自主性是這些年來不少高校努力爭取的權利,爭取過程之艱難,素有耳聞。在浙江進行的三位一體招生,便是高校招生自主性的較好體現。全省統一的高考之后,包括北大、清華在內的一流高校,均要在浙江進行自主命題的筆試、面試,考生的高考成績和自主命題的筆試面試成績各占一定百分比,綜合排序后錄取。
這一招考模式即將在北京進行,政策公布后被諸多學生家長抗議。家境中下游的學生,將更難考上一流高校了,畢竟,無論是學科競賽難度的筆試還是需要靠日常積累的面試,都對學生的時間成本、金錢成本,提出了隱性要求,階級流動的實現愈發艱難。
一名網友評論說,清華、北大都是公辦高校,公辦的學校為什么不更敞開向農村孩子開放?按目前的政策來看,公辦高校的資源是開放的,但也是有限的。教育公平性、普惠性的使命,由高校擴招來完成,越來越多的高中畢業生可以接受進一步的大學教育。而其中最優質的一流大學,則通過最有效的自主招生,選拔出符合他們期待的一批學生,用有限的資源對其進行培養。在這個過程中,高校的思考路徑是自上而下的。而學生和家長的思考路徑則是自下而上的。有效性與公平性在此產生了矛盾。出發點不同,你無法責怪任何一端的思考模式,能在其中調和的,唯有國家政策。
目前,優質高校在中西部連片貧困地區均有單獨的招生名額,但對于東中部普通鄉鎮、農村來說,這里的孩子不乏可培養的優秀人才,他們如何能在高校的自主招生中獲得與城市學生相同的機會,并在這樣的機會中被人鑒別出來,是個難題。
在滿足高校招生自主性、全國高考公平性的前提之下,如何給予這些學生機會,或許是國家政策需要兜底的一個問題。
猜你喜歡
作文大王·笑話大王(2021年4期)2021-04-26 19:00:35
甘肅教育(2020年6期)2020-09-11 07:45:28
大眾投資指南(2020年10期)2020-07-24 08:03:48
甘肅教育(2020年12期)2020-04-13 06:24:56
電影(2018年9期)2018-11-14 06:57:21
作文世界(小學版)(2018年4期)2018-10-16 17:13:34
數學大世界(2017年31期)2017-12-19 12:29:35
快樂作文·低年級(2016年12期)2017-01-03 20:52:44
快樂作文·低年級(2016年6期)2016-06-24 18:58:40
中國航海(2014年1期)2014-05-09 07:5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