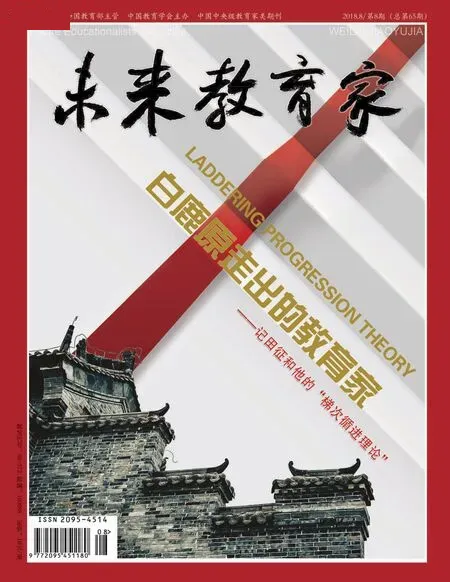由教師到教育家
——田征成長歷程的啟示

20世紀90年代,時任《人民教育》總編輯劉堂江先生就發現了藍田縣的教育典型——田征,被當時那個朝氣蓬勃、辦法總比困難多的小伙子一下子吸引住了。“二十多年來,劉總編一直關注著我的成長、發展,多次來西安藍田調研,給了我很多幫助和建議。”田征說,“這一次采訪,和以前的很多采訪不一樣,劉總編和他的團隊,一直在尋求我成長背后的原因、規律、環境等因素,把我個人的成長與時代的發展和地域的需求結合起來,讓我也重新審視了自我成長之路。”
教育改革發展是一項長期進行但進展緩慢的工作,在這一過程中,教育工作者們碰到的問題大體相似,比如體制機制的牽引因素,師生個體差異,校際辦學差異、區域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問題,這些都是掣肘教育生態健康發展的“攔路虎”,尋求不同教育實踐家改革的路徑以及個人成長的規律,是《未來教育家》的宗旨和使命。
“教育家首先應當是實踐家,實踐是真知的土壤。”在田征身上,我們再一次得出這個結論。
在創新實踐的道路上,田征從未止步,也正因為實踐,梯次循進教育理論才有著無比強大的生命力。“梯次循進”這一母概念,以長期實踐為基礎,汲取傳統教育精華,借鑒現代教育哲學和諸多教育科學成果,體現現代教育發展思想和素質教育理念,通過實踐升華理論和創新,直面教育現實問題,力圖建立一種促進教育實現科學永續發展、促進人實現健康適宜發展的管理評價體系,確立一種體現倫理價值和生態意義的教育新思維。梯次循進生態化教育特性體現為“梯次”的題設。“梯次”既表現為一個靜止狀態中的“物態化”概念,又表現為一個活動狀態中的“生態化”概念。用“梯次”來抽象概念活動行為,既客觀準確,又形象生動。管評對象發展前的基礎呈現梯次差異,發展中的速度呈現梯次差異,發展后的結果呈現梯次差異,實行分類型、分層次推進后,使其發展趨向于平衡,沿著“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平衡”方向不斷進步,體現了事物發展的方向,助動事物和個體因時而宜、因地而宜、因人而宜的發展。在教育管理評價過程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互主體都在實踐中不斷進行自我反思,自我調控,自我完善,力求實現現實發展與理想發展相對意義上的最大、最優化的梯次和諧。梯次循進反映事物的客觀生態,貫穿事物的發展始終,符合事物的發展規律,揭示事物的進化方向,體現主觀與客觀具體歷史的統一,講求可持續發展的教育意義,追求教育“共享差別、生態和美”的發展取向和實踐價值。
古往今來,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有千千萬萬,但絕大多數人,尤其是教育行政人員,鮮有在機制上有大創新、在理論上有大突破。而田征為什么成了教育家并且有了體系較為完整的理論建樹呢?我們認為,田征的成長規律有五點值得關注:
一是豐富的經歷和扎實的基層實踐。在當了兩年民辦教師后,田征考入師范學校讀書,畢業后從語文教師、班主任、教研組長做起,歷經教導主任、副校長,到縣教育局機關教育科科長、副局長、局長,后來又到副省級城市西安市教育局副處長、處長、副巡視員,可以說,他有著最為豐富的基礎教育工作經歷,從一名普通教師逐漸成長為擁有理論建樹的教育管理者,從最基層的農村學校一步一個腳印成長為譽滿全國的知名教育家。
二是積極的問題思考和管評創新。無論身處何種角色,無論工作崗位怎么變化,田征都沒有停止過自己對教育教學問題的思考。思維創新是教育的本質要求。作為教育人,田征在教給學生思維方法,培養學生創新意識的同時,自己在每一個工作崗位,也都保持了積極而獨立的思維。而且,面對困難和問題,他從沒有陷于外界的干擾,總是從自己最熟悉、最擅長的地方入手,尋找到突破口。馬克思的“內因決定外因”理論,在他身上得到鮮明體現。他總是能根據實際情況,對管評機制進行科學的創新,以此對不同層次的教育對象和管理對象實施激勵評價,調動他們的學習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堅持以評價引領和促進教育發展,抓住了教育乃至各行各業持續發展的“牛鼻子”,也把自身的潛力得以充分挖掘。
三是不斷累積的實踐經驗和理論建構。梯次循進教育理論是田征在“白中現象”“藍田現象”成功實踐探索基礎上的經驗總結和學理升華,具有原創性、生態化、適用型的特性。全面的基礎教育工作經歷,賦予了他豐富的實踐體驗、連續的精進思維和科學的改革思路,梯次循進教育理論也伴隨著他的職業生涯不斷延伸而漸漸傳播開來。
四是面向教育未來發展的寬闊視野和行動謀劃。格局決定高度,視野指導創業。田征在教育一線,但其實踐和理論創新,從來沒有局限在一個很小的區域。他腳踩的是一方地域,眼里卻裝著世界。因為有著大格局,所以在小小的白村里他也能夠聯通世界教育前沿;因為有著大氣量,所以冷言冷語從不會阻擋住他前進的步伐。他的創新和理論建構,日漸成為具有普適價值和超越時空的實踐與思想指導。
五是對教育本真發展實事求是的態度與情懷。任何事業的開創源于興趣,盛于適用。但在摸索、創建的過程里,尤其在碰到艱難險阻的時刻,都是意志與情懷的力量在推動事情發展。田征把教育當成畢生的事業,把對孩子的負責作為自己的目標,把還原教育生態本真作為動力,敢于與經常碰到的急功近利、心浮氣躁、彰顯政績等不良風氣決裂,幾十年如一日,潛心于梯次循進實踐與理論研究,這是工匠的精神,這是傳統文化人的操守,這是一個真正現代“士人”的精神風骨。
蘇霍姆林斯基出生于烏克蘭基洛沃格勒的一個貧民家庭,后來長期在農村學校任教。他擔任帕夫雷什中學的教師、校長長達32年,他以長期細心的觀察、持之以恒的探索和孜孜不倦的寫作,奇跡般地寫出了40部專著、600多篇論文、約1200篇兒童小故事,把自己的思維、思索、建議和見解全部傾注在了他的著作當中,即怎樣培養“真正的人”。
不難發現,田征和蘇霍姆林斯基有著相似的成長背景。可以說,他們都是從豐富的教育經歷、積極的問題思考和有效的實踐探索中走出來的教育家,以幾十年如一日的情懷和擔當,為中國乃至人類教育的持續健康發展貢獻著自己的智慧。
教育,是永恒的話題。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教育的理想就在于使所有的兒童都成為幸福的人。“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面對人生,不斷地尋找自我、認識自我,努力地自我實現、自我超越,做有益于事業、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會的人,就是最值得珍重的價值,最有質感的幸福。”田征動情地說。田征是虔誠的播種者,他要把梯次循進理論播撒到教育的沃土里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與田征一樣,期待播種后的生根、發芽、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