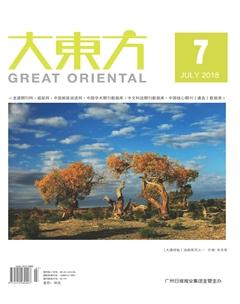《禁閉島》中“島嶼”的象征解讀
摘 要:本文以電影作品《禁閉島》作為研究對象,對電影中島嶼的象征意味進(jìn)行了理性解讀。電影在個(gè)人心理、社會、人性等諸多層面的探討中都蘊(yùn)含著深刻的哲理,也促使了觀眾深思暗含在錯綜復(fù)雜的劇情背后的多重寓意。
關(guān)鍵詞:《禁閉島》;島嶼;象征
改編自美國小說家丹尼斯·勒翰同名小說的電影《禁閉島》是由美國好萊塢導(dǎo)演馬丁·斯科塞斯拍攝的一部懸疑心理片。影片中的島嶼充滿了象征意味,片名《禁閉島》更是增強(qiáng)了這座島嶼的封閉性和神秘感,是一個(gè)耐人尋味的意象,我們可以從中解讀出它隱喻的多重含義。
禁閉島首先是對男主角封閉心理狀態(tài)的一種象征。故事圍繞一座海上孤島展開,情節(jié)由明暗兩條線索交織穿插一并進(jìn)行。明線主要講述了聯(lián)邦執(zhí)法官泰迪和搭檔查克來島上調(diào)查女病人瑞秋離奇失蹤案的曲折經(jīng)過。可在種種撲朔迷離的線索背后,實(shí)際是泰迪帶領(lǐng)觀眾一同尋找“誰是67號病人”。另一條暗線主要以泰迪夢境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其中對戰(zhàn)爭場景和故亡妻子的不斷回憶暗示著他是在對真實(shí)“自我”的一種尋找。種種證據(jù)面前,泰迪最終承認(rèn)了自己就是殺害妻子的兇手,他就是島上“第67號病人”。他一直把自己關(guān)閉在內(nèi)心的“禁閉島”上,活在一個(gè)由臆想構(gòu)造出的虛擬世界里。在那里,他是敢于追求真相的正義執(zhí)法官泰德,從而可以將殺害妻子的罪責(zé)轉(zhuǎn)嫁到他內(nèi)心分裂出來的殺妻兇手——縱火犯安德魯身上。他拒絕做現(xiàn)實(shí)中殺害妻子的安德魯,而是選擇迷失在內(nèi)心的那座禁閉島上,以虛擬泰德的身份繼續(xù)存在著。
故事情節(jié)的背后其實(shí)隱含著諸多的社會問題,結(jié)合故事發(fā)生的時(shí)代背景來理解,禁閉島其實(shí)也是對20世紀(jì)美國社會政治環(huán)境的一種隱喻。故事發(fā)生在1954年,美國政府開始推行麥卡錫主義時(shí)期。當(dāng)時(shí)共產(chǎn)主義思潮在美國也十分盛行,由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政府對共產(chǎn)主義進(jìn)行無情地打壓。在這一過程中,有大量無辜的人被牽扯其中,甚至被誣蔑、誹謗加以莫須有的罪名,這對美國民眾造成了極大的心理陰影,人人自危。影片中所流露出的壓抑、恐懼、迷茫的特征,也正是當(dāng)時(shí)的美國社會所共有的。即使當(dāng)年的時(shí)代已經(jīng)離我們遠(yuǎn)去,但是人類暴力的本質(zhì)并沒有改變,你我淪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的悲劇時(shí)刻還會上演。禁閉島本身就是對社會的一種象征。影片結(jié)束時(shí),站在遠(yuǎn)處的院長、獄長和醫(yī)生,就像他們所代表的政權(quán)、軍權(quán)和科學(xué)權(quán)威,是統(tǒng)治小島這個(gè)孤立社會的最高階層。影片中他們甚至采取切除人的前腦葉白質(zhì)這種殘忍的治療方式,讓精神病患喪失意志和靈魂,成為絕對服從秩序和統(tǒng)治者命令的附屬者。作為一個(gè)社會人,我們又何嘗不是生活在社會這座大的禁閉島上。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是被統(tǒng)治階層管理著的精神病患者。統(tǒng)治階層用道德、法律這些文明的手段管束壓迫著每個(gè)人,我們每個(gè)人的人性也不同程度地被扭曲著、控制著。比如影片中飽受戰(zhàn)爭摧殘的男主角,他始終無法走出戰(zhàn)后的心理陰影,終日酗酒。無法忍受這一切的妻子患上抑郁癥,親手溺死了他們的三個(gè)孩子。男主角發(fā)現(xiàn)后痛不欲生,開槍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從此精神分裂,被關(guān)押在禁閉島上治療。現(xiàn)實(shí)社會生活中也有千萬個(gè)像男主角那樣為了“榮譽(yù)”、為了“正義”而戰(zhàn)的士兵們,他們曾經(jīng)作為國家機(jī)器浴血奮戰(zhàn)、殺戮無數(shù),戰(zhàn)爭中慘無人道的暴行給他們的心靈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痕。很多人不能從戰(zhàn)爭的陰影中解脫出來,甚至無法在戰(zhàn)后的文明社會中正常生活。影片集中營旁尸體堆積如山的畫面,是對戰(zhàn)爭中兇殘行徑赤露露的批判,同時(shí)也控訴了政治暴力將多少無辜的生命變成了權(quán)力的犧牲品。
影片結(jié)尾男主角和醫(yī)生的一番對話,“像正常人一樣活著,還是像好人一樣死去,到底哪一個(gè)更糟呢?”則進(jìn)一步升華了影片的主題。醫(yī)生們嘗試用角色扮演的方式給男主角進(jìn)行精神治療,最終恢復(fù)理智的男主角不愿做一個(gè)清醒面對現(xiàn)實(shí)的“正常人”,而是選擇“像好人一樣死去”(片中以他走向進(jìn)行摘除前腦葉白質(zhì)實(shí)驗(yàn)的燈塔為暗示)。由此,我們可以展開對人性的相關(guān)思考。作為生命存在的我們和管理者們一同處在“生存”這座更大的禁閉島上。作為生物性的存在,人類遵循著自然生老病死的法則。而作為精神性的存在,人類不斷尋找生存的意義,不斷尋找真理和價(jià)值。人類是一種需要意義支撐活下去的生物,自然法則并不賦予生存以意義,對世界本質(zhì)再蹩腳的注解也好過于意義的空白,人類必須制訂一套安身立命于世界中的價(jià)值體系。我們需要充滿意義的生活、充滿價(jià)值的人生以及真正指導(dǎo)人生的真理。從柏拉圖到黑格爾一直試圖尋找證明的“理念世界”已經(jīng)不存在了,尼采宣布了上帝的死亡。舊的價(jià)值體系早已經(jīng)沒落,我們拒絕任何價(jià)值以絕對真理的方式向我們頒布,我們必須直面生存的本質(zhì),憑借每個(gè)人自由的意志從頭去尋找存在的意義。我們就像不斷尋找“瑞秋”的男主角一樣,而尋找本身就是人類在生存這座禁閉島上的存在方式。絕對真理就像影片中的瑞秋一樣,終究不會以某一固定的方式存在,她只存在于尋找的過程中。世界或許本來就沒有根底,每一個(gè)民族都是在自己獨(dú)特的生活實(shí)踐中試圖總結(jié)世界的本質(zhì)、描摹真理的模樣。在人類燦爛的文化長河中,一切形而上學(xué)、倫理學(xué)、宗教都是人類在尋找瑞秋過程中留下的蛛絲馬跡。而當(dāng)你停止尋找的那一刻,即精神理想破滅的時(shí)候,也就意味著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存在,就是選擇自我毀滅的開始。所以影片最后,男主角終究是選擇“像正常人一樣活著”還是“像好人一樣死去”也有了哈姆雷特式追問般的意義。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值得我們每個(gè)人去嚴(yán)肅思考的問題。
藝術(shù)接受是一個(gè)無限的創(chuàng)造過程,一部好的藝術(shù)作品就像一個(gè)掏不盡的黑箱一樣,欣賞者從不同的視角出發(fā)就能獲得不同的感受和啟發(fā)。《禁閉島》是一部極富思想內(nèi)涵的電影,影片中反映出的諸多問題和哲理思考是值得我們不斷細(xì)細(xì)品位和深入挖掘的。
作者簡介:
吳奇霜(1990—)女,苗族,籍貫:湖南懷化人,湖南師范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16級在讀研究生,碩士學(xué)位,專業(yè):藝術(shù)學(xué)理論,研究方向:美術(shù)史論研究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