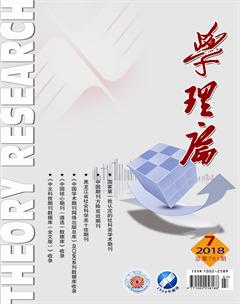彼得洛維奇實(shí)踐哲學(xué)的建構(gòu)
畢燕歌
摘 要:彼得洛維奇針對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壟斷性”的解釋進(jìn)行了系統(tǒng)批判,認(rèn)為斯大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對立的。他從對“人”的理解、異化與揚(yáng)棄異化、實(shí)踐與自由以及社會主義與政治四個主要方面,對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思想進(jìn)行了重新解釋,建構(gòu)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實(shí)踐哲學(xué)。彼得洛維奇實(shí)踐哲學(xué)的建構(gòu)打破了蘇聯(lián)教條主義模式,恢復(fù)了“人”的地位,但卻沒有完全正確理解與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最終走向了人道主義。
關(guān)鍵詞:彼得洛維奇;實(shí)踐哲學(xué);建構(gòu)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7-0075-02
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斷言“物質(zhì)”是全部理論體系的起點(diǎn),而彼得洛維奇的出發(fā)點(diǎn)及關(guān)注點(diǎn)則是“人”。彼得洛維奇認(rèn)為,在馬克思那里,人的概念不只是一個純理論的存在,更是一種對人的現(xiàn)實(shí)生存狀況的反思,是對異化的人的批判,從而將創(chuàng)造性、自由、實(shí)踐、目的、主體等概念穩(wěn)定地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所以,他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重新闡釋了馬克思的哲學(xué)思想。
第一,關(guān)于“人”的理解。斯大林認(rèn)為,在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中,物質(zhì)是最重要的,因此他過于強(qiáng)調(diào)物質(zhì)的客觀性與第一性,重視其決定作用而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割裂了人與世界的統(tǒng)一。彼得洛維奇批判了斯大林主義對馬克思有關(guān)人的理解,他認(rèn)為馬克思一生都致力于實(shí)現(xiàn)人的自由與解放,“人”在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中處于中心地位。他指出:“馬克思不僅允許討論人的一般本性,在《資本論》中,他精確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本性不能得到實(shí)現(xiàn)。因?yàn)樵谄渲小畬④娀蜚y行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則扮演及其卑微的角色一樣”[1]63-64。因此,馬克思設(shè)想了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在那里,人們將在最適合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jìn)行生產(chǎn),實(shí)現(xiàn)自我解放。關(guān)于人的理解,馬克思“既不認(rèn)為理性可以成為人的本質(zhì),也不認(rèn)為政治活動、工具制造、財產(chǎn)或者其他具體活動可以成為人的本質(zhì)”[1]67,人之所以為人,是因?yàn)樗恼w存在方式,人是實(shí)踐的存在。作為實(shí)踐的存在,人類不僅僅是“理性動物”或者“制造工具的動物”,而是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豐富的、立體的人。雖然這種真正的人未必時時刻刻都處于創(chuàng)造狀態(tài),但卻永遠(yuǎn)與創(chuàng)造性本質(zhì)不可分離,并且在面向未來的時候,能夠“意識到歷史賦予他的可能性并創(chuàng)造出更新的和更偉大的可能性”[1]16。
第二,異化與揚(yáng)棄異化。馬克思關(guān)于人的概念是一種對人的現(xiàn)實(shí)生存狀況的反思,是對異化的人的批判,談?wù)撊说母拍畈荒苊撾x關(guān)于異化與揚(yáng)棄異化的這一重要理論。因此,彼得洛維奇認(rèn)真分析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中的異化理論,認(rèn)為異化并非一個經(jīng)濟(jì)問題,而是關(guān)系人的本質(zhì)發(fā)展的問題。他深入分析了馬克思勞動異化的四個特征,認(rèn)為產(chǎn)品的異化、人與人之間的異化是生產(chǎn)異化、人的本質(zhì)異化的結(jié)果和表現(xiàn)形式,異化現(xiàn)象的本質(zhì)即人與自身的異化,自我異化的人與其本質(zhì)相疏離,事實(shí)上并不是他本質(zhì)所是。他提道:“馬克思贊揚(yáng)黑格爾抓住了人的自我創(chuàng)造就是異化和揚(yáng)棄異化的過程這一點(diǎn),”而且“馬克思同意費(fèi)爾巴哈對宗教異化的批判,但是他強(qiáng)調(diào),宗教異化只是人的自我異化的許多形式之一。”[1]120根據(jù)對人的本質(zhì)的理解,彼得洛維奇進(jìn)一步提出,在人類發(fā)展進(jìn)程中,異化和自我異化具有必然性和階段性。“馬克思本人似乎傾向于認(rèn)為,人總是自我異化的,但盡管如此,他能夠而且應(yīng)當(dāng)在將來克服自身的自我異化”[1]129,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chǎn)主義是一切異化的積極揚(yáng)棄,是人復(fù)歸到他的人的存在。但要絕對揚(yáng)棄異化和永遠(yuǎn)消除異化是不可能的,不論是個人層面的還是社會層面的異化,因?yàn)椤敖^對的揚(yáng)棄異化只有當(dāng)人類是一次性全部給定的和不變的東西才是可能的。”[1]131不過,創(chuàng)造一個基本非異化的社會是有可能的,這樣的社會將有助于真正的人的形成。
第三,實(shí)踐與自由。馬克思正是基于對實(shí)踐的認(rèn)識來理解“人”,將人理解為一種實(shí)踐的存在,那么實(shí)踐又是什么呢?彼得洛維奇說:“實(shí)踐首先是指人的一種特定的存在模式,這種模式是特定存在獨(dú)有的,是一種超越人所有其他存在模式,且從根本上與之不同的模式”[1]103。也就是說,實(shí)踐是一種客觀的、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一種人們能動地改變和創(chuàng)造現(xiàn)實(shí)世界及人自身的一切社會性活動。但要真正完全理解實(shí)踐,這樣的解釋還是不夠的。所以,彼得洛維奇又探討了實(shí)踐的核心要素——自由。“自由是實(shí)踐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沒有自由就沒有實(shí)踐;自由的存在必須要實(shí)踐。自由的問題就是實(shí)踐問題的組成部分,因此,也是人的問題的組成部分。”[1]103自由的首要問題是自由的本質(zhì)問題,要想探討自由的本質(zhì)問題,就要先了解自由是憑借什么成為人的組成部分,了解作為人的自由。因?yàn)椤白杂傻谋举|(zhì)問題,就如人的本質(zhì)問題一樣,不僅僅是一個問題。它同時已經(jīng)是對自由生成的參與。”[1]105針對傳統(tǒng)上對自由的三種理解(一,自由是對運(yùn)動或活動的外部障礙的不在場;二,自由是對必然的認(rèn)識;三,自由是自主決定的)彼得洛維奇分別提出自己的觀點(diǎn)進(jìn)行批判,他認(rèn)為自由不是人可自由感知的外在事物,而是他的特殊的存在模式或者存在結(jié)構(gòu);自由的本質(zhì)不是征服已經(jīng)給定的,而是創(chuàng)造新的;只有在人可以創(chuàng)造性地決定其行為,且其行為拓寬人類極限時,他才是自由的。
第四,社會主義的哲學(xué)與政治。很多社會主義國家將哲學(xué)視為政治的仆從,斯大林主義者認(rèn)為哲學(xué)作為政治的需要而存在,應(yīng)為黨和政府服務(wù)。彼得洛維奇反對這種看法,他認(rèn)為馬克思從來沒有如此說明過社會主義的哲學(xué)與政治的關(guān)系。他說道:“如果有人詢問共產(chǎn)主義中哲學(xué)和政治的關(guān)系,我的回答是:作為人類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哲學(xué)應(yīng)該指導(dǎo)人的全部活動,但是我不認(rèn)為政治行為能夠或應(yīng)該由哲學(xué)或某個哲學(xué)論壇定”[1]144,也就是說,哲學(xué)必須使包括政治在內(nèi)的現(xiàn)實(shí)世界成為它的批判對象,也必須破除在狹窄的職業(yè)哲學(xué)家圈子里進(jìn)行討論的限制。彼得洛維奇解讀了馬克思在《哥達(dá)綱領(lǐng)批判》中的共產(chǎn)主義理論,認(rèn)為共產(chǎn)主義本質(zhì)上是實(shí)踐的人道主義的生成,即人的自我異化的揚(yáng)棄與自由的實(shí)現(xiàn),在共產(chǎn)主義社會中,哲學(xué)不是作為政治的或者其他活動的附屬品,也不再是與其他任何活動相區(qū)別的特殊活動,而是全部活動的協(xié)調(diào)力量。同時,政治也發(fā)生了很大的改變,不再處于高高在上的統(tǒng)領(lǐng)地位,而是向著哲學(xué)相同的發(fā)展方向,有更多的評判性思維和討論功能。
綜上所述,筆者認(rèn)為可以從本體論、方法論和價值論幾個維度理解彼得洛維奇的實(shí)踐哲學(xué)。實(shí)踐是彼得洛維奇哲學(xué)的核心范疇,他一直強(qiáng)調(diào)“人是實(shí)踐的存在物”,這具有非常強(qiáng)烈的本體論意味,即是說,實(shí)踐、存在和人構(gòu)成了其哲學(xué)本體論的主要內(nèi)容。他的實(shí)踐哲學(xué)也有解決問題要遵循的原則:一種基于人本身的開放性批判方法,以此辯證法驅(qū)趕異化論始終存在于彼得洛維奇的理論之中。在價值論層面,彼得洛維奇實(shí)踐哲學(xué)自始至終所關(guān)注的中心都是人,實(shí)現(xiàn)人的自由與解放是其追求的目標(biāo),這恰好構(gòu)成了實(shí)踐哲學(xué)的價值取向。
總體而言,彼得洛維奇實(shí)踐哲學(xué)的建構(gòu),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第一,這是南斯拉夫第一次對斯大林主義的哲學(xué)批評。彼得洛維奇對羅森塔爾的批判是南斯拉夫第一次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哲學(xué)批評,他批判了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壟斷性”解釋,認(rèn)為斯大林主義是教條主義的、虛無主義的,完全背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種全面徹底的批判,對彼得洛維奇和整個實(shí)踐派探討馬克思主義的真諦都有重要意義。第二,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人”的地位。彼得洛維奇建構(gòu)實(shí)踐哲學(xué),最重要的貢獻(xiàn)就是批判了斯大林主義對人的存在與作用的忽視,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人的地位。彼得洛維奇在《實(shí)踐》發(fā)刊詞中說道:“近幾十年來,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shí)踐遭受失敗和被歪曲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們力圖貶低馬克思思想的‘哲學(xué)向度,亦即公然或暗中否認(rèn)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人。”[3]325第三,彼得洛維奇沒有抽象地談?wù)撊诵裕菍⑷诵缘挠懻撝糜趯?shí)踐活動之中。在建構(gòu)實(shí)踐哲學(xué)的過程中,抽象的人性不是彼得洛維奇理論的出發(fā)點(diǎn),他不是以抽象的、概括的方式來討論人性,而是堅(jiān)持將人與人的實(shí)踐活動結(jié)合起來,進(jìn)行結(jié)構(gòu)地、具體地和歷史地分析。通過實(shí)踐,人能不斷探索新的發(fā)展方向,更好地認(rèn)識并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滿足自身豐富的需求,實(shí)現(xiàn)一種更人道化的生活,從而發(fā)展為一個更全面的人。
盡管彼得洛維奇的實(shí)踐哲學(xué)建構(gòu)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但其本身也存在局限性。第一,彼得洛維奇建構(gòu)實(shí)踐哲學(xué)是以“人是實(shí)踐的存在”這一命題為前提和基礎(chǔ)的,所以在他看來,無論是馬克思的經(jīng)濟(jì)批判還是政治批判,都是以這個命題為“哲學(xué)基礎(chǔ)”的,馬克思后來的研究結(jié)論都來自這一“哲學(xué)基礎(chǔ)”。顯然,這是對馬克思思想的錯誤理解,并不符合事實(shí)。青年馬克思確實(shí)關(guān)注人及人本身的發(fā)展,那時也主要是一種人本主義的哲學(xué)思想,但正是對人的關(guān)注使他開始對市民社會和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產(chǎn)生興趣,并逐漸深入研究,完成了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到共產(chǎn)主義者的重大轉(zhuǎn)變。第二,彼得洛維奇實(shí)踐哲學(xué)的建構(gòu),雖然掙脫了蘇聯(lián)的教條主義模式,但卻走向了與蘇聯(lián)完全相反的錯誤方向。彼得洛維奇建構(gòu)實(shí)踐哲學(xué)是以人為核心和基礎(chǔ)的,他認(rèn)為全部的問題在于人,社會政治批判的目的是“發(fā)現(xiàn)那些摧殘人、阻礙人的發(fā)展并把某種簡單的、易測的、單調(diào)而刻板的行為模式強(qiáng)加給人的特殊社會制度和結(jié)構(gòu)”[4]8,所以社會主義的目的是人的自我實(shí)現(xiàn)。從根本上來說,這是按照人本主義精神去解釋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第三,對指導(dǎo)南斯拉夫社會實(shí)踐作用有限。彼得洛維奇對哲學(xué)改變世界的功能和理論指導(dǎo)實(shí)踐的作用,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在具體實(shí)踐中,他的理論常常會與現(xiàn)實(shí)社會狀況產(chǎn)生矛盾和沖突,他不能使更多的人尤其是政府信服他的理論,提出的措施無法投入實(shí)踐應(yīng)用,所以實(shí)踐哲學(xué)的價值也就得不到良好的檢驗(yàn),這證明了實(shí)踐哲學(xué)理論在指導(dǎo)社會實(shí)踐的應(yīng)用層面存在著局限。
參考文獻(xiàn):
[1]加約·彼得洛維奇.二十世紀(jì)中葉的馬克思[M].姜海波,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5.
[2]衣俊卿.人道主義批判理論——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述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5.
[3]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加約·彼得洛維奇.實(shí)踐——南斯拉夫哲學(xué)和社會科學(xué)方法論文集[M].鄭一明,曲躍厚,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0.
[4]馬爾科維奇,彼得洛維奇.南斯拉夫“實(shí)踐派”的歷史和理論[M].鄭一明,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