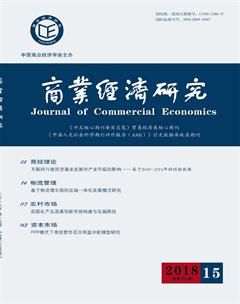我國商貿流通業發展對食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分析
謝育玲
基金項目:廣州工商學院2016年度院級科研課題“‘互聯網+背景下對外貿易創新研究”(項目編號:
KA201614);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2017年度學科共建項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居民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研究—以廣東省為例”(項目編號:GD17XYJ33)
中圖分類號:F724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食品出口不同于一般產品的出口,它對質量要求較為嚴格,而發達的商貿流通業則可以保障食品的安全儲存和運輸,進而對食品安全出口產生影響。本文利用我國2004-2015年間的省級層面數據,就商貿流通業發展對食品業出口競爭力影響的程度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整體上商貿流通業的發展促進了食品在國內市場的銷售,但不利于食品業出口競爭力的提升;分地區來看,商貿流通業的發展增強了東部地區食品的出口競爭力,而對中部和西部地區食品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則都不顯著。
關鍵詞:商貿流通業 食品出口競爭力 促進效應
引言
食品的出口不同于一般的產品,它要求食品能夠得到安全的儲存,并能夠安全快速地運到出口目的地,商貿流通業的發展水平決定著食品能否以較低的批發和運輸成本運送到海外各個消費市場。
目前關于食品出口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術壁壘、食品檢驗標準以及食品出口沿線的安全狀況等。宋國宇和杜會永等(2016)利用灰色分析方法進行的實證分析發現,綠色食品產業的發展壯大有利于擴大黑龍江省食品的總體出口規模。吳洪(2014)通過詳細的案例分析顯示,我國對食品出口的風險和預警存在重大的缺失,這不僅減少了我國食品行業的外貿收入,也對國內食品消費者的利益產生了重大影響。錢華生(2017)進行了詳細的案例分析,指出我國在食品質量安全、包裝安全以及轉基因等方面存在監管不到位等情況,嚴重損害了我國食品出口的形象,對我國食品出口收益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王瑛(2015)認為“一帶一路”沿線的海合會國家由于氣候和人口等方面的因素,使得其對食品的進口量較大,雖然我國的出口食品和這些國家的需求存在較大的互補,但是我國對這些國家的食品出口規模仍然偏小。李丹和王守偉等(2014)認為,雖然加入WTO后我國的食品出口結構有了一定程度的優化,但是我國的食品出口仍然集中在初級農產品和水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而加工類的技術密集型食品依然偏少。周星和范燕平(2008)運用我國1995-2005年間對日本、美國的食品出口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雖然我國的食品出口占有的相對優勢有所提升,但是食品總體的出口競爭力還沒有增強趨勢。蘇芳(2012)以臨夏州食品的生產和加工為例,發現該地區清真食品的加工以及綠色農作物種植的發展,都需要健全的商貿流通業服務的支撐。
本文運用我國2004-2015年間的省級層面數據,實證分析商貿流通業的發展對食品業出口競爭力的促進效應,并為今后食品業提升出口競爭力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議。
實證研究設計
(一)因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采用副食品加工業和食品制造業的總出口額與二者的總銷售產值的比值來衡量食品業的出口競爭力(ex),該比值越大,說明我國的食品越受國外市場消費者的喜歡,我國產品在國外市場越富有競爭力。商貿流通業發展水平由批發和零售業的實際增加值(val)來衡量,實際增加值越大,則表明商貿流通業為國內外其他企業提供商貿服務的能力越強,發展水平也越高;在回歸中若該變量的系數值為正,則表明商貿流通業的發展增強了食品業的出口競爭力。
(二)其他控制變量說明
本文額外選取了6個控制變量,從而控制其他變量對食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
第一,外資流入規模(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與GDP的比值來表示。外資企業在海外市場擁有完整的銷售渠道,因而他們在我國進行投資有利于將更多的食品銷售到海外市場。
第二,城鎮化(city):采用城鎮常住人口與總人口的比值表示。城鎮化水平越高的地區對加工類食品的需求就越高,而且對其質量也有更高要求,這有利于促進食品企業提升食品質量,進而提升食品的出口競爭力。
第三,工業發展水平(fina):采用第二產業增加值與GDP的比值來表示。工業技術越雄厚的地區,越有能力加工出高質量的加工類食品,進而提升食品的出口競爭力。
第四,交通狀況(traff):采用單位面積上的交通里程密度表示(交通總里程=內河航道里程+鐵路營業里程+公路里程)。交通基礎設施越發達的地區,越有利于食品運輸到海外市場進行銷售。
第五,經濟發展水平(city):采用城鎮常住人口與總人口的比值表示。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對高端食品的需求量越大,越有利于高端食品的規模化生產,從而提升食品的整體出口競爭力。
第六,金融發展水平(fina):采用金融機構各項存貸款余額與GDP的比值表示。金融發展水平越高,則食品企業越容易獲得改進生產技術和擴大經營規模所需要的資金,進而提升食品業出口競爭力。
回歸中所使用的變量都為對數值或者比值。由于我國西藏的數據缺失嚴重,回歸數據為2004-2015年期間除我國西藏外的剩余30個省級層次行政單位的面板數據。數據主要來自于中經網數據庫和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各回歸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在表1中。
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利用總體樣本數據進行了面板回歸,結果顯示在表2中。其中表2的(1)(2)列采用固定效應進行回歸,(3)(4)列采用隨機效應方法進行回歸。由于相應的計量檢驗顯示采用固定效應回歸方法更為合理,因而本文的實證分析主要圍繞固定效應結果展開。
從表2第(2)列可以發現,商貿流通業發展水平val的系數為負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這表明從全國總體層面來看,在控制住了其他因素的影響后,商貿流通業的發展不利于食品業出口競爭力的提升。商貿流通業的發展使得其增加了對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服務規模,但是對國內市場的服務量要大一些。此外,隨著金融危機后國外市場需求的疲軟,食品出口企業開始將更多的目標銷售市場定位在我國,而國內商貿流通業的發展使得食品企業生產的各種加工類食品可以較快的運送到各地區市場進行銷售,進而降低對國外市場的依賴,從而減少國外出口量。國內市場需求規模的不斷壯大,以及國內對食品加工質量的要求沒有國外市場那么高,加之便利的國內商貿物流服務,進一步激勵食品企業更多的生產符合國內消費者需求的質量較低的一些食品,進而不利于其食品質量的提升和出口。
控制變量中外商直接投資(fdi)的系數為正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這表明外資的流入增加了食品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外資企業長期在國外市場生產經營,更加了解國外市場政府對食品質量的要求,對國外消費者更喜歡哪些食品也更為清楚,再加上外資企業在國外市場擁有完善的食品銷售渠道,因而他們在我國市場生產的大量食品更具有出口競爭力,更容易出口到海外市場。
交通基礎設施(traff)的系數為負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反而不利于食品出口競爭力的提升。當前沿海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已經較為完善,更多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而中西部地區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使得這些地區的商品更容易銷售到東部地區的消費市場,從而擴大了總體食品的市場銷售量,但是出口量增長幅度較小,從而總體的食品出口占比呈現下降態勢。
我國各個地區間經濟、科技發展水平差異大,不同地區食品消費量和食品加工技術都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商貿流通業發展對不同地區食品出口規模的影響也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本文進一步分地區進行固定效應回歸,回歸結果顯示在表3中,其中表3的(2)(4)(6)列控制住了其他因素對食品出口競爭力的影響。由表3可以發現,首先,在控制住了其他因素的影響后,商貿流通業的發展增強了東部地區食品的出口競爭力,而對中部和西部地區食品出口競爭力的影響都不顯著。其次,東部地區科技實力雄厚,現有的技術條件足以支撐該地區生產出大量符合發達國家要求嚴格的、質量安全的、綠色標準的高質量產品,而且東部地區擁有大量懂得貿易實務的高水平人才,因而商貿流通業的發展可以有效的與東部地區的良好條件結合,進而提升食品的出口競爭力,并將大量食品出口到境外。最后,中部和西部地區由于受到科技技術的制約以及國際商貿人才匱乏的影響,使得其難以在食品業開展出口活動,因而隨著商貿流通業的發展中西部地區將更多的致力于國內市場的開發,而難以有效提升食品業的出口競爭力。
控制變量中工業發展水平(second)的系數在東部和西部地區都為正且顯著,這表明工業發展水平的提升顯著提升了東部和西部地區食品的出口競爭力。工業發展水平的提升使得食品企業可以采用更加先進的技術,進而生產出更多符合發達國家嚴格要求的綠色食品,提升東部和西部地區食品業的出口競爭力。
科技水平(patent)的系數在中部地區為正且顯著,這表明科技水平的提升顯著提升了中部地區食品的出口競爭力,表明中部地區將大量的科學技術創新集中在如何更好地生產出高質量食品。
市場需求規模(sale)的系數在中部地區為正且顯著,而在東部和西部地區都不顯著,這表明市場需求規模的擴大顯著促進了中部地區食品企業出口競爭力的提升。東部地區居民收入水平高,當前居民已經將更多的消費支出用于教育和娛樂活動方面,而對食品的支出規模未有明顯改變,進而對食品業的影響較小,難以對食品出口競爭力產生有效影響。中部地區居民消費支出增長中的相當大一部分用于購買食品,食品市場規模的擴大有利于食品業規模化生產并激勵食品業采用更先進技術生產,進而能夠提升食品出口競爭力。
交通發展水平(traff)的系數在東、中和西部地區都為負且顯著,這表明交通基礎完善后越來越多的食品企業將目標市場轉移到國內,削弱了其開發海外市場的積極性,進而不利于食品業出口競爭力的提升。
結論
本文利用我國省級層面2004-2015年間的數據,就商貿流通業發展對食品業出口競爭力的影響程度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整體上看商貿流通業的發展促進了食品在國內市場的銷售,但不利于食品業出口競爭力的提升;分地區來看,商貿流通業的發展增強了東部地區食品的出口競爭力,而對中部和西部地區食品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則都不顯著。
由于不同地區的商貿流通業發展對食品業出口競爭力的促進作用存在較大的差異,因而本文的研究結果包含的政策意義在不同地區間存在較大的差異。首先,東部地區應當繼續培養高端的貿易實務人才,從而有利于商貿流通業更有效地開展對外貿易活動,進而提升食品的出口競爭力,并將大量食品出口到境外。其次,中西部地區應當大力補齊發展食品出口所必須的各種軟硬件設施,并加大對食品流通體系的監督,有效提升食品的品質。由于出口食品存在較高的質量要求,因而從食品的生產、加工和運輸的各個過程當中都要進行嚴格的質量監督。最后,食品的出口涉及到海關、稅收等各個環節,這必然會影響食品出口過程中的運輸時間,因而各級政府應當在食品出口過程中開辟相應的綠色通道,確保食品高效、安全、有序的通關和交稅。
參考文獻:
1.蘇芳.商貿流通與產業融合耦動—以臨夏州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12(4)
2.李丹,王守偉,臧明伍等.加入WTO后中國食品出口貿易結構分析及展望[J].世界農業,2014(4)
3.宋國宇,杜會永,尚旭東.黑龍江省綠色有機食品出口協調發展評價研究[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2)
4.吳洪.出口風險與預警—基于食品出口的案例分析[J].河南社會科學,2014(5)
5.錢華生.我國食品出口中有關檢驗標準違規的風險問題[J].對外經貿實務,2017(5)
6.王瑛.“一帶一路”與中國對海合會的農產品與食品出口[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4)
7.周星,范燕平.我國食品出口競爭力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8(3)
8.任婷婷.談對外貿易中商貿流通業對經濟運行速度效益的引導作用[J].商業經濟研究,2017(18)
9.衛莉.我國商貿流通渠道發展現狀及優化路徑探究—基于內外貿易一體化視角的考量[J].商業經濟研究,2015(27)
10.葛萬軍.“外轉內”背景下浙江商貿流通業態結構優化與升級[J].商業經濟研究,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