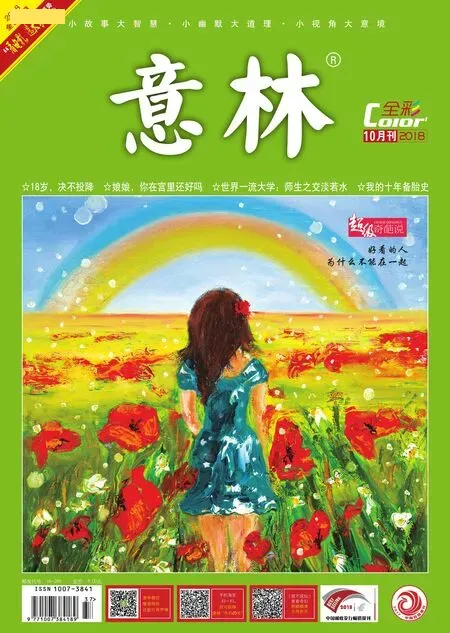世界一流大學:師生之交淡若水
□ 石毓智
高校師生關系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非同小可,關乎人才成長和學術求真。根據我對世界一流大學多年的親身體驗,最理想的師生關系既不是朋友關系,也不是父子關系,而是一種“淡若水”的君子關系:老師教好自己的課,學生學好自己的功課,大家為了求真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國內教育界有一種說法,認為西方的老師和學生的關系像朋友。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我們知道,朋友之間生活上相互關照,感情上經常交流,信息上內部分享,遇到困難則相互幫助。這些都跟世界一流大學的師生關系沾不上邊。
世界一流高校的師生之間是君子之交,互相尊重,相互獨立,大家平等。這首先體現在稱呼上。在美國的大學校園里,師生之間都是直呼其名的,既不用加職稱,又不用稱官銜。可不要小看這個細節,這首先可以排除因等級差別而造成的心理障礙,如此一來,師生之間消除了權威,也沒有面子上的顧忌,大家討論起問題來,就可以獨立地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以求真為最終目的,以觀點本身來判斷是非。
師生完全平等,在世界一流大學的校園,處處都可以體現出來。就以學術講座來說吧,斯坦福大學的學術講座特別多,大家聽講座的熱情也十分高。我從來沒見過一次講座或者學術會議設有嘉賓席,不管學術地位多高,官銜多大,大家都一視同仁,誰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從不拿座次排高低。我幾次遇到這樣的場景:一些資深老教授來晚了,找不到座位,就席地而坐,有些甚至坐在窗臺上。而那些先來有座位的學生也不需要給老教授讓座,這是一種平等文化的體現,不會被認為是一種失禮。
拿到學位畢業了,自己去闖世界,導師頂多給寫一個推薦信,像找工作這種事都是學生自己的事。我博士畢業后,要把自己的畢業論文用英文出版。我的導師伊麗莎白·特勞格特是世界著名的學者,擔任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多家出版社有關叢書的編委,自然在出版界有很多人脈關系。所以我就寫信讓她給推薦出版社,伊麗莎白教授只給列出了幾家出版社的聯系方式,一切都讓我自己去辦。最后,我的書在荷蘭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但是這里邊沒有摻和任何人情,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書稿本身的質量而辦成的。雖然缺少了點人情味兒,但是更利于年輕人的成長,不僅可以早日培養出年輕人的獨立精神,而且也維護了學界的公平氛圍。
學生畢業,當然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在美國這里,研究生畢業,大都是老師請客,因為老師又有一個“新產品”問世了。我在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讀書期間,參加過幾次教授家辦的晚會,其中有些就是導師為了給自己剛剛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慶祝而舉辦的。
學生獲得學位,也不必感謝老師,自然也就沒有“謝師宴”這種現象。反過來,導師可以從學生身上獲得成就感,覺得自己應該破費慶祝一番。
我觀摩了斯坦福大學文理各個學科的本科生課,沒見過哪個老師特別喜歡某些學生,也沒有見過課前課后,某幾個學生纏著某個老師,說東說西,想跟老師建立一種特殊的關系。
此外,我對斯坦福多個系科的課堂進行觀察,發現一個共同現象——老師從來不干涉學生的學習方式和態度,學生遲到、早退、上不上課,老師從來不過問。有些學生上了大半節課才進來,還有些學生中間離開,老師看都不看一眼,更不要說批評了。至于課后如何學習,老師從來不在課堂上講。老師擺明一種態度:學習是你自己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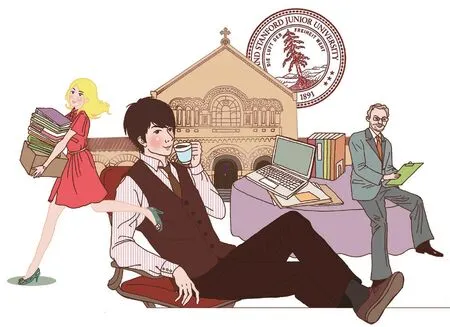
導師家里的事情也不需要學生過問操心。我離開斯坦福不久,聽說伊麗莎白教授提前退休了,原因是她的丈夫在家臥病不起,需要人來照顧。這些事情,她壓根兒沒告訴學生,更沒有麻煩學生。學生們不需要去醫院探望,更不需要去照顧。這種教育和家事分開的文化,使得師生雙方都很輕松,表面看雖然缺乏一些溫情,但是少了很多牢騷抱怨,可以專注自己的事。伊麗莎白教授的丈夫去世后,她又重新回到學術界,十幾年過去了,仍然活躍在學術研究的第一線。
理想的師生關系最終體現在互不抱怨上。我在斯坦福這么多年,印象最深刻的一點是,不管是在公開的場合還是在私下里,從沒有見過任何老師批評或者訓斥學生,也沒有見過任何學生抱怨或者謾罵老師,因為他們都是君子,也視對方為君子。老師和學生各自守住各自的道:老師要盡職盡責,提供最優秀的教學;學生要認真努力,表現出最優秀的學習。
他們的關系單純得如同沒有任何雜質的清水,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提高教育的效率。
- 意林·全彩Color的其它文章
- 知過
- 云舒
- 紅線引(連載二)
- 收入越低,大腦越不靈光
- 昆明到瑯勃拉邦,是一輩子的距離
- 意粉求上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