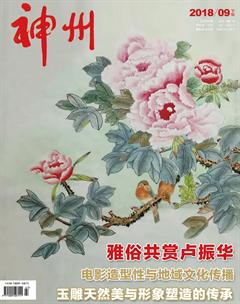芻議建盞的傳承與創新
邱華忠
摘要:建窯建盞,釉色紺黑純正,又富有變化,且斑紋為自然形成。建窯從宋代起到現代,都是以黑釉茶盞馳名海內外。其強烈的藝術特色與豐富的人文內涵使之成為當之無愧的中華文化的產物與藝術瑰寶的標志性代表。本文試圖從建盞的特征及其發展歷程進行考證,從而闡述建盞的傳承與創新。
關鍵詞:建盞;藝術審美;傳承性;創新性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國陶瓷,因它們獨特表現形式及其根植的深厚的文化底蘊,而與國畫藝術一同成就為世界文化藝術中精粹。其中,建盞更是被稱之中國陶瓷文化中的“國之瑰寶”。它具有強烈的藝術特色、豐富的人文內涵、鮮明的時代特色,同時擁有極高的藝術與審美價值。宋人崇尚于自然簡約中,發散無盡之美。建盞就是宋式極簡的最佳印證之一。
每一種藝術都根植于一定社會時期內的歷史與文化,是該時期一切文化現象的總結與代表。具有豐富的人文內涵的建盞藝術同樣直接的體現了它所處時代的文化與審美價值。為了促進當今建盞藝術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就有必要了解和揭示建盞藝術的內在審美特征和發展規律,從它的發展與表現形式入手,結合其所處的歷史時期去綜合考量它,這便是本文的意義所在。
建盞,創燒于晚唐,興于兩宋。在宋朝年間,人們喝的是壓制成餅的研膏茶,因其建盞器型和質地適合點茶,其低調而變幻莫測的釉色又適應宋人審美,于是挾龍鳳團茶的威名獲得了從宋徽宗到朝廷百官的喜愛,上行下效,名動一時,建盞將黑釉茶盞推至宋代茶器的最鼎峰。宋徽宗在《大觀茶論》中說到斗茶所用茶盞,直指斗茶須用“盞色青黑、玉毫條達”的建盞,卻只字未提宋代五大名窯及其他窯口。由此可見,宋徽宗在當時已經將建盞作為斗茶第一茶盞,并親自為其代言。甚至被日本茶人傳回日本,成為日本國寶!目前,日本官方認定的國寶級文物中,瓷器只有14件,有8件是中國瓷器,8件中有4件是宋代建盞,含3件曜變盞,1件油滴盞。此外,英國、美國等國的世界級博物館也均有收藏建窯建盞。兩宋時期,建窯最長的龍窯達135.6米,窯寬1-2.35米。依山而建,頭尾高差28.65米。堪稱世界之最。有學者研究稱一窯可達10萬件。可見當時裝窯是何等繁忙熱鬧,出窯又是何等壯觀。
建盞算是中國陶瓷中第一個被專用做茶杯的。《中國陶瓷史》 《大觀茶論》 《飲流齋說瓷》等古籍均有中記載。一般來說建盞的外壁都是施半釉,以避免在燒窯中釉面熔化粘在窯板上;由于釉在高溫中是膠水狀的熔化狀態,經常掛釉現象,俗稱“釉淚”、“釉滴珠”。這是建盞的特點之一。眾所周知,建盞是從古至今燒制難度最大的瓷器之一,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胎釉中含鐵元素的氧化物比較多,胎土吸釉度一般,并且相比其他用作燒瓷的土來說,收縮率更大。所以建盞從古至今難以燒出特別大型的作品,也難以燒出特別復雜的器形。由于要求的窯溫很高,又要使用強還原氛圍,所以燒成過程的不確定性很強。這點即使是在21世紀的今天,雖然很多高端產品采用很多現代化的科技手段,雖有改善,但是也難有大幅提升。古代由于燒制條件所限,建盞一般都是套匣缽(主要為了防止直接接觸燃料的煙或者落灰)在木柴窯中燒制的,其制作工藝,燒成技術要求相當嚴格。
建盞,到了元代就戛然而止了,這樣就失傳了有800多年,到20世紀70年代前后才逐漸恢復研究與生產,不過在早期品種很單一,始終停留在模仿老器型、缺乏創新的狀態中,對傳統的傳承不應停留在復制古代這一單一的層面上,而應在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只有創新才有生命力,也只有創新才能更好的把建盞藝術傳承下去。當今經濟和技術的一體化以及文化的全球化既給中國傳統手工藝的產業化創造了機遇,也給非物質文化的保護工作帶來了難題。許多有著悠久歷史的傳統工藝種類慘遭市場淘汰而面臨消亡。在近百年里,技藝失傳或瀕臨失傳的傳統工藝種類難以計數,如何保護好面臨技藝失傳或瀕臨失傳的傳統工藝品種,是目前相關部門應該重視的一個問題。其實,古往今來的絕大多數藝術行為都不純然是非功利的,今天人們在博物館里看到的古代的藝術杰作,通常都誕生于普通人的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之中。今天被視為傳世佳作的珍品都曾是人們的日用器物,傳統工藝美術需要煥發生機,需要在符合當代人的生活理想、反映當代人的審美情趣。既要保留傳統技藝,又要有清新的時代氣息,建盞不應該只有情懷價值,而應當在現代的社會結構中實現創造性的文化轉換,即要大膽的融入當代的知識、信仰、技術、道德以及藝術情調,體現時代精神,這樣才能更好的傳承和發揚。
所以在建盞創作中首先要觀念創新,就是要在繼承建窯制作工藝的基礎上,樹立新的創作觀念,要用新的觀念,新的思維去進行建盞的創新工作,還要進行工藝方面的創新,在繼承提煉古代建窯制作工藝的基礎上,大膽創造新的工藝,另外還要進行設計方面的創新,就是要大膽創新設計,努力創作更加精美具有民族風格的符合現代審美的新作品,以滿足社會和人民的需要。我創作的建盞作品<<瑚璉>>創作靈感來源于傳統文化中瑚璉儒商鼻祖子貢,他是孔子的學生,孔子稱贊子貢是“瑚璉”之器。撇口“瑚璉”盞,彰顯寬容大度之氣,又以其穩重不失絢麗、低調不失高雅的玄秘兼容;以其在光影下的閃耀的彩色光芒,特立于建盞的潮頭。瑚璉者,飾美玉之器也,在廟堂中,與鼎配合使用,是“大器”、“重器”。這件作品是在我的另一件金獎作品“盞中蓮”的基礎上研制而成,此作品經過無數次調整窯爐的溫度曲線,摸索流程工藝;經過多次揣摩,上百次百折不撓的試驗,最終研制成功。“瑚璉”是建窯撇口建盞,它繼承了古代瑚璉器皿的尊貴、華美,斑紋美麗燦爛,燈光下更是色彩斑斕、光彩奪目,盞底猶如盛放蓮花的花盆,散發著溫潤優雅的尊貴之美,滲透著清晰高貴的氣質。此作品的創新點更在于其內壁摸起來也有凹凸感,打破了建盞的傳統工藝,這也是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嘗試進行創新的其中一件作品。廈門金磚會晤期間,“瑚璉”代表建陽建盞成功入選廈門市博物館舉辦的藝術中國(廈門)國際交流展,獲國內外人士盛贊。更加堅定了我在作品創作中走創新之路的信念。
要做到工藝與實用相結合,對傳統工藝再創造,以現代的審美理念對傳統文化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煉和運用,實用性的追求能給予建盞更豐富的表現形式,所謂實用即是美,在創新過程中還要注重發揮建盞的收藏作用,建盞本身檔次比較高,再注入高超的手工制作技藝和個性化的設計,使得建盞作品具有更高的藝術價值。
參考文獻:
[1]李達.建盞鑒賞[J].收藏家,2007(04):4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