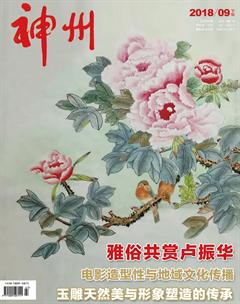一戰期間英國民眾對拒服兵役者的態度
莊芹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拒服兵役者獲得了《兵役法案》賦予的兵役豁免權。然而這種法律上的豁免并不能消弭英國民眾對拒服兵役者的敵意。隨著戰爭的持續,民眾對拒服兵役者的態度由最初的平靜變為普遍的憤怒。民眾的態度勢必會影響法庭的審判和政府的行為,而這些都加重了拒服兵役者的負擔。
關鍵詞:一戰;英國民眾;拒服兵役者;態度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人們用“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來形容那些因為宗教或道德等良知原因拒絕服兵役的人。實際上,由于拒服兵役者群體的復雜性,他們在職業、年齡、甚至“良知原因”(包括宗教、道德和政治良知)上各不相同,準確界定這一群體是非常困難的。筆者認為,歷史學家約翰·雷(John Rae)對拒服兵役者的定義是較為準確的,即“那些良知理由的真實性得到法庭證實,以及那些沒有向法庭申請或者申請理由未獲法庭認可但仍以良知理由拒絕服兵役的人”。這一定義基本涵蓋了所有的拒服兵役者。截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符合這一定義的拒服兵役者人數不過16500人左右,相比近500萬的征兵總數,拒服兵役者數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微小的。
出于歷史傳統和現實政治的考慮,在1916年的《兵役法案》中,阿斯奎斯政府為拒服兵役者提供了可以免除兵役的“良知條款”——“任何出于良知原因拒絕服兵役的人,可以依照本法案向地方法庭申請兵役豁免”。雖然法案措辭存在模糊之嫌,但與其他國家的相關條款相比,英國的良知條款對拒服兵役者是非常慷慨的。拒服兵役者可以以宗教、政治和道德理由申請豁免兵役,允許法庭授予拒服兵役者不參與戰斗、替代服役、絕對豁免三種豁免形式。然而這種寬容只是法律層面上的,民眾的不友好態度影響了法案的實際執行。
一、民眾對拒服兵役者由平靜轉為憤怒
戰爭初期,英國社會對這場戰爭懷有普遍的樂觀情緒。雖然報紙上偶爾會出現攻擊拒服兵役者的報道,但民眾對此的反映還是比較平靜的。這種平靜可能是出于對引以為傲的志愿兵傳統的自信,或是民眾認為這些所謂拒服兵役者只是些暫時未被說服,他們遲早會去為戰爭服務的。
隨著戰爭的惡化,軍隊兵源嚴重不足,戰爭的樂觀態度一掃而光,民眾對拒服兵役者的態度由平靜轉為憤怒,而拒服兵役者的做法則是火上澆油。《兵役法案》通過后,拒服兵役者不僅沒有按照英國民眾的預想欣然接受軍隊中的非戰斗服役,反而聯合起來成立了“反征兵聯合會”,公開號召拒絕服役。顯然,這傷害了有親人和朋友服役的英國人的感情,民眾的情緒徹底被激怒
民眾的憤怒首先體現在法庭對拒服兵役者的審判上。法庭成員在審判中會使用類似“無賴”、“懶鬼”、“惡棍”這樣侮辱性言語。一些知識分子例如羅素、蕭伯納、韋伯等對此非常不滿,但是知識分子的同情并不能改變普通民眾的態度。1916年3月到5月,《泰晤士報》連續刊登民眾批評拒服兵役者的信件,一位讀者認為,拒服兵役者的這種“和平、進步和生命屬于我們,死亡屬于你們”的理論是不公平的,一名圣公會牧師說:“沒有哪一個正直的公民會容忍這些毫無用處的神經質怪人。”民眾的態度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法庭成員的判斷。
民眾的憤怒還更為直接地體現在集會場所。1916年4月,當反征兵聯合會成員試圖通過集會宣傳和平主義觀點時,等待他們的是大批情緒激動的群眾。集會現場幾乎失控,憤怒的群眾不顧警察的阻攔沖向拒服兵役者,他們手持各式簡陋武器攻擊他們。在這一問題上,即使是受人尊敬的羅素也不能幸免。當倫敦的教堂邀請羅素去做和平演講時,一些激進的民眾闖進教堂,與參加演講的人爆發了沖突。在沖突過程中,羅素本人遭到一名手持木板的婦人的攻擊。所有拒服兵役者的衣服在離開教堂時都被扯爛,憤怒的民眾燒毀了教堂的布道壇。
民眾明確而激烈的態度勢必會影響政府的行為。倫敦教育委員要求已經申請兵役豁免的教師在一個月內離職,公立學校不得聘用拒服兵役的教師;豁免兵役的公務員的工資按最低工資或者臨時工工資計算,無權享有定期加薪和養老金;政府對不服從法庭判決的拒服兵役者施以嚴酷的苦役監禁。盡管政府聲稱這些政策并非迫于民眾壓力,但民意對英國這樣一個議會制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民眾情緒的短暫緩和與再度惡化
隨著戰爭形勢和國內政治的變化,民眾對拒服兵役者的態度并非一成不變:每當軍方或監獄出現虐待拒服兵役者的丑聞時,部分民眾對拒服兵役者的態度會發生一段時間的緩和;而一旦戰爭形勢惡化或者拒服兵役者暴動,民眾對拒服兵役者的憤怒和不滿又會持續很長時間。1917年,由于厭戰情緒蔓延加上監獄爆發多起虐待拒服兵役者的事件,民眾對拒服兵役者態度較為寬容。
1917年7月,著名拒服兵役者史蒂芬·霍布豪斯的母親瑪格麗特·霍布豪斯撰寫了《向凱撒上訴:拒服兵役者的情況》的小冊子。書中,瑪格麗特以一名母親的身份講述拒服兵役者的故事,要求政府釋放監獄中的拒服兵役者。8月,《泰晤士報》罕見的對這本冊子發表了帶有同情色彩的評論。霍布豪斯夫人利用這本書暫時改變了民眾的態度,英國社會出現了自《兵役法案》通過以來時間最長的對拒服兵役者較為寬容的社會環境。
然而,這種緩和的情緒并沒有維持到戰爭結束。1918年春,英國在歐戰戰場上出現嚴重的軍事失利,不斷惡化的戰爭形勢使得公眾和政府重新恢復了對拒服兵役者的強硬態度。英國各地持續爆發民眾與拒服兵役者的沖突,雙方的緊張關系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后的一段時間。一戰期間,英國只有350人獲得完全的兵役豁免,近2000名拒服兵役者被強征入伍,約1400名拒服兵役者被監禁。
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民眾對拒服兵役者的敵意,我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那些支持戰爭的普通人,他們的親人在戰場上陣亡,他們有充分的理由表達對拒服兵役者的憤怒”。即使今天我們也不能否認,宗教或道德上的良知信仰與公民的兵役義務之間存在著基本矛盾,當國家面臨戰爭,尤其是防衛戰爭時,是尊重個人信仰還是履行公民職責?這不僅煎熬著拒服兵役者的內心,也考驗著國家解決這一問題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