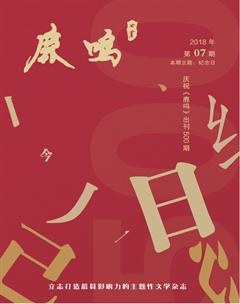呦呦《鹿鳴》
趙劍華
《鹿鳴》五百期了。細細點驗我在《鹿鳴》發表的詩歌作品真還不少,間或還有散文的發表。
包頭,蒙語“包克圖”,漢語的意思是“有鹿的地方”。《詩經》似乎為這座現代化大工業城市鋪就了底色:“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我就生活在這座城市,作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與詩歌為伍的業余作者,近水樓臺,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地利不言而喻,人和在于我和《鹿鳴》的幾任詩歌編輯都是以文結交的朋友,重要的是,1985年7月,在我文學生涯茁壯成長的時期,內蒙古“呦呦詩社”在包頭孕育而生,我作為詩社初創時的核心成員,見證了三十多年來“呦呦詩社”的輝煌與滄桑,而且把文學的初衷堅守到了現在,這對于一個詩人是生命的大幸和終極緣分。
三十多年來,寫了好多詩,也發表了好多詩,出版了幾部詩集。《鹿鳴》始終是我文學生命中值得信賴的“靠山”。相比之下,我在《鹿鳴》發表詩歌很晚,1987年在《鹿鳴》第一次發表詩歌《初戀時我們不懂愛情》。那時,距我的處女作發表已是五年以后,在這之前我已在區內外的省級刊物幾次發詩,我的呦呦詩社的同仁們大多也在《鹿鳴》發表作品,梁粱、白濤、楊挺、童華作為青年才俊,更是重點頭條,組詩迭出。《鹿鳴》有其自身的選稿標準,編輯和作者即使是好朋友,也不一定開面。沒辦法,只好默默地寫作,默默地投稿,重要的是心平氣和地接受一次又一次的退稿(那時我們生活在一個文學的幸福年代,作者一筆一劃的手寫稿,編者諄諄指導,真誠善意的手寫退稿信)。期待與折磨,現在的寫作者已經無法體驗到那種初戀般的痛苦和幸福了。微信時代,五分鐘前的想法,五分鐘后就變成了標準字體,手指一點,朋友圈就為之歡呼雀躍了,如履平地的情緒漫流,才華盡現,情懷遲暮,也許,全民寫作的年代,就是把所有的敬重和敬畏踩在腳下,娛樂至死。我們的文學情懷是那個年代培育成長的,在敬畏中堅守,一直到現在。
呦呦鹿鳴。陰山、黃河、草原、沙漠,加之神山圣土的白云鄂博以及派生出的包鋼特大型鋼鐵稀土聯合企業,詩歌的要件,詩歌的元素,詩歌的硬朗,詩歌的遼闊,無一不融會貫通在我們的血液中。這座城市給了我美好的最有價值的年華,我也把生命的真情和壯麗獻給了鐘情的詩歌。“人生若如初相見”。我從一個幾乎被遮蔽的省級地圖也沒有任何標注的山區煤礦,1978年通過高考上學來到這座城市,接受人生的洗禮,多年后以城里人自居,并深深地熱愛、融入。詩歌給了我自信,也給了我在這座城市顯山露水的平臺。
1988年《鹿鳴》舉辦首屆青年詩歌大獎賽,呦呦詩社的幾十位同仁心里都憋著一股勁,機會來了,誰都不會輕易放過,參賽者把自己認為最有沖擊力的原創作品投稿,每個人都期待滿滿。開始是本市的專家評委評獎,結果還沒有公布就議論紛紛,公平公正受到質疑,大家心里的不服氣公開流露,當時的詩歌編輯張之靜老師決定把所有的參賽作品拿到北京,聘請以著名詩歌評論家謝冕老師為首的專家重新評審。聽到這個消息我心中暗喜,我的參賽作品《流凌時節》在第一次評獎時好像都沒有進入等級獎,在北京評獎隱隱覺得應該有期待的結果。果不其然,夢想成真,九個一等獎中,我位列其中。這是我詩歌創作中的第一個獎,對我太重要了,信心、目標、能力、堅守……這些給力的詞逐一澆筑在我的生命中。所謂人生,其本質的要素就是時間,從那時到現在,三十年過去,參賽者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軌跡,青春的花朵盡情地開,也盡情地落,在過程中成長是一件充實快樂的事,遼闊自然中走過中間的開闊地帶,懵懂也罷,油膩也罷,只隔著小小的時差,經歷詩歌給予的大好年華,也經歷生活的苦辣酸甜,在三十年后呦呦詩社兌現了當時在《章程》中的豪言壯語:“努力構成閃爍在鹿城上空的詩歌星座”。
堅守是一種品質,也是一種崇高。《鹿鳴》從1959年創刊,沉甸甸的五百期,到明年整整一個甲子。在紙媒迅速萎縮的當今,作為一本地市級純文學刊物,堅守顯得彌足珍貴。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期刊的“四小花旦”,磨礪至今,閱盡繁華,無疑也耐得住寂寞,風華過往,成熟的果實更令作者和讀者擁有和珍藏,并且應該給予更廣闊的想象空間,作為純文學應該有一種對人的命運的銘心刻骨的關懷。莫言的第一篇小說是1981年在地區級的雜志《蓮池》上發表的,隨后一連發了四五篇,受到孫犁老先生的贊賞,從此走上文學的道路。現在保定地區的《蓮池》早已干涸,而莫言卻成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第一人。如果沒有《蓮池》這汪水,也許莫言早已枯萎成一個小老頭了。《鹿鳴》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文學繁榮時在全國有不小的勢力范圍,那時能在《鹿鳴》上發東西是一個文學青年多么大的榮幸啊。我想《鹿鳴》一定不會像《蓮池》那樣因經費而窮死,但怕窮而遠離了文學,堅守近六十年的童子功也就漏氣了。這年頭任何堅守、不甘墮落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況且,從金錢的角度講,文學何時富有過?2012年《鹿鳴》改版牽動了這個城市文學的目光。改版后的《鹿鳴》疏朗、大氣、應時、醒目,令人贊嘆,如果細品就要看其內在的品位和文學的真偽了。形式的展示是必要的,但關鍵是否從內心出發,從人的角度去發現理念無法概括的存在,有一種詩意的打量。派克的《永遠的蒸汽機車》讓我找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文學不只是“年味兒”“手藝、營生”之類的描紅小唱,也不是單一的“河流”,熱鬧的“酒吧”所呈現的別樣風景。停留在舊夢中多有糾結,命題之作肯定有無奈的苦境。愉快的書寫多了,溫潤會自然流淌。如果我們背負創新的包袱重了,為創新而創新,動作就會變形,那就舍本逐末了。文學是什么,真是個矯情而糾結的問題。一本很紅的書中有句話記下了:不要因為走得太遠,忘記了我們為什么出發。如果沒有記錯這應該是紀伯倫的“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出發”的演化。文學急不得,想用文學掙錢,不入流的商人想入非非可以,文學中人有此想法就顯得愚蠢了。沉靜、沉著、沉下心來做文學的事,方為正題。“沉”可通“誠”。誠,方不失做人為文的本分。被莫言詼諧為無用的文學起碼是于精神的高潔,心靈的衍化有關。看看陳忠實的《白鹿原》,看看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看看莫言的《紅高粱》《豐乳肥臀》,看看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聽聽北島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文學是什么?愛她的人們心里有數。不是寫出來沾點邊的文字就是文學,文字后面還有不少看不見的功夫,涉獵復雜而多維的視野。文學是一種狀態,是一種境界,其高貴和清潔可用氣節書寫,手高手低明白人看一眼便知。如果寫作的隊伍里迎合之風日盛,人們越來越看不起文人也是應該的。
對文學的堅守,是我們心底默默的祈禱。我們有理由相信,有勇氣亮劍,因為《鹿鳴》和我們共同已經擁有過戈非、紀征民、許淇……我相信他們不會散失到歷史的空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