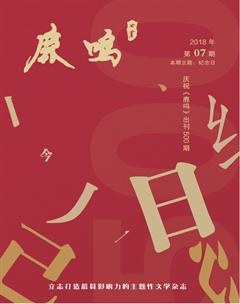不見南來一點風
潘姝
白云鄂博的天空是無云的,就好似魯迅先生筆下的童年玩伴閏土,實則命數之中五行缺土一樣。白云的天,藍得清新爽利,若是利用傳統顏色分類方式來形容,應屬恰在縹與碧之間。就像仙界諸神用畢生法力精心打磨的玻璃鏡面一般,于行進之中的車輛窗口舉目遠眺,與櫻草青蔥的原野各分得畫幅的一半,遠遠相接于草天一線。能判斷車輛是在行進抑或是在暫歇的唯一方式便是不停狂奔而去的勻速轉動的用于風力發電的白色風車和輸電高壓線。倘若掉個書袋,這天地正如明代馮夢龍先生筆下所述:“萬里無云賀六龍,千林不放鳥飛空。地燃石裂江湖沸,不見南來一點風。”
“江山好,立馬白云飛處。”結束一天的奔波,佇立于曠野之上,西望長河落日,嫻靜轉身耐心等候即可迎來月出東方,在天地之間孑然一身,感受時光的流逝。世人都道“八千里路云和月”,似是云必與月同生,只有彩云追月的夜空才是美滿的,其實,那是他沒有機會真正見識過萬里無云的夜空。月圓之夜,當紅月似名門閨秀般四平八穩一步一步走出地平線,只有在周圍沒有任何遮擋物的情況下,你才能清楚地看到玉盤中由暗色火山噴出的玄武巖熔巖流充填的巨大撞擊坑所組成的廣闊“月海”。紅月是天空與原野間唯一的亮色。在周圍沒有任何光污染的環境中,草原的月也顯得比別處的碩大,似是月光真的就鋪成了一條直達九重天的路,也就不難理解草原上為什么形成了那許多與月有關的動人旋律與瑰麗傳說。
一幕曠遠雄渾的沉靜
當紅月升至中天,夜幕才能算作正式降臨草原,只身站立在被皎潔月光暖化的草原,背向草天之間城市夜晚那一抹喧囂的霓虹,身側燃著沸騰的篝火,耳畔傳來悠揚的長調和委婉的馬頭琴聲,張開雙臂,盡情地擁抱初夏夜晚和煦的微風,一絲醉人的草香便攻城掠地般直入胸腔,迎面而來的是草原的開闊與包容,輕輕合上被電子設備整日侵蝕的雙目,涌入思緒的是人作為生物意義上的存在,你會真切地感受到,此時的你和腳下的草,腳畔的石,吃飽喝足悠閑打著響鼻的馬兒,是如此平等,不過是長生天恩賜,容忍你此時此刻有機會和這些草原天生的主宰共處一處。玩兒心濺起漣漪,雙手攏于嘴畔,悠悠學幾聲狼嘯,靜待草原的回音,長生天似乎真就感受到了我發自肺腑的卑微,一陣低吟淺唱般的絲竹與陶土之聲由遠及近淺淺傳入心田,側耳凝神,那是排簫與塤的和鳴,似是奏著一支遠古的曲調,像《蘇武牧羊》,又像《陽關三疊》,細細辨析就是《陽關三疊》,過了初疊,聲音越來越響,進入二疊,眼前開始如電影放映般飛馳而過一幀又一幀的影像,那應是冷兵器時代的刀光劍影、金戈鐵馬,刀劍鏗鏘、鐵馬錚錚之中,一瞬短兵相接的火花飛濺,強烈刺激著我源自靈臺深處的一絲清明。
不禁莞爾,這是長生天在給這個初次踏臨茂明安草原的我,傾訴它輝煌的過去。對,這里是白云鄂博,曾是“但使龍城飛將在”定可阻胡馬于北麓的,荒涼蕭瑟、戰火紛飛的陰山;是“天似穹廬,隆蓋四野;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天地遼闊、水草豐美的陰山下,敕勒川;曾是那“月黑雁飛”單于夜遁之所。這里是陰山北麓不可多得的沃野千里丘陵草原,是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英雄古來必爭之地,若是這里天公不作美,缺水少雨長達一年有余,借著三杯兩盞淡酒,游牧民族的首領一腔熱血賁張便可提韁縱橫,長刀至劈,揮旌南下,越陰山、過平川,一舉拿下河套平原,直逼中原腹地錦繡皇城,與農耕民族一較高下,竟逼的那僅擅陣地戰的中原君主在這無險可依、無石可用的草原不得不數次勞心勞力,就地取材,興土木、壘邊墻……
鴻雁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歷史是個頑皮的孩童,他總會選擇性遺忘一些事。所以風起云涌的茂明安草原,并沒能留下與他的金戈鐵馬濃墨重彩相匹配的明顯標記。但是,長生天不會忘記,它把這里的故事嵌入陰山山脈數以萬計的巖畫,糅進牧人世世代代心口相傳的呼麥長調與英雄傳說。白云鄂博在等待,等待著一個來推門走進他的,懂他的人……直到那一天。
一位擦身而過的青年
這是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的一天。若是我們以今天為起止線,站在上帝視角,回望匆匆向前滾動的歷史車輪,就會發現這一年發生了許多蕩氣回腸的重大事件,對白云鄂博,乃至對整個中國而言,都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但在當時一切卻再正常不過。
這一年,白云鄂博迎來一位與它擦身而過的青年,這位青年的到來,正式將這片孑身自立卻又從不孤寂的草原推上舞臺……
這個青年是一貴州老表,生于世代書香,族內人人皆以讀書為榮的官宦清流之家,年近三十,幾年前,懷著滿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只身北上,考入全國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又歷六年寒窗,半工半讀,兢兢業業,順風順水讀到畢業,留校當了個小助教,快滿一年。可以說正是風華正茂的好時候,但還不完全具備三十而立的資本。
他一直秉承“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志向,可自打入私塾讀經那日起至今二十余年,盡在閉窗苦讀,路卻沒機會多走幾步。最近一年,國內形勢依舊幾多動蕩,好在學界一片清明,不過是在臘梅剛落、玉蘭初放的時候,從膠東沿海傳來學界楷模康先生病逝的消息。也就在此時,機會來了。校方欲和十多位歐洲科學家組成一個西北科考團,他和幾個同事因年富力強、勤奮好學接到了主辦方的橄欖枝,他此前從未有機會走出書齋,禁不住好奇心的驅使,踏出了他今生野外科考的第一步,不過,他當時自然不會知道,這一步使他在青蔥年華便實現了一生之中最為輝煌的成就。他的這一步被一個叫做“白云鄂博”的地方等待了數千年……
戒臺寺那20多棵百年的古丁香剛開一二朵,科考團一行就出發了,坐上剛修通不幾年的京綏鐵路一路直抵包頭鎮,嗯,不對,包頭縣城。包頭縣城北望延綿數百公里的陰山山脈之中那巍巍的大青山,南臨滾滾黃河水,半城山半城水,一直是軍事要塞,古稱“云中郡”,地名之中就詩意滿滿,近幾百年在走西口的晉商辛勤耕耘之下,又成了享譽西北的毛皮集散地。近年來,鐵路運輸與黃河航運交匯,往來客商云集,是標準的水陸碼頭。去年剛剛撤鎮設縣,自有西北小城的一番氣派。這里是科考隊途徑的最后一座城,亦是此行的首發之地。科考隊在這兒有個為期十天的休整,登臨黃河,打點裝備、辦齊糧草、雇傭仆從、聘請有經驗的商賈做領隊,坐擁山西勢及綏遠的百川督軍聞悉此事,亦送來一隊蒙古族青年,以防沿途遭遇馬匪胡子,同時便于和當地的少數民族原住民溝通。
十日期滿,隨著晉商領隊一聲響徹十里的“走嘞”,科考隊正式出發。出發前一日傍晚,從他們走下火車那刻起就一直在刮,接連數日戰斗力極強的白毛風,忽就停了。火紅的晚霞紅透西天,正應了“朝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的好兆頭,同行的蒙古族小警衛說這是長生天的庇佑,此行必定無波無瀾,平平安安。出發當日果然是個難得的好天氣,科考隊群心振奮。
借著好天氣并好心情,科考隊在晉商領隊的引領下沿傳統商道,一路北上,出夾邊溝,過陰山,進入草原。青年第一次踏上草原,便被這里的遼闊雄渾所傾倒,心胸都變得開闊。他知道作為小字輩,在這支由考古學、人類學、生物學、民俗學、天文地質氣象學,各界學術精英前輩云集的隊伍中,除了承擔基本的科考任務外,還得時常打頭陣當先鋒,與領隊溝通,與衛隊協作,休息時幫助仆從裝卸易損的書籍設備,因此很快被勤快的領隊和仆從所喜愛。且自幼崇尚“天人合一”儒學思想的他在目睹崇尚武力的歐洲人使用現代火器以殺戮草原生靈為樂時并不參與,也很快被信奉薩滿教,堅信萬物有靈的蒙古衛隊所接納。甚至經過幾次短暫接觸,還迅速與當地熱情好客的蒙古族土著僧侶、牧民成了朋友。大家都知道這個名叫仲良的青年,就喜歡石頭,所以無論誰看到好玩兒的石頭,都愿意拿給他看看。
轉眼間又一月有余,考察隊在草原中找了片開闊地安營扎寨,之后便兵分三路探路、繪地圖,仲良領到的任務是北線,他精心點了幾個聊得來、工作合拍的晉商領隊和蒙漢兼通的蒙古族侍衛出發了,人帶的不多,大量駱駝都用來拉趁手的書籍和設備。
接下來的幾日,天氣格外晴好,草原已經等這個青年很久了,騰格里也在冥冥之中為這支小分隊漸入草原腹地保駕護航,藍天碧草,天高地闊,青年老成持重的脾性逐漸褪去,原屬于這個青蔥年華的朝氣和熱血反增了不少,他越來越愛在草原之上擇一個正確的方位之后信馬由韁,唯一憂慮的是原野太過遼闊,草天之間乏著一個具有不同等高線特質的地理坐標。
改寫白云鄂博歷史的這一天就在此時悄然而至。晨起,旭日東升,迎著北方繼續行進,隨著馬兒歡快律動的青年,遙遙望著一個被朝陽包了一層金衣的凸起,緩緩躍出地平線,繼而逐漸清晰,那是一個黑金色的山頭,青年喜不自禁地抬手指向山頭“那是”,身側的領隊隨聲應和,“對,那就是白銀博格都,富饒的神山,是方圓幾百里的圣山,是整個茂明安草原的守護神。”其實,白云鄂博地名的由來,并不如筆者薄文開篇所述那般膚淺,“白云博格都”是蒙語的音譯,若是意譯過來便是“富饒的神山”。許是我們的祖先有未卜先知的大智慧,又許是在歷史車輪滾滾行進之中,真的蘊含某種神秘的力量,使白云鄂博在名字中就蘊含了千百年后這里即將發生的故事……這是青年數天以來希之盼之的一個坐標點,對于搞地質的人來說,有山必有石,有石就會有發現。青年越想越興奮,手下的鞭子不禁就加緊幾分,大有朝著圣山策馬奔騰之勢,領隊知道至少還得有幾十里的路,怕青年真就望山跑死了馬,“仲良,莫急,莫急,聽聽故事”,領隊這條路走過多次,早知道那山的故事,但怕自己嘴笨,吸引不了仲良,遂喚來一個能言善語的蒙古族牧人,并囑咐他慢慢說。仲良聞聲略略將行進速度調了回來,他在大本營時和一位常年風餐露宿的考古學家學到一個經驗,好多傳說都不是空穴來風,故事的源頭或許都蘊藏著某些更深層次的科學道理。
那是一個在這片草原流傳了近千年的故事,關乎一個對草原居功至偉的英雄和他的輝煌時代。大意是成吉思汗征伐西夏,手下愛將特古斯追西夏軍至此,敵我雙方戰馬見山均止步不前,而后特古斯的馬鞍、馬鐙、馬掌皆化作一匹金馬騰空而起,至此金馬庇佑著整個茂明安草原。仲良的喜悅和歡騰隨著故事的推進有增無減,豐厚的學識積淀告訴他,這故事背后許就真有些地質學的原理,這山怕是必不一般。
又三日,青年腳步日漸趨緩,晝夜少眠,白天走訪牧民,晚上挑燈夜讀,可是他并沒有在史書上翻到只言片語,只在一個軍事地圖上找到一點蛛絲馬跡。他那時恐怕還沒有清楚意識到這座山已等了他千百萬年。
行至山前只見白云博格都傲然屹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頂天的敖包,五彩的經幡迎風招展,據說茂明安全旗的牧民都會來此祈求長生天庇佑草原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進而,青年終于迎來了他猜測、期盼已久的發現,鐵礦礦沙沿溝散布,愈深愈富,青年許在那一刻篤定,這圣山在幾十年之后,國泰民安之時,必定給草原帶來源源不斷的財富。
之后他負重登山,足跡遍布整座山峰,憑著知識儲備和職業直覺順利找到礦床,摸清成因,采集標本數十箱計,繪圖數以百計,撰寫文字資料數以萬計。他清晰判定,白云鄂博是一個蘊藏豐富且有開采價值的大型鐵礦。
十幾天后,因此次科考還有更長的路要走,青年只好繼續西行,與茂明安草原,與白云鄂博匆匆擦肩。之后三年,青年在戈壁沙漠之中,于荒無人煙之地,跋山涉水,歷盡艱辛,行程數萬里,橫跨蒙寧隴青新五省,對近400萬平方公里區域內的自然地理狀況進行了詳盡考察。
西北科考結束后,白云鄂博依然是他魂牽夢縈的地方,又三年,他撰寫了著名的《綏遠白云鄂博鐵礦報告》,在其中提出內蒙古首次發現大鐵礦。他還設想修鐵路將附近的大青山煤田與之相連,使煤鐵積于一地,并在包頭建設一個鋼鐵基地,進而連通京綏鐵路,對西北的交通、經濟將有重大影響。他還將不遠萬里帶回的珍貴標本贈予同窗,他的同窗亦歷三年寒暑,從標本之中提煉出了珍貴的稀土,并在那個內憂外患的時代預言了,中國——世界稀土大國的地位。
這是白云鄂博最初的故事,也是鋼城包頭最初的故事。
“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云深處。”白云鄂博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文獻之中,就是源于這個青年,他叫丁道衡,發現白云鄂博鐵礦這一年,他28歲。他的同窗叫何作霖,從白云鄂博礦石之中提煉出稀土這一年,他34歲。
白云鄂博終用他上億年的積淀等來了這個與他擦肩而過的青年,草原用他的寬廣與包容引得跨越兩千公里前來的青年實現了他初出茅廬的學術抱負。青年雖然步履匆匆,卻也不遠千里為草原帶來千年未有之福音。許是因第一個將白云鄂博推向歷史與世界舞臺的恰是青年的緣故,使這座塞外小城于孕育之中就自帶了昂然向上的生機和朝氣蓬勃的希望。
一部感天動地的史詩
那一天,“英英白云浮在天,下無根蒂旁無連”。那是一個中華民族處于內憂外患時代之中的一天,那是讀書人與時運的博弈,雖幾經長途跋涉,幾歷冷凳寒窗,除了引來外寇的數度垂涎,論斷依舊是論斷,推演只能是推演,草原還是那個沉靜的草原。茂明安在等待一個風調雨順,白云鄂博在祈禱一個國泰民安。
直至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終被白云鄂博等來,一元復始,百廢待興,一個曾經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國家渴求強盛,一個痛徹地經歷過山河破碎之苦的民族期望復興,他們比任何人都更珍惜來之不易的民族尊嚴,比以往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期盼失之已久的工業復蘇。白云礦區就在這樣一個時期迎來新生。
草原工業的起步階段幾近與共和國同齡,新的一批和丁道衡同一專業領域,甚至和他當年初次來到這片土地時年齡相仿的青年,最先來到這里,他們是這片土地的拓荒者,他們通宵達旦,風餐露宿,甚至與狼共舞,他們繼續丁道衡當年想做但沒有機會做的事,他們一做就是三年又三年,他們殫精竭慮、廢寢忘食地將這項工作做深、做細,他們比丁道衡幸運,因為他們的推演可以不再是推演,草原的一個新局面將在他們推演的基礎之上形成。
之后的幾年間,白云鄂博開始大量迎來一批又一批青年,他們來自天南地北,他們之中有功勛卓著的支邊干部,有浴血奮戰的轉業軍人,有各大礦山的產業工人,也有剛剛走出校門的讀書人,他們曾有過不同的人生經歷,操著不同的口音,他們拜別年邁的父母,揮別摯愛的戀人,來到蒙古高原,他們或走出書齋,或鑄劍為犁,他們將青春的熱血潑灑在白云鄂博的廣袤之上,他們擁有共同的目標,懷著同一個夢,振興鋼鐵工業,改變少數民族地區沒有重工業的歷史。
茂明安是延綿起伏的草原,一望無垠,是一張等待描繪的白紙,對于早已習慣城市喧囂的青年,除了每日熱火朝天的工作,最難排解的就是面對自己內心時的孤寂,他們把自己交給繁忙,將孤寂溶解進廢寢忘食的生產。
白云鄂博是內陸干燥氣候,因受西伯利亞強冷空氣影響,常年低溫少雨,干旱多風,晝夜溫差特別大。春旱風沙大,夏短雨集中,秋爽多日照,冬長天寒冷。一年四季三季風,一季長達四個月。黃沙漫天,風吹石跑,最難忍受的,是對家長的思念。他們把自己交給繁忙,將思念隨風播灑進不分晝夜的建設。
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他們沒有大型機械,只有鐵錘鋼鉗,他們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血肉之軀與激情堅韌。
他們建廠采礦,工業生產逐漸從人工作業被大型機械所取代。同時,也將居住環境由原本的毛氈帳篷變為水泥建筑,生命之源由原本的湖泊降雨變為引黃而入,必由之路由原本的勒勒車轍變成高速公路。草原之上開始有了商圈、學校,繼而有了政治文化中心,家家炊煙縷縷,戶戶雞犬相聞……一座現代化城市在白紙一張天地茫茫的草原之上,由一草一木一磚一石之中,牙牙學語蹣跚學步。
草原亦是仁慈的,她如母親般深愛著這群青年,當他們結束勞作,走出廠區。春天,草長鶯飛,返青的嫩綠,是他們孤單寂寞之時,最溫柔的撫恤。夏天,花開遍地,迎面而來的馬蘭花海,是他們盼來愛人之時,最浪漫的慰藉。秋天,雁過留聲,牧人肥壯的牛羊,是他們擁抱孩童之時,最豐盛的補給。冬天,冰天雪地,油光锃亮的毛皮,是他們思念父母之時,最貼心的獻禮。每一天的日暮降臨,他們和白云鄂博在一起,看著一天天處于變化之中的城市,聽著草原腹地吹來的風,便有一種從心靈深處滿溢而出的不懊悔也不羞恥的平和與喜悅。他們自信而篤定,如白云的天空一般從容。
就這樣,有人來了又走,但更多的還是選擇留在這里。他們在遭遇打擊時,記起夢想的珍貴,在陷入迷茫時,堅信勤奮的力量,他們行在白云,愛在白云,聽從本心,無問西東。他們并不是沒有遇到過外界的誘惑,而是,當誘惑來臨時,他們更能關照自己的初心,更能體味對白云的深情。他們有人是因愛人而來,進而愛上了這片土地。有人是因事業而來,白云給了他們最廣闊的天地。無論他們飛得多高,白云都給他們托底。
無云,草原便感謝風的恩賜,一朵蒲公英吹至草原,它在這里扎根,來年春天,就是一片花海;一群青年吹到草原,他就在這里扎根,明年春來,便是一座新城……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生處有人家。”這段故事不長,因為再多的語言在一個甲子的堅持面前都略顯蒼白。這段故事的主人公,是無數白云鄂博建設者的剪影,他們是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繼的白云鄂博青年,他們來到白云鄂博時大多都剛剛二十出頭,從他們踏上這片土地開始,他們就擁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白云人。
韶光逝,留無計,六十載時光匆匆,數代來到白云的青年用自己未知的青春換來白云已知的今天,一座盛放的新城自草原之上拔地而起,這里成了享譽世界的“稀土之都”。
一個不負韶華的明天
今天,在白云鄂博這片土地上的青年,無論他們來自何方,無論他們因何而來,都漸漸被這片土地特有的城市性格所浸染,他們不但擁有千年前游牧民族的豪放與包容,擁有百年前莘莘學子的開放與嚴謹,擁有六十年來產業工人的熱血與堅韌。他們的視野更廣、“野心”更大、思想更前衛,他們已經不滿足于從深山之中一鏟一鏟地挖掘財富,他們正在講故事翻開新的章節……使初次踏臨這片草原的我亦被他們深深感染。
隨著時光的輪回,白云鄂博草原的支柱產業已經完全更替為以能源工業為中心,積淀上億年,傲視草原生靈的圣山和馬蘭花開遍地的草原,漸進退出并讓步于廠房,為人們對工業的追尋奉獻。視眾生萬物平等的騰格里在目睹著作為新主宰的人類帶給草原百年來的飛速迭代時,應是有滋滋歡騰的喜悅自心底滾滾溢出吧。但,當他同樣目睹著曾沃野千里的草原,隨著現代機械的晝夜運轉似樹木年輪般逐年探入地心時,除了感嘆這是白云載入史籍的深嵌指紋外,心底是否隱約透著一絲淡黑色的疼痛與憂慮。不過,日夜耕耘于這里的青年在任何時刻對這賜予他們財富并默默奉獻的草原都保有足以使人嘆喟的深沉之愛。僅僅為今天的草原創造財富,早已不足以滿足他們,他們把目光放得更遠,他們不能允許在這匹萬里青山畫卷之上人為留下墨跡污點,用自己的心血修復著大地的創痕,他們重新在廢棄的礦坑之上遍植松林,建千頃礦山公園。人道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而他們還曾經的金山銀山又一個綠水青山。不難想象,假以時日,萬畝松林必會枝繁葉茂,樹大根深,綠茵漫天,草長鶯飛,引萬物生息。重歷萬千年時光流轉,幾經日月滄海桑田,這萬畝松林許又是一個金山銀山。
其實,無論白云鄂博一望無垠、無云縹碧的天空多么詩意,他總會伴隨一個致命的弱點。云是大氣中的水蒸氣遇冷液化成的小水滴或凝華而成的小冰晶,頑皮地飄在天空,聚在一處報團取暖的化相,它代表著地球上最為龐大的水循環系統,無云便是無雨。在地理學中有一條看不見、摸不著的線,它將同一時間里降水量相同的各點連在一起,被稱為“等降水量線”。白云鄂博恰在“400米等降水量線”以北。缺水是白云鄂博繞不過的致命弱點。無水之地的人最是愛水,曾幾何時,就是這水引得游牧民族在極度少雨的年份,與中原政權幾經無數次生死較量。白云隨著礦山建設的推進,引入滾滾黃河水解決缺水問題的同時,伴隨產生了大量的工業廢水,這也險些成為白云鄂博又一個繞不過的發展桎梏。但是,今天,新一代的白云青年比這片土地的先民更愛水,他們為這滿腔的愛注入智慧的助推,他們用水動力循環系統實現稀土的管道運輸,大大降低生產成本;他們又將原本的生產廢水凈化成中水,打造草原中難得一見的濕地,六湖連綴,使得豪放粗獷的塞外草原坐擁江面小鎮的溫婉可人……
我自幼居住的地方,隔壁曾是一間大型的工廠,我自幼騎著一輛小童車,扎著兩條麻花辮,搖頭晃腦、哼哧哼哧地騎行在廠內的機械與吊橋之間,因而體內勃發對機械,對大工業生產與生俱來的親近感。在我的記憶中,工廠的環境嘈雜喧囂。空氣中升騰著車床的碰撞聲,偶爾夾雜著工人師傅的高聲談論,滿眼充斥著他們奔波忙碌的身影,腳下生風,往返穿梭,吊橋起落,扳錘叮當,偶爾一不留神就會有機油蹭到花枝招展的新衣服上,很難清洗干凈,短不了一頓打,便是我對工業生產的全部印象。沒來白云之前,我帶著對白云儲量占世界近三分之一的稀土,滿足全世界近八成的稀土消耗的認知,對礦山企業的想象,依舊是深植于記憶之中的熱火朝天,直至有緣來到白云,走進包鋼,帶上安全帽,走進工廠,碩大的廠房之中,數層樓高的機械靜默無聲的勻速運轉,廠區內放眼望去幾近無人,所有大型機械操作幾乎全部由工人利用智能設備數控完成。曾經繁復的人力勞動被大型機械所取代,寧靜之中襯著悠然。
“北望平川。飛步孱顏。人語笑,白云間。”短短數十年,今天的白云青年,他們還草原以青山,他們還草原以綠水,他們還草原以寧靜,以夢為馬,正在努力給草原一個不負韶華的明天。
白云,無云。許是因白云的云化作了白云的礦山、風車與羊群。白云的云滋養了世代生活在這里的牧人、產業工人,亦滋養了在《草原晨曲》中巍然屹立起來的包克圖……
一曲終了,驀然回首。白云的萬千過往皆烙于心間。草香幽幽,白云用一曲《陽關三疊》給初臨茂明安的我講述了一段《鳳凰展翅》的歡歌。
“去從鬧市紅塵去,歸向白云深處歸。”翻閱浩如煙海的史書,任思緒信馬由韁,一座城市聚落的形成需要多長的時間?洛陽是4000余年,長沙是3000余年,桂林是2000余年,拉薩是1000年,就連承德也用了300年,而白云鄂博在這片廣袤的草原之上從無到有,僅僅用了60年。人們常說:“三千年中國史看西安,千年中國史看北京,百年中國史看上海”,其實,若問甲子興盛事,請君還看白云城。60年,短短一個甲子,60位星宿神剛剛輪值了一遍,于白云鄂博山地質年齡遠古代的加里東時期不過是滄海一粟;于千百年的游牧民族爭霸史也無非是白駒過隙。但就是這個再渺小不過的甲子所實現的成就,卻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白云鄂博,從無到有,由弱至強,終于書寫出屬于自己的濃墨與重彩。這是因一代代白云人將生命中最美好的芳華留在這里,白云也以他的寬廣和智慧為下一個甲子的青年搭建好一個實現自我的平臺。
有友人講過一個故事說,當年白云鄂博初創期的條件艱苦,不能刮風,一場大風刮過,可能會刮走幾個大學生,留下來的人都有鐵花一般的奉獻與堅毅,他們把根深深地扎在這里。而今,他們用一個甲子把白云鄂博打造成白云鄂博無云的天空,寬廣縹碧,深深包容吸引著下一個甲子的青年,走進這座城,愛上這座城。再不見南來一點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