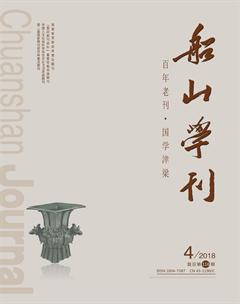中古佛典序跋的佛教史價值芻論
趙紀彬
摘 要: 中古佛典序跋具有重要的佛教史價值,保存了印度早期佛教的因子,勾勒出佛教中國化的變遷、記錄了佛典翻譯與整理的底本,映射出統治者與佛教的關系,折射出佛教的發展程度,反映了佛教的態勢,記載了佛教史實。中古佛典序跋對佛教史的記錄、保存、還原、映射、反映、評判具有鮮明特色,一方面所承載的佛教史具有一定的廣闊性,囊括了域內與域外,佛教史內部的各個要素以及與佛教史相關的多個層面, 另一方面承載佛教史的手段多樣化,既有正面、直接記錄,又有側面折射。
關鍵詞: 中古;佛典序跋;佛教史價值
序跋有時或涉及到書寫對象所形成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其作者的生平事跡,或對其書寫對象的梳理,在此過程中無疑涉及到對歷史的記載。序跋具有濃厚的歷史因子,一方面對歷史的記載具有一定的廣泛性,另一方面對歷史的記載方式多樣化。
作為序跋的一個子類,中古①佛典序跋相應地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只不過它與佛教、佛典、佛事活動等密切相關,融進了大量的佛教史因子:印度早期佛教的某些風貌、佛教中國化變遷的痕跡、佛典翻譯與整理底本的變化、統治者與佛教的關系、佛教的發展程度、佛教的態勢、佛教史實。整體觀之,中古佛典序跋對佛教史的記載方式較為多樣化,所記載的范圍涉及域外與域內兩個層面。
一、保存印度早期佛教的因子
中古佛典序跋盡管在形式上源于我國,其內容則多與佛教、佛典等域外文化有關,其中不乏印度早期佛教。由于記載印度早期佛教的原始佛典,在我國翻譯與整理時被保存下來。漢譯佛典源于對域外佛典的翻譯,二者的內容具有一致性,因此域外佛典中的印度早期佛教成分,在其漢譯本佛典中得以呈現。含有印度早期佛教成分的漢譯本佛典在被書寫序文或跋文時,印度早期佛教的相關內容有時不可避免地被觸及,對中古佛典序跋而言亦是如此。中古佛典序跋描述了佛陀講經的情形,如康孟祥的《佛說興起行經序》描述了如來因舍利弗問及十事宿緣,對眾講授的情形,“如來將五百羅漢,常以月十五日,于中說戒。因舍利弗,問佛十事宿緣。后以十五日時,將本弟子,說訖乃止,如是至九。往所以十問而九答者,以木槍之對人間償之,欲示人宿緣不可逃避故也”[1]2 - 3,此描述與如來講經的情形相一致,因為佛陀在講經時,往往先有一人發問,然后由他為之作答,是他們之間的反復問答。再者,康僧會的《安般守意經序》描述了世尊宣講《安般守意經》時所引起的反響:
世尊初欲說斯經時,大千震動,人天易色,三日安般,無能質者。于是世尊化為兩身,一曰何等,二曰尊主,演于斯義出矣。大士、上人、六雙、十二輩,靡不執行。[2]244
佛陀在為眾講說《安般守意經》時,三界為之震動、天人為之變色,他的身體一分為二,于是大士、上人、六雙、十二輩均尊奉該佛典。世尊講授佛典所引起的反響被視為佛典的流通品,有利于增強佛典的流傳效果,然而其中不乏神異虛構。
中古佛典序跋記載了早期佛典的形成機制。阿難在佛陀的眾多弟子中,記憶力最強、被譽為“多聞第一”,他在小乘佛教的第一次結集大會上背誦出《長阿含》《中阿含》《雜阿含》《增一阿含》《譬喻經》《法句經》等佛教典籍,釋道安的《陰持入經序》對此有所記,“大弟子眾深懼妙法混然廢沒,于是令迦葉集結,阿難所傳,凡三藏焉”[2]248,從中暗示了早期佛典的形成機制。
中古佛典序跋對印度早期佛教的記載盡管微乎其微,其價值卻不容忽視,一方面擴大了中古佛典序跋所書寫的歷史范圍,鑒于多數中古序跋所記載的歷史囿于域內,中古佛典序跋對印度早期佛教的記載則觸及域外歷史,這就擴大了自身所書寫歷史的范圍。另一方面對中古佛教尤其是佛典的狀況有所折射,在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佛典序跋的題寫對象多為域外佛典的漢譯本,這就間接映射出當時域外佛典偏多,編纂于我國的佛典則相對較少的狀況。再者,中古佛典序跋中的印度早期佛教因子的偏微,體現了其題寫者的敘事策略,鑒于國人對印度早期佛教的陌生,其含量不宜過多,從而有利于佛典在我國的傳播。
二、勾勒佛教中國化的變遷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要在我國具有廣泛的受眾則必須實現中國化,借助中國文化來擴大自身影響力。佛教的中國化是一個動態過程,具有階段性差異,這在中古佛典序跋中具有鮮明反映。
佛教傳入之初,依附于我國的神仙方術,附著于黃老思想,趨于道家化,黃老與浮屠并提,道家人物的一些屬性被移植到佛家人物上,使其具有我國神仙的特性,“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覆刃不傷,在污不辱,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也”[3]2,佛陀被賦予“神通”的屬性,此乃其原始形象所未曾有之,是其中國化的產物,此情形在中古佛典序跋中也有所呈現,“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項有日光,飛在殿前”[2]242,在該佛典序文中,佛陀被神仙化。不僅佛陀被神仙化,其他佛家人物也披上了神仙的外衣,以安世高最具代表性,康僧會的《安般守意經序》對此有所記:
有菩薩名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其為人也,博學多識,貫綜神模,七正盈縮;風氣吉兇,山崩地動;針脈諸術,睹色知病;鳥獸鳴啼,無音不照。懷二儀之弘仁,愍黎庶之頑暗,先挑其耳,卻啟其目,欲之視明聽聰也。[2]244
在該佛典序文中,安世高能預知吉兇禍福、觀色知病、識鳥獸鳴啼之音,其博學多識非常人所備,具有神異的特征。此類中古佛典序跋題寫于佛教被道教化的環境之中,是對佛教中國化的真實記載。
佛教的中國化處于動態之中,它隨著我國的社會文化、自身的實力等因素而變化。降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實力有所提升,開始與我國文化互動,其中以與玄學的合流最具代表性。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與般若學互相影響、吸收彼此,時之佛典序跋對此有所記,如道安法師的《鼻奈耶序》曰:“以斯邦人莊老教行,與方等經兼忘相似,故因風易行也。”[1]25般若學因玄學而得以廣泛傳播,玄學則因般若學更加興盛,彰顯出佛教與我國當時社會思潮的融合。
中古尤其是漢末魏晉南北佛典序跋真實勾勒了佛教中國化變遷的歷程,客觀記錄了它的發展脈絡,在勾勒的過程中彰顯出特色。中古佛典序跋對中古各個歷史階段內佛教中國化的勾勒,映射出其題寫者對佛教的關注。中古佛典序跋對佛教中國化的記載,與佛教中國化的同步,由此彰顯出它的與時俱進。中古佛典序跋對佛教中國化的記載具有一定深度,往往超越佛教本身而觸及我國的社會思潮、社會文化以及國人的思維方式等。
三、記錄佛典翻譯與整理的底本
中古尤其是漢末魏晉南北朝佛典序跋記載了佛典翻譯與整理過程中所依的底本,如支敏度的《合首楞嚴經記》曰:“敦煌菩薩支法護手執胡本,口出《首楞嚴三昧》,聶承遠筆受。[2]271由該佛典序文可知,支法護在翻譯與整理《首楞嚴三昧》時以胡本為底本。僧伽提婆在翻譯與整理《阿毗曇心經》時以胡本為底本,鳩摩羅什法師在翻譯與整理佛典時以胡本為底本,釋慧遠的《阿毗曇心序》與釋僧叡的《大品經序》對此分別有所記。道慈法師的《中阿含經序》、未詳作者的《首楞嚴經記后記》與《華嚴經記》等其他中古尤其是漢末魏晉南北朝佛典序跋對佛典翻譯與整理過程中,以胡本為底本的現象也多有記載。整體觀之,隋唐佛典序跋對此問題鮮有論及,可能與當時佛典翻譯與整理活動的成熟狀態有關。
中古尤其是漢末魏晉南北朝佛典序跋對佛典翻譯與整理過程中所依底本的記錄具有一定意義。一方面為認識佛典翻譯與整理提供了重要線索。佛典翻譯與整理是重要的佛事活動之一,所依底本又是該活動中必不可缺的要素之一,中古佛典序跋就此記錄,有利于對該活動的認識。另一方面有利于解決佛教史上的一些問題,如佛教傳入中土的路線。目前學界對佛教傳入我國的路線存有爭議,有學者認為佛教直接由印度傳入我國,另有學者則認為佛教并非直接由印度傳入我國,如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認為“佛教之最初傳入中國的邊疆塔里木盆地一帶”[4]607。中古佛典序跋對佛典在翻譯與整理時,以胡本為底本的記載從側面證明了佛教并非由印度直接傳入中土,而是在西域胡化后傳至,否則佛典在我國翻譯與整理時就不會以胡本為底本,這就為厘清佛教傳入我國的路線問題提供了一定啟示。要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對佛典翻譯與整理過程中所依底本的記錄具有雙重意義,不僅彰顯出它的存史價值,而且為某些歷史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有益啟發。
四、映射統治者與佛教的關系
佛教與歷代統治者的關系較為微妙,在整體上表現為親密或排斥。魏晉南北朝時期,某些統治者推行積極的佛教政策,組織甚至親自參加佛事活動,對佛教極為尊奉,此現象在當時的佛典序跋中多有反映,如陸云公的《御講般若經序》記錄了梁武帝組織宣講《御講般若經序》時的情形,“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曇摩,舍三殿之俗娛,延二坐以問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亦咸發深心,并修凈行,薰戒香以調善,服染衣而就列”[1]12,該佛典序文描述了梁武帝時的皇太子、宣成王及其他王侯宗室在聽講《御講般若經》之前所做的準備工作。聽講者多達千余人,多為當時的官僚士大夫,其中包含諸多域外使者,“凡聽眾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1]12。陸云公的《御講般若經序》對梁武帝蕭衍組織宣講《般若經序》的記載,映射出梁武帝蕭衍對該佛典的尊奉之情,折射出他對佛教的積極態度。漢末魏晉南北朝佛典序跋對統治者尊奉佛事的記錄,在某種程度上暗示出二者的親密關系,是對當時社會的真實反映。
觀漢末魏晉南北朝佛典序跋題寫者群體的構成成份可知,其中不乏當時上層統治者,如姚興、蕭衍、蕭綱等,為佛典題寫序文的行為映射出他們對相關佛典的積極態度,彰顯出他們對佛事的崇奉,映射出他們與佛教的親密關系。
隋唐佛典序跋對統治者與佛教的親密關系也有所映射,武則天所作的《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暗示了她與佛教的親密關系,曰:“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記,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寶雨之文后及”[1]308。武則天的另一篇佛典序文——《大周新翻三藏圣教序》亦表達了她對佛教的崇奉,詳情可參看該佛典序文的相關內容。
隋唐佛典序跋的題寫者群體中不乏統治者,其中以武則天最為典型,她題寫有《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大周新翻三藏圣教序》《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序》,李世民有《三藏圣教序》,李治有《圣記三藏經序》,李隆基有《大寶積經序》,李豫有《大唐新翻密嚴經序》《大唐新翻護國仁王般若經序》,李適有《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序》等。與漢末魏晉南北佛典題寫者群體相比較而言,在隋唐時期,上層統治者的成份明顯增加,此現象在某一層面上折射出佛教與統治者的親密關系得以加強。
要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真實記錄了當時上層統治者與佛教的親密關系,具有多重意義。一方面為把握中古佛教的發展脈絡提供了有益啟發。縱觀漢末魏晉南北朝至隋唐的數百年間,佛教與上層統治者的關系以親密為主流,佛教依附于上層統治者,上層統治者則利用佛教以維護自身的統治,正是二者的互相利用推動了佛教的發展,因此中古佛典序跋就此記錄為準確把握此時期佛教的發展脈絡提供了有益啟示。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古佛典序跋對佛教史的真實記載、在中古的數百年間,親密成為佛教與上層統治者之間關系的主流,因此中古佛典序跋的相關記錄較為真實客觀,符合歷史事實,彰顯出它對歷史的尊重以及真實記錄。中古佛典序跋對上層統治者與佛教親密關系的映射具有連續性,從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在某程度上暗示了其題寫者對佛教發展問題的充分關注,也是對佛教發展規律的總結,充分意識到上層統治者在佛教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五、折射佛教的發展程度
佛典序跋能夠在一定層面上折射出佛教的發展程度,可謂是佛教發展的“晴雨表”,因為它的數量、題寫者群體、題寫章法等要素與佛教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在漢末,佛典序跋在數量上微乎其微,僅有嚴佛調的《沙彌十慧章句序》、康孟詳的《佛說興起行經序》、牟融的《牟子理惑論序》等篇,題寫者群體不夠廣泛、參與者寥寥無幾并且多為域外僧人,章法不夠成熟、篇幅短小、內容相對狹窄、藝術特色也不夠鮮明,這與佛教傳入我國的時間尚短、發展尚不成熟等因素相關。
降至中古時期,佛典序跋的構成要素進一步發展。中古佛典序跋的數量有一定提升,產生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多達178篇、隋唐時期有217篇,佛典序跋數量的增加則意味著佛典數量的上升,而佛典數量的上升又與佛教的深入發展密不可分。中古佛典序跋的題寫者群體進一步擴展,它的題寫者主體由域外僧人逐步轉變為域內僧人,同時它的題寫者階層呈現出擴大的傾向,由先前單一的僧人到最高統治者、官僚士大夫、居士、文人學者等。中古佛典序跋的技法顯著提升,篇幅明顯增加,內容涵蓋面更為廣泛,句式多為四言,講說方式以譬喻為主,形成了鮮明的藝術特色。中古佛典序跋構成要素的發展與此時期佛教的趨于成熟密不可分。
中古佛典序跋對佛教發展程度的折射有時更為細膩,不僅觸及該時期內佛教的整體狀況,而且關注每個階段的具體狀況。總體而論,佛教在中古時期整體上趨于繁盛,具體到每個階段的情形則不盡相同,這一現象在中古佛典序跋中有所體現,從其數量上得以印證。由于魏太武帝推行消極的佛教政策,嚴重阻礙了佛教的發展,相關佛典序跋相應地偏微,題寫于此時的佛典序跋寥寥無幾。南朝的統治者大多推行積極的佛教政策,由此推動了佛教的發展,相關佛典序跋的數量明顯提升。佛典序跋發展的不平衡性在隋唐時期亦有所呈現,如武則天尊崇佛教,無疑有利于佛教的發展,相關佛典序跋相應地豐富;唐武宗推行消極的佛教政策,導致佛教遭到毀滅性打擊,相關佛典序跋隨之偏少。一言以蔽之,中古佛典序跋的數量與佛教的發展程度在一定范圍內呈正相關,前者對后者有一定映射。
中古佛典序跋在一定范圍內折射出佛教的發展程度,因為它的構成要素與后者密切相關。中古佛典序跋以相關佛典為基礎,在數量上與之正相關,而后者又與佛教的發展程度有一定關聯,前者由此與佛教的發展程度建立起間接聯系。中古佛典序跋的題寫群體與佛教的發展程度密不可分,若佛教發展不夠成熟,其影響力相對較弱,佛典序跋的題寫群體相應薄弱。中古佛典序跋的題寫章法與佛教的發展程度存在間接關聯。佛教的深入發展必將對佛典的章法產生一定影響,這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古佛典序跋的題寫者,因為他們在題寫序跋時必先誦閱相關佛典,無形中為之浸染,中古佛典序跋的章法由此與佛教的發展程度建立起間接關聯。中古佛典序跋對當時之佛教發展程度的折射,是其存史價值的升華。
六、反映佛教的態勢
何謂佛教的態勢,即佛教在某一時期內的發展走向。佛教自傳入中土,它的態勢表現在哪些方面?湯用彤先生認為“自漢以來,佛教之大事,一為禪法,安世高譯之最多,道安注釋之甚勤。一為《般若》,支讖、竺叔蘭譯大小品,安公研講之最久”[5]136,由此而知禪法與般若成為當時佛教的主流態勢。
何謂禪法,今人唐思鵬認為“所觀境 (五欲、五蓋,甚或一切諸法),專注一趣,審諦觀察,如實了知其過患相、功德相、雜染相、清凈相、粗苦相、凈妙相等,從而引生神通智慧現行,成辦一切諸應所作,是名為禪”[6]12,禪是一種內心專注的狀態,內心專注而沒有任何意念,進而獲得智慧、成辦一切諸應所作。中古佛典序跋對禪法多有涉及,康僧會的《安般守意經序》闡釋了禪法的內涵,“禪,棄也,棄十三億穢念之意”[2]243,該佛典序文認為禪法則為棄、棄眾穢,唯有如此方能內心專一。
除康僧會的《安般守意經序》之外,其他漢末魏晉南北朝佛典序跋對禪法亦有所論及,如釋慧遠的《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表達了對禪法的贊譽,概括了禪法的特色,指出修習禪法的裨益,闡釋了禪法“五門”中的“四門”,指出佛大先修習禪法的行為。再如,僧叡法師的《關中出禪經序》亦大為贊許禪法,指出禪法的形成途徑,記載了鳩摩羅什法師對禪學典籍的整理。最后,慧觀法師的《修行地不凈觀經序》論及禪智的特色,初學禪法者指明修習途徑。總而言之,中古尤其是漢末魏晉南北朝佛典序跋含有豐富的禪法要素,概述禪法的要義及特色、指出修習的裨益及途徑、記載與禪法相關典籍的編纂,由此映射出禪法在我國佛教界廣泛盛行的態勢,從而推動對我國佛教態勢的認識。
何謂般若,它是般若波羅蜜多的略稱,是大乘佛教中的佛、菩薩所具備的一種智慧,它既是大乘佛教修行所要達到的目的,又是觀察一切事物的準則。般若類佛經大約產生于印度案達羅王朝中葉(約1世紀中葉),其中《小品般若》和《大品般若》在龍樹時代(2或3世紀)已經開始流行,所謂“大品”“小品”是指兩部《船若經》在篇幅上有大小長短之分,中心內容則基本相同。《小品般若經》在中土先后經過七次漢譯:東漢竺佛朔譯的《道行經》一卷,吳國康僧會譯的《吳品經》五卷,吳國支謙譯的《大明度無極經》四卷,西晉竺法護譯的《新道行經》十卷,東晉祗多蜜譯的《大智度經》四卷,前秦曇摩埤與竺佛念合譯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五卷,后秦鳩摩羅什法師譯的《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大品般若經》在我國漢譯的時間相對較晚,先后產生三個譯本:西晉竺法護譯的《光贊般若波羅蜜經》十五卷,西晉無羅叉與竺叔蘭合譯的《放光般若波羅蜜經》三十卷,后秦鳩摩羅什法師與僧睿法師等合譯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四十卷。觀上述可知,般若類佛典在中土先后經過多次的翻譯與整理,流傳廣泛。
中古尤其漢末魏晉南北朝佛典序跋廣泛涉及般若學,從而映射出當時佛教態勢的另一個層面。對般若多有贊譽,如釋僧叡的《小品經序》稱頌《般若波羅蜜經》是菩薩成佛的最佳途徑,“《般若波羅蜜經》者,窮理盡性之格言,菩薩成佛之弘軌也”[2]297。再如,支道林的《大小品對比要抄序》對般若也大為贊譽,“夫《般若波羅蜜》者,眾妙之淵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來之照功”[2]298。再者,為般若類佛典書寫對象的序跋極為豐富,僧叡法師有三篇,除上文所提及的《小品經序》外、還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序》及《大品經序》,道安法師的《道行般若經序》及《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 慧遠法師的《大智論抄序》,智昕法師的《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序》,蕭衍的《注解大品序》,法虔法師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后記》等,由此彰顯出中古佛典序跋對般若的廣泛關注。
由上可知,中古尤其是漢末魏晉南北朝佛典序跋對禪法及般若均有廣泛涉及,從中反映出中古佛教的態勢,因而具有多個層面的價值。一方面為認識中古佛教的整體風貌提供了一定幫助。佛教態勢實際上是佛教主流形態及其整體風貌的一個構成層面,是某一階段內佛教的風向標,佛教在某一階段內的主要發展走勢,中古佛典序跋就此記載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對當時我國佛教整體風貌的認識,體現出它的歷史價值。另一方面有助于對中古佛教發展規律的歸納,由于佛教的發展態勢受多個因素影響、往往呈現出階段性變化,若將中古佛典序跋中的相關記錄加以匯集則構成了佛教的發展脈絡,進而有利于歸納佛教的發展規律,這是它的延伸意義之所在。體現出中古佛典序跋承載佛教歷史手段的多樣化,中古佛典序跋不僅從正面記錄佛教史,而且從側面反映佛教史。要而言之,中古尤其是漢末魏晉南北朝佛典序跋在映射中古佛教發展態勢的過程中,形成鮮明特色,形成自身的歷史價值。
七、記載佛教史實
中古佛典序跋記載了一些與佛教相關的事或人,保存了一些佛教史實,由此被賦予存史功能。中古佛典序跋對當時重要的佛事活動——佛典的漢譯與整理極為關注,詳細記載了該活動的各個要素,如時間、地點、參與者等,力圖真實再現該活動的風貌,如未詳作者的《道行經后記》記載了《道行經》被漢譯與整理的全過程: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陽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薩竺朔佛,時傳言譯者月支菩薩支讖,時待者南陽張少安、南海子碧,勸助者孫和、周提立。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洛陽城西菩薩寺中沙門佛大寫之。 [2]264
該佛典序文記載了《道行經》漢譯與整理的起訖譯時間、漢譯者、漢譯地點、書寫者等要素。曇林法師的《毗耶娑問經譯記》詳細記載了《毗耶娑問經》翻譯與整理的整個過程,其組織者為魏尚書令儀同高公,起因是“愍諸錯習、示其歸則”、即有感《毗耶娑問經》的舛誤,地點是魏尚書令儀同高公之宅,參與者為曇林、瞿曇流支,起譯在“興和四年歲次壬戌,月建在甲,朔次乙丑”,訖譯則在“建初辛巳甲午”,詳情可參看該佛典序跋的相關內容。要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詳細記載了佛典翻譯與整理的過程,由此拓寬了相關史料的保存途徑。
中古佛典序跋記載了佛教史上的某一重大事件。在佛教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個別歷史事件多為中古佛典序跋所記,如關于佛教傳入我國的時間,未詳作者的《四十二章經序》對此有記:
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明日問群臣,此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殆將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至大月支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于今不絕也。[2]242
此記載具有一定歷史價值,為解決佛教傳入中土的時間問題提供了寶貴材料,令人遺憾的是該佛典序文的題寫時間、題寫者信息均未詳記,著名佛教學者湯用彤先生認為它可能早于《牟子理惑論》,“牟子《理惑論》作于漢末,《四十二章經序》出世或更早”[5]18。若湯先生的觀點成立,《牟子理惑論》的“永平求法說”則襲自于《四十二章經序》,故該佛典序文對這一歷史事件的記載具有開創意義,為后人所承襲。反之,若該佛典序文的“永平求法說”則承襲于《牟子理惑論》,由此彰顯出該佛典序文所記內容的真實性,不能因題寫時間及題寫者的模糊性而否定它的歷史價值。
玄奘西游之事為敬播的《大唐西域記序》、李治的《圣記三藏經序》、釋顏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等隋唐佛典序跋所詳細記載,詳情可參看相關佛典序跋內容。
中古佛典序跋不僅記錄佛教史實而且加以評述,在尊重佛教史實的基礎上,對某一問題加以評判,由此成為其題寫者表達觀點的工具,如釋寶唱的《比丘尼傳序》對比丘尼之始這一問題有所論斷,“比丘尼之興,發源于愛道”[7]1,該佛典序文認為比丘尼始于愛道,這一論斷具有一定科學性。在原始佛教僧團中,起初并沒有比丘尼,比丘尼始于佛陀的姨母愛道,《瞿曇彌經》《四分律》卷四十八、《五分律》卷下、《中本起經》卷下、《中阿含經》卷二十八、《大愛道比丘尼經》卷上、《毗尼母經》卷一等佛典均有相關記載。相關情節如下: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阇波提憍曇彌(漢譯愛道)聽佛陀講法后而萌發出家為尼的意念,遂率五百女子至佛陀的住所請求出家,卻遭到拒絕,如此三次均被回絕,她們著“法衣顏色憔悴而不悅”,在佛陀住所外面悲戚。阿難就此詢問佛陀,世尊曰:“今使母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法地清凈梵行大道不得久興盛。”[8]1經過阿難的多次請求,佛陀最終應允此事,前提是她們必須遵守八敬法,愛道答應佛陀的要求而出家為尼,因此釋寶唱的《比丘尼傳序》的論述具有一定可信度。
釋寶唱的《比丘尼傳序》認為我國比丘尼始于凈檢,“像法東流,凈撿為首”[7]1,凈撿之所以更為接近真正意義上的比丘尼,源自她意識到佛教戒律的重要性,因為她在出家之初就進行了受戒。由于當時我國尚無比丘尼,所以凈檢不得不“從和上受十戒”,后來她又上戒壇受戒,因此凈撿是我國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比丘尼。
中古佛典序跋保存了大量的佛教史實,或關注佛教史上的某一類事件、或重點關注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個別事件,并且在此基礎上加以評述,間接體現出保存佛教史的功能,因而具有一定意義。一是保存了佛教史,中古佛典序跋無論是對佛教史實的記載還是評述,均是對佛教史的真實記錄,為后世留下了寶貴史料。二是對佛教史實記錄的完整性,中古佛典序跋既記載了佛教史上的某一類事件又關注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個別事件,體現出點與面的結合,做到了宏觀概述與微觀關注的有機統一。三是對佛教史實的客觀評判,中古佛典序跋不僅充當佛教史實的客觀記錄者、亦做裁判者,在尊重佛教史實的基礎上對之加以評判,重在厘清佛教史上的一些問題,為相關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參考。要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對佛教史實做到尊重、真實記錄、客觀評判,是彌足珍貴的佛教史料。
【 參 考 文 獻 】
[1] 許明.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東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
[2]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
[3] 釋僧祐.弘明集//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社,1990.
[4] 翦伯贊.秦漢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5]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
[6] 唐思鵬.禪法要義.佛教文化,2005(1).
[7] 釋寶唱.比丘尼傳序.北京:中華書局,2006.
[8] 譯者失傳.大愛道比丘尼經//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社,1990.
(編校:馬延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