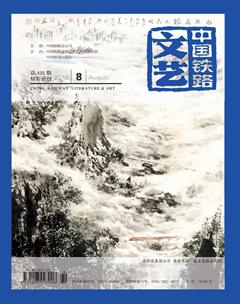關(guān)于門
屈春梅
烏海是礦區(qū),父親是礦工。
因?yàn)橐蠈W(xué),離開水草豐美的姥姥家,去往烏海時(shí),我8歲。初到烏海,我們吃飯用的家當(dāng)都不夠,父母親、我和妹妹,每頓飯,總會有一個(gè)人是用父親的鋁制大飯盒當(dāng)做飯碗,用我未削開的鉛筆當(dāng)筷子。在我的記憶中,這些家當(dāng)我們也堅(jiān)持使用了一段日子。那時(shí)候,似乎總是刮風(fēng),不太密實(shí)的屋里總有打掃不完的灰塵,準(zhǔn)確地說,是“煤”塵。雖然有山,山上卻沒有綠色,父親說:“那底下,全是煤。”而最讓我介意的,要數(shù)“門”了。
我家的門是用礦上廢棄了的木材皮做成的,是單位統(tǒng)一發(fā)的。
那時(shí)候,東西大部分是單位統(tǒng)一發(fā)放。入冬前,單位的家屬們都被通知在某一處寬敞地集中,分土豆、大白菜。一時(shí)間,每家菜窖里的土豆堆得小山一般,院子里的窗臺上、涼房里,成片成片的大白菜。大人們說,那是個(gè)物資匱乏的年代,可在我的小小眼光里,看著那些成堆成片的食物,心里滿是豐收的喜悅,滿是富足的感覺!那時(shí)候沒有集中供暖,家家用的都是土爐子,做飯、取暖用的煤、木材都是集體統(tǒng)一發(fā)的。人們平日吃的肉、糧油也都是“發(fā)”的,憑“發(fā)”的一張蓋章的小票,按票面上規(guī)定的重量,花很少的錢買回來,如果想要繼續(xù)買,就要花高價(jià)。而這個(gè)價(jià),可能也“高”不到哪里去,我印象中,“高價(jià)”白面0.18元1斤。我小小的年紀(jì)里,對錢沒有概念,也沒拿這1毛8分錢當(dāng)回事。記得有一次,母親拿著僅有的1毛錢買菜,而我見到別的孩子手里拿著紫色的“甜玉米稈”在啃,鬧著要吃,無奈,母親只好滿足了我的要求。從小生活在北方的我,實(shí)在沒吃過這個(gè)叫“甘蔗”的東西,說實(shí)話,不如姥姥家的蜂蜜甜,這讓我更思念姥姥家了!還有一次,隨父親買肉,父親在肉食品門市部遇到了熟人,按票面上規(guī)定的斤數(shù)買到了大塊的肥肉,因?yàn)榭梢院某鲇停词故侨獬酝炅耍煤某龅挠统吹牟死锒紩腥庀恪K裕@一大塊肥肉,就意味著我們家那一段時(shí)間的生活會比較“富裕”。父親高興得騎著車子往家趕,當(dāng)他把肉放在母親面前,母親問:“姑娘呢?”父親滿是自豪的臉上立刻滲出汗珠,他飛車返回,幸好我還在原地獨(dú)自玩兒……
我是想說,我家那時(shí)候的門,很像是用這種“發(fā)”的木材簡單釘成的。木材大多是靠近樹皮的部分,所以,這扇門上,滿是蟲洞、樹疤。這個(gè)門,是用三根短的、相對厚實(shí)的橫木和一些豎排著釘在橫木上的木板組成,對于那些釘?shù)貌辉趺唇Y(jié)實(shí)的木板,父親就用粗鐵絲再綁一下,實(shí)在綁不住的,就再找一塊木板,橫著或斜著摞在兩塊豎板上,再釘。這一綁、一釘,不但沒有讓這扇門顯得結(jié)實(shí),反倒更增加了它的破敗感。
書上說,門,也叫做戶或者護(hù),具有護(hù)衛(wèi)、保護(hù)的含義。《釋名》中提道:“戶,護(hù)也,所以謹(jǐn)護(hù)閉塞也。”其實(shí),門,是家與外的分界,是一個(gè)安全的象征。而我家的這扇門,實(shí)在談不上“分界”,更遑論“保護(hù)”,木板間的縫隙,少說都有一指寬,無論推開還是關(guān)上,它都是不情愿、鬧意見似的吱嘎響。甚至有時(shí)我出入得不靈巧,沒有認(rèn)真地用手把門提一下,再推上去,而是用肩頂開時(shí),不知哪顆釘子或哪根鐵絲,便會鉤掛撕扯我的衣服。偶爾使小性踹它一腳,那門不但踹不開,還會因?yàn)橄掳虢潜货邉佣习虢遣粍颖粡椈貋怼T上的鎖也沒有“保險(xiǎn)”,而是一個(gè)掉了漆皮、扭得變了形的鐵皮鎖扣上,掛著一個(gè)任何同等大小的鑰匙都能打開的鎖。據(jù)說,現(xiàn)在有一種“萬能鑰匙”,能開各種鎖,而我家那是“萬能鎖”,能被各種鑰匙開。不過,即使是這樣的門,居住在那里時(shí),也從未被小偷光顧,現(xiàn)在想來,大概是因?yàn)樾⊥祻拈T縫處便對院子里的東西一目了然,失了“神秘”感,也沒有了入室的欲望。
我坐在窄小的院里大聲朗讀,風(fēng)穿過寬闊的門縫,帶著煤塵吹進(jìn)我大張著的嘴,直到現(xiàn)在,我說多了話就會嗓子疼,我都以為是被那時(shí)的門縫的風(fēng)所傷。可是,這不是城市嗎?這就是傳說中的礦區(qū)嗎?這比我之前生活的村里的姥姥家也強(qiáng)不到哪里去呀!
姥姥家的門,是一個(gè)一人高的大膠皮車轱轆。也有可能不是一人高,總之,是比那時(shí)候的我高!
姥爺?shù)鸟R是可以一躍而過的!但是,我難得見它一躍而過的樣子。僅有一次,我把給兔子拔的一籃子草,連帶鏟子、竹籃一起丟了,哭著回來,姥爺帶著我去鐵匠那里重新打鏟子,回來后,為了哄我高興,姥爺打馬從大轱轆門上一躍而過,那種飛起來的感覺,簡直妙極了!
扯遠(yuǎn)了,繼續(xù)說門。姥姥家的“門”,不是用來“推”,而是要“轉(zhuǎn)”動打開的。
姥姥家的外墻是用土坯壘起來的,大概1米多高,中間留一處“豁口”,用“大轱轆”一擋,意為“門”。
日暮時(shí)分,等馬、狗、豬、羊們都回來后,姥爺便轉(zhuǎn)動那個(gè)大膠皮轱轆,擋在墻的豁口處。這個(gè)門的最大用處,大概就是“擋”我了。有力氣的大人們無論是從里還是從外都能“轉(zhuǎn)”動這“扇”門。豬馬狗羊一早就被放出去了,貓兒可以輕易地鉆進(jìn)鉆出、跳上跳下,大人們都干活兒去了,這偌大的院子,就只有我和那個(gè)在我面前大搖大擺踱步又可以隨意出入“門”的貓。現(xiàn)在想起來,姥姥家的貓比我受重視多了!它除了能隨意出入院門,就連家門的右下角,也專門為它打造了一扇“小門”,一枚合頁將同等大小、材質(zhì)的木片同真正的門連在一起。冬天,那里甚至有一塊棉“門簾”。夜里睡得正香時(shí),門上“咔嗒”一聲,那便是貓兒回來了!都說貓是“奸臣”,嫌貧愛富,不戀家、養(yǎng)不住。可姥姥家的貓,更像個(gè)“圣斗士”,它可能好幾天不回來,某一天,便滿身疲憊、灰頭土臉地回來了,那深沉的樣子,像是指揮了一場戰(zhàn)役。在家休整幾天后,又昂首闊步、精神百倍了!很少見它出現(xiàn)在姥姥、姥爺面前,它一般都在我面前趾高氣揚(yáng),可能是因?yàn)榇霾灰粯樱那榫筒灰粯恿税桑⊥蚁啾龋龈鼉?yōu)厚,人家有專屬的“門”!
可能是從那時(shí)起,我幼小的心里,便有了門的“情結(jié)”。
我想,我家的門,應(yīng)該是那種被木匠刨過的、光滑的、嚴(yán)絲合縫的,漆成藍(lán)色,有著油漆的香味,寬窄兩扇。日常出入時(shí),走寬的那扇,只有在運(yùn)送重大貨物時(shí),才把寬窄兩扇同時(shí)打開,每天回家,我就像朵白云投進(jìn)一片藍(lán)天……可是,沒有。我家的門,盡管有著純木的淡香,可距離我理想中的門,還是有距離的。
后來,我見到了各種整齊的、豪華的、開放的、鐵的、柵欄的、木頭的、防盜的門,寺廟里帶著銅釘?shù)那f嚴(yán)的大紅鐵皮門,甚至有棕紅色、香檳色、小木屋上童話般的異形門,可是沒有一扇是規(guī)矩、整齊的藍(lán)色木門!直至后來,丈夫(那時(shí)還是男朋友)帶我初上他家時(shí),站在門前,我渾身的細(xì)胞都驚呆了!光滑厚重的實(shí)木門,漆成藍(lán)色,寬窄兩扇……
——選自呼和浩特局集團(tuán)公司文聯(lián)《鐵馬》2017年秋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