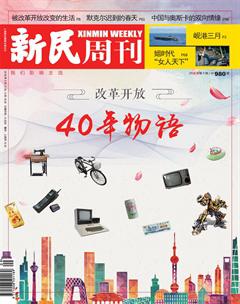暖
王泠一

我挺害怕過年的,主要是害怕小孩子來拜年。這些戴著紅領(lǐng)巾的十齡童,總是帶著各種問題來“請教”我。拒絕,有負(fù)孩子們的信任;回答,則很費(fèi)工夫。如狗年春節(jié),有個(gè)神童就很哲學(xué)地詢問:“有溫度的城市,到底是怎么樣的呢?”在他的樸素概念里,溫度就是團(tuán)聚、團(tuán)圓。至于加班,他不理解。聰慧的他認(rèn)為信息化可以替代假日里的值班。
他覺得智能系統(tǒng)可以解放交警、環(huán)衛(wèi)、醫(yī)院等很多崗位,這些崗位上的叔叔和阿姨就可以在節(jié)日里回家陪伴他們的孩子。我和他說不清楚技術(shù)的局限性,再說“咖啡的熱氣”也替代不了“城市的溫度”,得調(diào)研去、到現(xiàn)場去看看。正好新民周刊的微信公號在提倡向節(jié)日里堅(jiān)守崗位的白衣天使致敬。我和神童就去了他推薦的上海市第八人民醫(yī)院(以下簡稱“八院”)。因神童讀幼兒園時(shí)比較過幾家醫(yī)院,這地處地鐵一號線漕寶路口的八院“打針不疼”,讓他難忘。
和任何醫(yī)院都一樣,除了特急搶救業(yè)務(wù),八院通常就醫(yī)的第一道窗口就是空間特別寬敞的門診部。門診部護(hù)士長沈偉燁,很罕見地接待了不是患者或者是患者家屬的我們。“春節(jié)里好像求醫(yī)的人不是很多嘛?”我看了一番環(huán)境后很自然地發(fā)問。“瞧你說的!過年嘛,第一句祝福的話不就是‘身體健康嗎?然后才是‘恭喜發(fā)財(cái)‘萬事如意。沒有健康,一切都是‘零啊!再說,過年前來求診的大病、急病基本上都控制住了嘛!”快人快語的沈護(hù)士長還一臉的自豪。
神童接著發(fā)問:“那么平時(shí),你們都特別忙嗎?”“很緊張的!經(jīng)常有突發(fā)事件和急救患者;還有轉(zhuǎn)院過來或者醫(yī)聯(lián)體接力的業(yè)務(wù),像流水線一樣、容不得一分鐘的耽誤和任何環(huán)節(jié)上的差錯(cuò)。”沈護(hù)士長答。再了解下來,其實(shí)狗年春節(jié)的相對“就醫(yī)量不飽和”是個(gè)孤案。絕大部分時(shí)間,白衣天使們都是超負(fù)荷運(yùn)轉(zhuǎn)的節(jié)奏;“三班倒”是常態(tài),年輕的醫(yī)護(hù)人員往往就選擇在八院附近租房。
沈偉燁介紹,前一陣上海突降瑞雪,朋友圈里曬的都是詩情畫意,但八院醫(yī)護(hù)人員應(yīng)對老人跌傷、成人滑傷和幼兒感冒,也是聚精會(huì)神、十分辛苦。總有突發(fā)因素來源于患者自身。如今年2月5日,一位八旬老太在辦理住院手續(xù)時(shí),突然不省人事、當(dāng)場昏厥。一場生死時(shí)速就此展開,最終把老太從鬼門關(guān)前搶回。
而看著眼下的平靜,也許是另一場“戰(zhàn)斗”前的蓄力吧。“那么,不是很緊張的時(shí)候,您喜歡什么呢?”神童繼續(xù)探究。“喜歡和姐妹們一起織圍巾,主要是贈(zèng)送給患者。”贈(zèng)送給患者?我們一開始以為自己聽錯(cuò)了。細(xì)細(xì)詢問下來,原來心靈手巧的護(hù)士長們和她們的小姐妹,認(rèn)為心理康復(fù)是門大學(xué)問;而多年的臨床實(shí)踐,又證明親情關(guān)愛極為關(guān)鍵。
然而,不是所有的患者都有親人、親屬,或者是在需要的時(shí)候能夠及時(shí)陪伴在身邊。這個(gè)時(shí)候,白衣天使們就成了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親情守護(hù)神。利用業(yè)余時(shí)間接力編織圍巾和圍脖,就是八院護(hù)士長們的親情康復(fù)創(chuàng)意。接著,我們遇到了“有你真暖”活動(dòng)的主持人、八院的工會(huì)主席李銀萍女士。她具體介紹說“圍巾和圍脖”的贈(zèng)送對象,主要有三類就醫(yī)人員:一是孤兒;二是九十歲以上的老人;三是特別的喜慶當(dāng)事者。這壽星們的禮遇,我很理解。只是“現(xiàn)在還會(huì)有孤兒嗎?”我不解。李銀萍很婉轉(zhuǎn)地說:“作為政協(xié)委員,我調(diào)研過,目前在短時(shí)間內(nèi)還沒有辦法徹底消滅棄嬰現(xiàn)象。”棄嬰,被好心人送來八院時(shí)往往已經(jīng)病重,治療后按規(guī)定移交給福利院;而兒科的醫(yī)生和護(hù)士過年去看望時(shí)則會(huì)送上圍脖。
至于“特別的喜慶”,則是可遇不可求的。八院,大年初一就遇上了。原來有一位叫王晶的媽媽產(chǎn)下了徐匯區(qū)的第一個(gè)“小狗寶寶”;是個(gè)2780克的健碩男孩,和外婆還同一個(gè)屬相。八院黨委書記、兒科專家周建元教授代表全院白衣天使,贈(zèng)送給“小狗寶寶”家的喜慶大紅包賀禮中,就包括了紅紅暖暖的圍巾。至此,神童也恍然大悟——人的情感是智能或者機(jī)器人所不能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