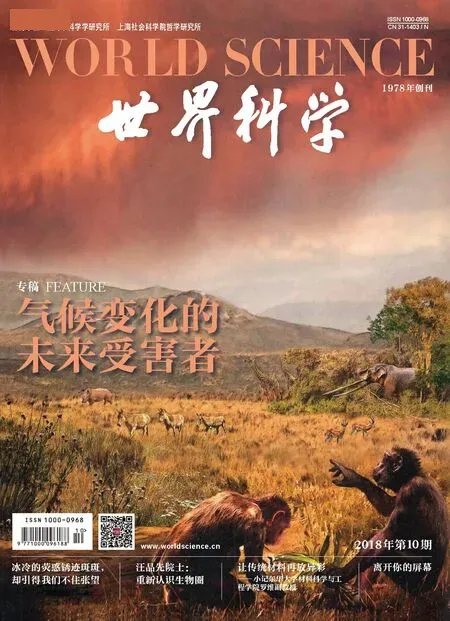離開你的屏幕
編譯 魏劉偉
本文作者尼古拉斯·坦皮奧(Nicholas Tampio)是紐約福德姆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他是《康德哲學的勇氣》(Kantian Courage)和《德勒茲的政治愿景》(Deleuze’s Political Vision)的作者。他最近出版了《共同核心:國家教育標準和對民主的威脅》(Common Core: 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the Threat to Democracy)。
當孩子們親身參與到真實世界當中時,他們學得最好。我們必須抵制基于屏幕學習的觀點。

在農場中動手實踐
農場里,公雞啼叫,吵醒了我和家人,我們在這里度過了一個長長的周末。這里空氣清新,夜空繁星閃爍。太陽從山頂上升起時,我們走近谷倉,那兒的馬、牛、雞、豬、狗和貓輪流爭奪著我們的注意力。我們清洗水槽并將其注滿水,把干草運給牛和馬。孩子們為早餐收集雞蛋。
春天的微風仍然攜著冬天的一絲寒意。當我們踏進水坑,泥漿裹住了靴子;當我們進入一個畜欄,豬撞到我們;當我們去看羊,它們一起蜷縮在一個角落。我們正在了解這個城市的分水嶺,雞蛋和牛肉來自這里,我們還弄清了谷倉在19世紀是如何用木栓而非金屬釘子建造的。我們感受到了谷倉的氣味、梯子的質地、鏟子的硬度、豬呼嚕時的震動、新鮮雞蛋的味道,以及與農民的友誼。
作為一名家長,我很明顯地看到,當孩子們全身心投入到有意義的經歷中時,他們比坐在電腦前學到的東西更多。如果你對此表示懷疑,只需將孩子們在屏幕前觀看某項活動與親自做同樣的活動做一個對比。他們更熱衷于騎馬,而不是觀看一段騎馬的視頻。與其在網絡游戲中玩一個模擬的運動,還不如親身做一項運動。
然而,如今許多有權有勢的人要求孩子們在電腦屏幕前花更多的時間,而不是更少。比爾·蓋茨和馬克·扎克伯格等慈善家為“個人學習”項目貢獻了數百萬美元。“個人學習”一詞描述了孩子們自己在電腦上學習的情況。勞倫·鮑威爾·喬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資助了XQ超級學校項目,該項目致力于運用技術“超越傳統的教學方法”。美國教育部長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等政策制定者稱,個性化學習是“K-12教育領域最有前景的發展之一”。羅德島已經宣布,在全州范圍內對所有公立學校學生推行個性化學習。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機構建議拉美國家建立“規模龐大的、覆蓋數百萬人的電子學習中心”。學校管理人員還宣揚給所有學生(包括幼兒園學生)提供個人電腦的好處。
許多成年人欣賞計算機和互聯網的力量,認為孩子們應該盡快使用電腦和互聯網。然而,屏幕學習取代了其他更有觸感的探索世界的方式。人類用眼睛,也用他們的耳朵、鼻子、嘴巴、皮膚、心臟、手、腳來學習。孩子們花在電腦上的時間越多,花在實地考察、建造模型飛機、休息、看一本書或與老師和朋友交談的時間就越少。21世紀,學校不應該與時俱進地讓孩子們在電腦前花費過多的時間。相反,學校應該為孩子們提供豐富的體驗,讓他們的整個身體都參與進來。
為了更好地理解為什么這么多人接受屏幕學習,我們可以求助于20世紀法國哲學的經典:莫里斯·默勞-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知覺現象學》(1945)。
根據默勞-龐蒂的說法,歐洲哲學一直首先把“看”,而不是把“做”作為理解的一條途徑。柏拉圖、勒內·笛卡爾、約翰·洛克、大衛·休謨、伊曼紐爾·康德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頭腦與世界、主體與客體、思維自我與物質事物之間制造了隔閡。哲學家們都想當然地認為,頭腦是從遠處觀察事物的。當笛卡爾宣布“我思故我在”時,他就在思維和身體之間制造了一個根本的鴻溝。盡管數字媒體有著新穎性,但默勞-龐蒂會爭辯說,西方思想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思維——而不是身體——是思考和學習的場所。
然而根據默勞-龐蒂的說法,“意識”最初不是“我認為”,而是“我可以”。換句話說,人類的思維是從生活經驗中產生的,我們能用身體做的事情深刻影響著哲學家的思維或科學家的發現。他寫道:“整個科學宇宙都是建立在現實世界之上的。”知覺現象學旨在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世界與意識之間的聯系。
哲學家們習慣于說我們“有”一個身體。但正如默勞-龐蒂所指出的:“我不在我的身體之前,我在我的身體里,或者說我是我的身體。”這種簡單的修正對學習有著重要的意義。那么,說“我是我的身體”到底是什么意思?
心靈并不在時間和空間之外。相反,身體思考、感覺、欲望、傷害,它存在一個歷史,并展望未來。默勞-龐蒂發明了“意向弧(intentional arc)”一詞,用來描述意識是如何將我們的過去、我們的未來、我們的人類環境、我們的身體狀況、我們的思想狀況和我們的道德狀況聯系起來的。他讓讀者開始關注這個世界上滲透著我們思想的無數方面。
默勞-龐蒂讓我們不要再相信人類的思想超越了自然界的其余部分的觀點。人類是思考的動物,其思維總是充滿著動物性。正如認知科學家艾倫·賈桑諾夫(Alan Jasanoff)最近在Aeon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解釋的那樣,將大腦獨立于其他內臟之外的這種理想化是一種誤導。學習過程發生在一個具有內在意識的“齒輪”進入世界之時。
以跳舞為例。對笛卡爾來說,頭腦就像木偶操縱者通過拉線來移動木偶一樣移動身體。在這個范例中,要學會跳舞,人們需要記住一系列的步驟。相反,對于默勞-龐蒂來說,學習跳舞的方法是在空間中移動自己的身體:“為了使新舞蹈融入一般運動的特定元素,它必須首先付諸運動。”在身體移動之前,頭腦不會思考并做出有意識的決定;身體會“捕捉”運動。
哲學家們長期以來一直賦予頭腦一種旁觀者的立場,而事實上,身體參與了這個世界。眾所周知,頭腦是“思想的中心”,但“我身體的主要區域被奉獻給行動”,而且“我的身體參與其價值”,這是常識。人們用身體的每一部分來學習、思考和評價,而我們的身體知道一些我們無法用語言完全表達出來的東西。
當然,人們可以反駁說,這可能對如舞蹈這樣的體育活動是適用的,但不適用于所有的智力領域。默勞-龐蒂會回答說:“身體是我們擁有世界的一般手段。”我們學習、思考或知道的一切都來自我們的身體。我們通過在草地上散步、在河邊徒步旅行、沿著湖面劃船,才能欣賞地理學;通過與其他人交談和學習他們的故事,才能欣賞文學;為家庭購買食物使我們相信我們需要學習數學。我們不總是能夠追蹤從經驗到知識、從童年活動到成人洞察力的路徑。但是,我們不可能繞開身體而學習:身體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駐所。
如果人們讓默勞-龐蒂看到學生們在屏幕上學習,他不會感到驚訝。就像許多人能夠抽象思維一樣,學生們可以通過屏幕把自己投射到世界之中。只要孩子們對世界和其他人有一些了解,他們就應該能夠對他們在屏幕上看到的東西有所了解。
盡管如此,默勞-龐蒂給了我們抵制計算機教育趨勢的理由。個性化學習的支持者認為,讓孩子在一天的大部分時間里在電腦上學習是有好處的,包括以自己的節奏完成學習目標的學生。然而,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我們還不清楚為什么當這種經歷從學生們的血肉之軀中被去除的時候,他們為什么仍然會在很長時間內想要這樣做。當孩子們想要跑步、玩耍、畫畫、吃飯、唱歌、比賽和大笑時,老師和家長將不得不使用獎勵、威脅和藥物,讓孩子長時間坐在電腦前。直截了當地說:屏幕學習的倡導者有時似乎忘記了,孩子是想在世界中活動而不是在遠處觀看的小動物。
在農場里,我的孩子們從周圍的動物、樹木、牧場、溪流、星星和其他事物中學習。事情變得比從屏幕中所看到的更真實、更直接。而且我們與農場主人建立良好關系的這種經歷也同樣深刻。農民們會抱著我的孩子,讓他們騎在馬背上,或者在解釋如何把羊從一個畜欄趕到另一個畜欄時不讓他們逃離自己的視線。晚飯前,我們的孩子和他們的孩子在河邊玩得很開心。當我們開車離開農場時,我的小兒子眼里含著淚水,他不想離開他的新朋友。
對于德沃斯這樣的支持者來說,基于計算機的教育使學生們能夠以自己的節奏獨立學習,包括在家里而在非在公立學校中。然而,根據我在農場的經驗,我認為這突出了屏幕學習的一個問題:它不容易使兒童形成人際關系,而這對于良好的教育經驗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馬庫斯·霍姆斯(Marcus Holmes)在他的重要著作《面對面的外交:社會神經科學和國際關系》(2018年)中闡述了證實這種直覺的科學。根據對心靈哲學、認知科學和社會神經科學的研究,霍姆斯認為,身體上的共處對于在人類之間產生信任和同情至關重要。盡管他的研究解決了為什么外交官們堅持在重要討論中要面對面會談這一難題,但他的工作也解釋了為什么人們會覺得見面比通過屏幕交流更讓人滿意。
據霍姆斯的觀點,外交官們堅持親自會見他們的同行。優秀的談判者只有在分享飲料、散步、握手或與同行私下交談時才會有“參與的感覺”。外交官們知道,他們需要擁抱、呼吸同樣的空氣、相互對視,才能取得最佳結果。
霍姆斯利用神經科學解釋了為什么面對面的會議通常會取得更好的結果。諸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神經學家馬爾科·亞科博尼(Marco Iacoboni)這樣的研究人員繪制了“鏡像系統”,使人類能夠理解彼此的意圖。大腦內部存在鏡像神經元,當我們做一個動作或看到另一個人在做這個動作時,這些神經元就會啟動。大眾心理學認為,當我們看到另一個人時,我們會在決定如何反應之前想一想。根據新的“模擬理論”,我們實際上感受到了另一個人的鏡像神經元的感覺,就像這種體驗發生在我們身上一樣。鏡像系統“使得個人之間的高級神經同步了”。
面對面的交流使人們能夠“發現面部表情的細微變化”,并察覺到他人的真誠。神經科學表明,人類在閱讀別人的思想方面做得很好。人們常常互相欺騙,但面對面的相遇有助于發現欺騙。在游戲中,人們在親自玩而不是在網上玩的時候會更加互信。同樣,當人們聚在一起時,會有更大的融洽和“耦合”。簡單地說,面對面的互動是理解意圖的一種無與倫比的機制。
新技術能在多大程度上復制面對面的互動?霍姆斯承認,寫作、打電話或視頻聊天對于許多形式的交流來說都是不錯的,但他堅持認為,人們必須親自見面,才能獲得高度的信任或社會紐帶。霍姆斯援引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話解釋說,人們希望與他人在一起,從而產生情感能量,一種自信、興奮、力量、熱情和主動采取行動的感覺。通過電子郵件或互聯網進行交流,使得人們對在計算機攝像頭前講話的人的肢體語言的閱讀或對正在發生的事情察覺變得更加困難。遠距離溝通并不能像面對面的交流一樣提供身體和情感上的聯系。
我們可以把對社會神經科學的認識從國際關系理論轉向教育理論。把孩子放在屏幕前可以讓他們接觸本來是無法接觸到的信息、認識世界各地的人、玩游戲、閱讀書籍、購買東西等等。但作為一種“互動儀式”,屏幕學習產生的情感能量比那些分享物理空間的教師和學生要少。通過屏幕觀看的學生不會在同等程度上信任或關心他們的老師或學生。當沒有相同的視覺暗示來約束自己的舌頭時,人們可能會更自由地說話,但這也意味著人們更有可能是肆無忌憚的和敵對的。人們對在線教育社區的投資也不會是一樣的。
屏幕不能像在農場參與其生活節奏并與其他人建立聯系那樣提供同樣的情感共鳴。教育工作者應該考慮如何為更多的學生提供這樣的機會,包括那些父母沒有時間和資源規劃這種旅行的學生。
對許多年輕人來說,即使使用得當,數字媒體也會使教育和社區生活變得更糟。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大多數人已經知道這一點。當私立學校做廣告時,場景通常是孩子們做體育活動或和一群朋友在一起。
人們可以合理地反駁說,許多年輕人喜歡待在屏幕前,并通過上網提高效率。這也是一個澳大利亞研究小組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的報告——《數字時代的兒童權利》(2014年)中的說法。研究人員采訪了世界各地的兒童,并用他們的話和例子得出結論:“通過8種不同的語言聆聽兒童的情感傾訴,我們得到一個響亮而清晰的真理:我們需要采取必要步驟,確保所有兒童都能獲得訪問數字媒體的機會。”
該報告描述了兒童在數字媒體上花費時間所帶來的真正好處。孩子們可以獲得信息、獲得更快的服務、以藝術和政治的方式表達自己、享受樂趣,并與世界各地的人建立和保持友誼。該報告也承認數字媒體的危險,包括接觸暴力和色情圖像、過度使用以及數據隱私問題。但它認為,“所描述的風險”被夸大了。該報告認為,如果兒童和他們的照顧者有責任心,他們很可能會從在線訪問中獲益。
然而,在其引人注目的尾聲中,該報告引用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的話,回答了如果數字媒體消失會發生什么的問題。以下是來自不同國家的青少年的一些回應:“我會花更多的時間在戶外做事情,而不是看電視或手機什么的,我會找到更有效率的事情去做”(澳大利亞)。“如果我沒有任何數字媒體,我就會讀故事書”(泰國)。“這不會有任何害處,畢竟我們并沒有徹底地與數字媒體連接起來,我們不受數字媒體的控制”(土耳其)。“這將使人們更有信心與其他人面對面交談,而不是通過互聯網,能夠與他們有著實際的交談”(澳大利亞)。“人們會學會用其他方式生活”(巴西)。“一開始很難習慣,但既然所有人都沒有,那么每個人都會克服它。這樣做也會更好,因為每個人都能說得更多,為了友誼而更加努力地工作”(澳大利亞)。
如果繼續數字化學習的話,孩子們會在屏幕前花費大量的時間。他們將在上學前使用應用程序,在電腦前度過他們的日子,在網上做作業,然后用數字媒體娛樂自己。孩子們正在失去體驗豐富多彩世界的機會。所以讓我們阻止它。
資料來源 A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