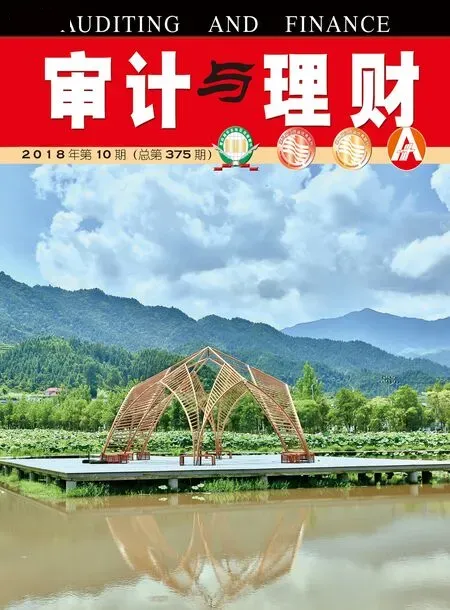基于高管過度自信的財務冗余與績效偏差研究
■袁 文
一、文獻綜述、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設
(一)財務冗余的研究
Meckling(1976)認為冗余會導致代理問題,從而影響企業管理行為、代理成本和所有權結構。同時,冗余資源是未被充分利用的資源,對整個組織無益,是一種低效率的表現。Cyert和March(1963)首次提出組織冗余概念,他們認為組織冗余能夠給企業中的員工或者部門帶來一定程度的滿足感,可以應對和減輕外部環境變化給企業造成的沖擊。
Ang和Straub(1998)認為財務冗余是過剩的財務資源,是組織冗余的一種特定形式,為超過維持組織發展而需要的財務資源的部分。財務冗余作為組織冗余的重要成分,最早由 Myers和 Majluf(1984)提出,由現金冗余(企業提前預留的現金及其等價物)和負債冗余(無風險的負債)構成,反映了企業低風險地滿足資金需求的能力。
(二)高管過度自信的研究
在行為財務學的非理性表現中,過度自信是顯著代表。Baginski et al(1993)研究發現在許多領域,公司高管相比其他人在做決策時更容易“過度自信”。Cooper et al(1988)指出,由于存在過度自信這個非理性行為,人們在做決策的時候,過分相信自己的能力,容易高估成功獲利的機會,低估損失和風險程度,這樣的認知偏差是避免不了的。Russo&Schoemaker(1992)發現,管理者普遍過高估計自身的經營決策能力和企業盈利能力,低估了自身的經營風險,對企業前景抱有樂觀心態。
(三)財務冗余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研究
Jensen(1986)認為隨著財務冗余的增加,管理者往往通過冗余資源為自己的利益服務,而不顧所有者的利益,他們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項目,或者盲目的多元化,最終導致低效率而非提高企業的績效。由此可見,適當的企業財務冗余能夠加強高管的自信,而過度的財務冗余會使高管信心過度膨脹,做出非理性的財務決策從而損害企業的績效。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1。H1: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財務冗余與績效偏差負相關。
(四)過度自信的調節作用分析
Lin et al(2005)選取臺灣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如果公司預期的盈利水平高于公司實際盈利水平,則認為高管存在過度自信,通過實證分析檢驗過度自信與公司投資行為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高管過度自信的企業更容易產生過度投資行為。Roll(1986)是學界公認的首批研究高管過度自信與企業并購關系的人,“狂妄自負假說”就是有他首次提出的,其中解釋了并購活動中大多數并購方高管的非理性行為,即高管的過于自信和驕傲自大,一方面會增加了許多并購活動,另一方面會高估并購項目的利益,因而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給被兼并方,最后導致并購方的整體價值受損。由此,本文提出假設2。H2:高管過度自信是企業財務冗余與企業績效之間的調節變量。相對于理性的高管,過度自信的高管會損害企業的績效。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滬市2009~2017年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考慮到金融類公司的業績指標和一般類公司的不同,無法統一比較,因此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高管過度自信的相關數據來源于Wind金融數據庫;研究樣本中上市公司有關的財務數據來源于CCER數據庫、國泰安數據庫(CSMAR)。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取值按照1%和99%水平進行Winsorize縮尾處理;為克服截面自相關,本文采用企業層面的聚類標準差進行調整。
(二)變量定義
1.財務冗余變量度量。
借鑒畢曉芳和姜寶強(2012)、王艷(2013)等,建立模型1和模型2分別反映現金持有和負債規模的影響因素。根據模型1和模型2對研究樣本進行回歸取得企業現金持有和資產負債率的期望值;現金冗余recash是企業實際現金與期望值之差,見模型3;預留負債能力relev是期望值與企業實際負債率之差,見模型4;財務整體冗余slack為recash和relev兩者之和,見模型5。
以上模型中Cash是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和除以總資產,Lev總負債除以總資產,Lnasset是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值,Grow是公司主營業務收入三年平均增長率,Credit是應付賬款與預收賬款之和與總資產的比例,Repl是運資本減去現金之差與營運資本結構之比,Cashflow是經營性現金凈流量除以總資產,Decashflow是前三年經營現金流量的標準差,Ddiv是虛擬變量股利支付,公司當年支付股利取1,否則為 0,State是虛擬變量,終極控股公司是國有企業的樣本設置為1,否則為0,Fix是固定資產所占比例,Devebit是前三年收入標準差,Year是年限,Ind是行業。
2.績效偏差的度量。
借鑒王菁等(2014),Ep1為歷史績效偏差,是企業未實現組織期望績效時,實際績效與期望績效間的差距(I1(P-A)<0)。以(P-A)計算實際績效與組織期望績效之間的差距,P代表企業實際績效水平,用總資產回報率(ROA)來衡量;A代表根據歷史和社會期望績效的線性組合計算而得期望績效,測量方式借鑒Cyert和 March(1963)、Greve(2003)等,具體計算公式為
其中,HA為公司 i歷史期望績效,用 t-1年公司i的總資產回報率衡量,SA為公司i所在行業內除公司i外其他公司第t年總資產回報率均值,a1代表權重,介于0到1之間,從0開始,每增加0.1進行賦予權重,選取“Log-likelihood”最大值的 a1,本文匯報 a1等于 0.5的檢驗結果。(Pi,t-Ai,t)為實際績效 Pi,t。
借鑒李曉翔和劉春林(2013),Ep2為未來績效偏差,是上一年末對下一年的預測績效減去下一年的期望績效,記為EP2=FP-A。
3.高管過度自信的度量。
在黃蓮琴(2010)對管理者過度自信度量的基礎上,本文對盈余預測有定量描述(披露了盈余預測最大變動幅度)的上市公司,將預測偏差大于或等于50%的視為過度自信樣本。預測偏差的計算公式為:預測偏差=預測年度凈利潤增長率-實際年度凈利潤增長率。其它控制變量Conf 1是高管過度自信程度,公司被歸為高管過度自信樣本組時,其取值1,否則取0,FS是財務冗余,SALEY是銷售費用除以營業收入,AT當總經理兼任董事長時取1,其他為0。TOP是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ASSET是總資產的自然對數,ZZL是總資產增長率,TOP10是前十大流通股東持股比例之和,DLDS是獨立董事比例,DSZCG是董事長持股比例,GGGDZX是高管過度自信。
四、實證檢驗和結果
(一)多元回歸分析
根據表1第2列可知,在以歷史績效偏差為因變量的模型中,財務冗余(Fs)與歷史績效偏差(EP1)在 0.0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負相關,這說明上市公司的財務冗余對企業的績效偏差具有負向影響。控制變量方面,企業規模、資產收益率、總資產周轉率、現金比率、前十大流通股持股比例均會正向影響企業的歷史績效偏差,而高管持股比例會負向影響企業的歷史績效偏差。
根據表1第3列可知,在以未來績效偏差為因變量的模型中,財務冗余(Fs)與未來績效偏差(EP2)在10%的置信水平下顯著正相關,這說明上市公司的財務冗余對企業的未來績效偏差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控制變量方面,企業規模、資產收益率、總資產周轉率、銷售收入增長率、現金比率、前十大流通股持股比例均會負向影響企業的未來績效偏差,而資產負債率會正向影響企業的未來績效偏差。

表1財務冗余對績效偏差的回歸分析結果
(二)調節變量回歸分析結果
根據表2第2列可知,在以歷史績效偏差為因變量的模型中,財務冗余(Fs)與歷史績效偏差(EP1)顯著負相關,高管自信(Gggdzx)與歷史績效偏差(EP1)顯著正相關,財務冗余與高管自信的乘積項(Fs*Gggdzx)與歷史績效偏差(EP1)顯著正相關,這說明高管自信起到了調節效應。控制變量中,企業規模、資產收益率、總資產周轉率、銷售收入率、現金比率與前十大流通股東持股比例均會正向影響企業的歷史績效偏差,而高管持股比例會負向影響企業的歷史績效偏差。
根據表2第3列可知,在以未來績效偏差為因變量的模型中,財務冗余(Fs)與未來績效偏差(EP2)顯著正相關,高管自信(Gggdzx)與未來績效偏差(EP2)顯著正相關,財務冗余與高管自信的乘積項(Fs*Gggdzx)與未來績效偏差(EP2)顯著負相關,這說明高管自信起到了調節效應。控制變量中,企業規模、資產收益率、總資產周轉率、銷售收入率、現金比率與前十大流通股東持股比例均會負向影響企業的未來績效偏差,而資產負債率會正向影響企業的未來績效偏差。

表2高管過度自信調節財務冗余對績效偏差的回歸結果分析

單元格左側數據為回歸系數,括號內為T的統計量,其中 *p<0.1,**p<0.05,***p<0.01。
五、結論
本文從高管過度自信的角度考察了財務冗余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通過文獻梳理及大樣本實證檢驗,本文發現高管過度自信是企業財務冗余和績效偏差之間的調節變量。具體來看,過度自信的高管是通過對企業財務冗余資源在企業融資活動和投資活動的使用方式的不同來影響企業績效的。從總樣本看,高管的過度自信會使企業擁有較高的負債率,在融資活動中優先使用企業財務冗余資源中的現金冗余,當現金冗余不夠不得不對外融資時,過度自信的高管認為市場低估了企業價值,同時為了避免權利被削弱、利益被分享,高管會優先考慮使用債務融資,即企業財務冗余資源中的負債冗余,而不愿進行股權融資。在企業投資活動中,高管的過度自信又因財務冗余情況的不同表現出兩面性:一方面,企業財務冗余資源不足且融資約束較大時,過度自信的高管會放棄一些投資回報率較高的項目,從而造成投資不足進而損害企業績效;另一方面,企業財務冗余資源充足且融資約束較小時,過度自信的高管會盲目投資,甚至投資一些凈現值小于零的項目,使企業出現投資過度,同樣傷害了企業的績效。高管的過度自信容易在企業的高管層蔓延,導致高管過高估計項目的收入和過低估計相關風險,最終造成企業的損失。
本文的研究結果有助于投資者更清晰地識別上市公司的真實水平,做出更合理的投資決策,也為企業高管審查自身過度自信提供了幫助,使企業實現更為合理的科學化管理。同時也為政府今后制定相關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