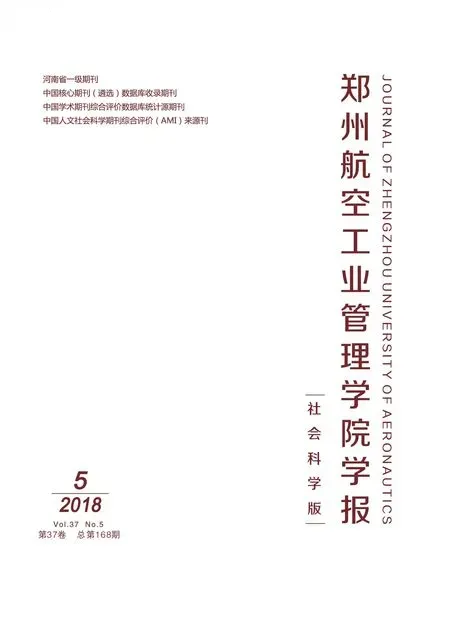宋代河南詩人的群體文化特征
史月梅
(華北水利水電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5)
在宋代詩歌發(fā)展史上,河南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區(qū)域。后周顯德七年(960年),趙匡胤在陳橋驛(位于今河南省新鄉(xiāng)市封丘縣東南)黃袍加身,建立宋朝,定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后改稱為東京,并先后設陪都西京(今河南洛陽)、南京(今河南商丘)。因此,無論在政治、經(jīng)濟,還是文化方面,這對河南本土出生和成長的文人都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筆者據(jù)《全宋詩》[1]統(tǒng)計(按詩題統(tǒng)計,一題計一篇,一題多篇者計為一篇),宋代河南有作品傳世的詩人共401人,詩歌創(chuàng)作總量為13 950首。《全宋詩》共輯錄兩宋詩人9220人,收錄詩作184 977首,從詩人數(shù)量來看,河南詩人約占宋代詩人總數(shù)的4.3%;從作品數(shù)量來看,河南詩人作品約占全宋詩總數(shù)的7.5%。可以看出,無論是詩人隊伍,還是詩作數(shù)量,河南詩人都算得上是宋詩創(chuàng)作的一支生力軍。
從地域文化角度對詩人群體進行整體考察是當前宋詩研究的一個熱點。目前學界關注較多的是以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楊萬里等人為首的江西詩人群和以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為首的四川詩人群,針對宋代河南詩人的研究尚未有學者涉及,可以說河南詩人群體是整個宋代詩學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huán)節(jié)。從整體和群體角度來看,宋代河南詩人的構成情況較為復雜,沒有形成明確統(tǒng)一的創(chuàng)作群體與創(chuàng)作風格。因此,立足于宋代社會文化,從地域分布、身份類別、文儒品格和詩歌風貌等四個角度探討宋代河南詩人的群體文化特征,使這一群體的歷史風貌得以重現(xiàn),從而反映出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與主流心態(tài)。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謂“河南”,是指當今河南省所轄范圍,而“宋代河南詩人”是指在北宋立國至南宋高宗趙構紹興末年(1162年)約200年的時間段里,祖上世代在河南居住的本土詩人,在河南出生并生活至成年的詩人,或自父輩起在河南定居的移民,以及公元1126年“靖康之變”后寓居江南的成年河南詩人,但不包括寓居或經(jīng)過河南的詩人。
一、宋代河南詩人的地域分布
筆者據(jù)《全宋詩》小傳中的詩人籍貫,對宋代河南籍詩人的地域分布統(tǒng)計如下(以當今地名為準,列出宋時地名以供參照):

表1 宋代河南詩人的地域分布

續(xù)表1 宋代河南詩人的地域分布
從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宋代河南詩人地域分布較為集中,開封、洛陽兩個地區(qū)的詩人數(shù)量較多。其中,開封詩人占總數(shù)的36.75%,洛陽詩人占總數(shù)的19.5%,可見宋代河南詩人是以開封、洛陽為詩壇重心。造成如此鮮明的地域反差,這里面既有開封、洛陽的政治文化因素,又有因血緣關系或婚姻關系而形成的家族性因素,也是歷史傳統(tǒng)、地理環(huán)境、宗教意識等諸多因素的綜合反映。
二、宋代河南詩人的身份類別
宋代河南詩人群體的構成情況較為復雜,既有帝王將相、王公貴族,又有文人雅士、野老閨婦以及僧道女妓。他們有的本身即為河南籍,又在河南成長生活,如魏野、石延年、蘇舜欽等人;有的是因宋室南渡而僑居江南的河南人,如陳與義、曾幾、朱敦儒等人。為了方便考察,筆者從河南詩人的身份地位、社會角色等入手,將他們的身份類別歸納為以下幾種:
一是帝王宗室。宋代十八位帝王,除北宋英宗、欽宗,南宋光宗、恭帝、端宗,末帝趙昺等在位時間較短外,其余12位帝王皆有詩作傳世,宗室姻戚有詩作傳世的共44人。
二是官吏政客。北宋時期共有宰相91人,其中河南籍宰相7人(呂蒙正、向敏中、馮拯、賈昌朝、富弼、韓琦、韓縝),且多由進士釋褐。《宋史·選舉志一》載:“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為盛。”[2]卷一五五,3603“天圣初,宋興六十有二載,天下乂安。時取才唯進士、諸科為最廣,名卿巨公,皆繇此選,而仁宗亦向用之,登上第者不數(shù)年,輒赫然顯貴矣。”[2]卷一五五,3603宋代科舉制度的完備、科舉規(guī)模的擴大、朝廷官職的增設,使得文人與國家政權的關系極為密切,讀書應舉、入仕為官,是他們實現(xiàn)自身價值的重要途徑。這一點,可在宋代河南詩人的政治身份上得到佐證,兩宋290名河南籍官員中,由進士入仕的多達171人。
三是隱逸之士。宋代實行的是“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政治,文人受到廣泛重用,但仍有不少文人選擇了歸隱山林。在宋代河南詩人當中,共有隱士16人。他們多追求品茗飲酒、吟詩作文的林泉生活,不為仕祿所動,如《宋史·魏野傳》載:“(野)及長,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huán)繞,旁對云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游,嘯詠終日。”[2]卷四五七,13430鄭景望《蒙齋筆談》載:“(楊)樸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駭。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樸,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樸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3]隱士多因高行節(jié)義受到官府賞賜或官員資助,如邵雍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隱居洛陽,“初至洛,蓬蓽環(huán)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zhí)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2]卷四二七,12726。魏野生前曾被宋真宗召,不赴,他去世后,真宗下詔旌揚,曰:“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賻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恤,二稅外免其差徭。”[2]卷四五七,13430
四是僧人道士。宋朝雖然大興文教,但建國之初僧道數(shù)量并不多,“國初,兩京、諸州僧尼六萬七千四百三人,歲度千人。平諸國后,籍數(shù)彌廣,江、浙、福建尤多”[4]325。后來自真宗朝起大興道教,佛教亦為之興盛,僧道數(shù)量有所增長,但河南籍僧道依然很少,能詩的僧道更少,共有11人(僧9人,道2人)。這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道士陳摶,宋太宗召見他多次,并賜號“希夷先生”,下詔賜錢為其修建華山云臺觀。
五是僅知其爵里,生平履歷今已無考者(30人)。他們身份各異,其詩作多見于筆記小說或他人的詩文。如張資,仁宗天圣汴京(今河南開封)貴官子,事見《醉翁談錄》壬集卷一《紅綃密約張生負李氏娘》,《歲時廣記》卷一二引《蕙畝拾英集·鴛鴦燈傳》。再如盧氏,許州(今河南許昌)人,能做墨竹,梅堯臣有《墨竹》詩題之。又如胡文媛,汴(今河南開封)妓,后歸河東茹魁,事見《宋詩紀事》卷九七引《續(xù)青瑣高議》。
三、宋代河南詩人的文儒品格
宋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重要轉(zhuǎn)型期,其社會文化特征與前代社會迥然不同。經(jīng)過唐宋之際的社會變動,尤其是宋代科舉制度的變革、發(fā)展,“大大鼓勵了士人參政的積極性,激發(fā)了他們中的優(yōu)秀分子關心現(xiàn)實的熱情和責任感”[5]16。士大夫的角色定位與心態(tài)的極大變化,讓其“既治學、修身,獨善其身,也憂國憂民,兼善天下,他們的文化品格是內(nèi)圣與外王的統(tǒng)一”[5]18。這種融匯政治、學術與文學的政治取向和文化情懷,正是“文儒”型知識階層所表現(xiàn)出的新氣象與新格局。
宋代河南詩人的“文儒品格”,既有當時士大夫的共性,又表現(xiàn)出了自己的個性。首先,宋代河南詩人的儒學素質(zhì)多體現(xiàn)在其德行敦厚的人生品格上。如三朝宰相韓琦,史稱其“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2]卷三一二,10221。他曾抵御西夏,參與慶歷新政,也曾被貶在外十幾年,但始終堅持守道耿介的忠諒之心,可以說這“代表了宋代士流中居主導地位的正氣”。再如另一位三朝宰相富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2]卷三一三,10249。韓琦言:“竊見富弼大節(jié)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慢書于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敵。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屈強敵,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2]卷一二,229葉清臣言:“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2]卷二九五,9849能以嚴格的道德規(guī)范約束自己,重操守,尚廉潔,其儒學素質(zhì)與文學素養(yǎng)相融合,從而形成了一種博通的文儒特征。其次,北宋中期,士大夫注重名節(jié)的道德意識很強烈。《宋史·忠義傳序》載:“真、仁之世……于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jié)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2]卷四四六,13149宋代河南詩人在這種道德相尚、名節(jié)相高的士林風習中,亦很注重自身修養(yǎng),追求完美人格,即使身處逆境,也能以一種安貧樂道的精神鼓勵自己。再次,張載提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6]664,既是宋代士大夫的襟懷,也是他們的器識與宏愿。詩人們崇學向善,并在詩作中展現(xiàn)自己的道德取向,彰顯發(fā)自內(nèi)心的名節(jié)情懷。最后,拋開學術義理和人生實踐層面,我們在史籍和詩文中也能看到眾多宋代河南詩人身上的深厚儒學素質(zhì)。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糅合士人精神、時代精神和個人性格特征的“文儒品格”的堅強支撐,宋代河南詩人表現(xiàn)出了經(jīng)世心態(tài)、道德品格與沖淡情懷相結合的氣質(zhì)特性。
四、宋代河南詩人的詩歌風貌
宋代河南詩人的詩歌風格多樣,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細述,茲根據(jù)以上所論詩人的身份類別,各舉代表性作品數(shù)例略做分析,以期從整體和群體性上展現(xiàn)出其詩歌風貌。
宋代帝王多好讀書,亦能詩文。即便武將出身的趙匡胤,其詩作也別有意境,如其《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達,千山萬山如火發(fā)。須臾走向天上來,逐卻殘星卻趕月。”[1]卷一,1語言質(zhì)樸而規(guī)模宏遠。宋太宗喜好詩賦,擅長書法,重視文化,組織修撰《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并開創(chuàng)了升平詩歌,使君臣賞花釣魚賦詩成為宋代詩歌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如其《太平興國七年季冬大雪賜學士》:“輕輕相亞凝如酥,宮樹花裝萬萬株。今賜酒卿時一盞,玉堂閑話道情無。”[1]卷三九,447詩語輕靈自然,便娟婉約。宋真宗好文學,也是一名詩人,其《賜道人鄭隱歸山》詩云:“盡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幾聽松聲。遍游萬壑成嘉遁,偶出千峰耫治平。”[1]卷一○四,1179宋仁宗《賞花釣魚》詩云:“晴旭輝輝苑粃開,氤氳花氣好風來。游絲羒絮縈行仗,墮蕊飄香入酒杯。魚躍文波時撥刺,鶯留深樹久徘徊。青春朝野方無事,故許游觀近侍陪。”[1]卷三五四,4401神宗的《賜秦國大長公主挽詞三首》其一:“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其二:“曉發(fā)城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銷。芳魂飛北渚,那復可為招。”其三:“慶自天源發(fā),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已隔秦。區(qū)區(qū)會稽市,無復獻珠人。”[1]卷一○四三,11957詩語雅麗精致,受到了廣泛贊譽。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三引《臨漢隱居詩話》載:“神宗皇帝以天縱圣智,旁工文章。其于詩,雖穆王《黃竹》、漢武《秋風》之詞,皆莫可擬其彷佛也。秦國大長公主薨,帝賜挽詩三首曰……噫,豈特帝王,蓋古今詞人無此作也。”[7]徽宗詩書畫兼善,亦能詩,如其《題芙蓉錦雞圖》詩云:“秋勁拒霜盛,峨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鳧鹥。”[1]卷一四九五,17069南宋諸帝能詩者亦多,如寧宗的《山市晴嵐》詩:“藪澤趁虛人,崇朝宿雨晴。蒼崖林影動,老木日華明。野店收煙濕,溪橋流水聲。青簾何處是,仿佛聽雞鳴。”[1]卷二八三五,33758寧宗《漁村夕照》詩:“林表墮金鴉,孤村三兩家。晴光明浦溆,紅影帶蒹葭。傍舍收魚網(wǎng),隔溪橫釣槎。炊煙未篝火,新月一鉤斜。”[1]卷二八三五,33758度宗《賞春》詩:“珠簾翠幕千門曉,麗日和風萬國春。乍雨乍晴雖莫測,無非天地發(fā)生仁。”[1]卷三六一六,43318詩語均清新明快,繪景如畫。

仕宦南北的河南詩人們除卻對時代氣象和社會盛況的描摹和歌頌,還多喜流連四時節(jié)序,吟詠風花雪月。如李九齡《荊溪夜泊》詩云:“點點漁燈照浪清,水煙疏碧月朧明。小灘驚起鴛鴦處,一雙采蓮船過聲。”[1]卷一八,265筆致散淡,韻致悠長。又如孫何《吳江》詩云:“晚灘如雪起沙鷗,咫尺姑蘇亦勝游。逸勢瀉歸滄海遠,冷聲分作太湖秋。葑田幾處連僧寺,橘岸誰家對驛樓。魯望不存無可語,片帆中夜渡清流。”[1]卷八八,979氣象宏闊,筆致細膩。再如石延年《詠春》詩云:“一氣回元運,恩含萬物深。陰陽造端數(shù),天地發(fā)生心。有信來還逝,無私古到今。和風激遺暢,南轉(zhuǎn)入薰琴。”[1]卷一七六,2000視界宏闊,舒卷自如,而情婉志微,表現(xiàn)出宋詩議論化的特點。
太平盛世之際的隱逸情懷,使詩風從官場的煩喧轉(zhuǎn)向了自然山水的清音麗辭。如魏野《冬日書事》:“一月天不暖,前村到豈能。閑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松色濃經(jīng)雪,溪聲澀帶冰。吟余還默坐,稚子問慵應。”[1]卷七八,896描寫隱居生活的閑適自在。再如趙遹《萬松嶺》:“清溪狹徑小橋東,風入桃花處處同。我為日長無一事,偶然來此聽松風。”[1]卷一四○五,16178從中可見清幽雅秀的隱居情懷。又如朱敦儒《絕句》:“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里住,臥吹銅笛過伊川。”[1]卷一四七八,16881儼然一派逍遙適意的名士風流。
宋室南渡,許多世居中原的詩人流寓江南,憶起汴梁舊都風光,神往昔日繁華流韻,譜寫的則多是一曲曲凄涼幽怨的時代哀歌。如康與之《題徽宗宸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余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1]卷一八六九,20907劉棐《題惠眾院》:“云迷鳥道嶺重重,松竹深藏釋子宮。戎馬不曾來爾界,太平元在亂山中。”[1]卷一九一一,21331王來《富沙》:“忽驚羈旅身,已落富沙灣。江海舊茅屋,遙岑帶潺湲。”[1]卷二○七四,23400趙善應《寧師西閣》:“飄泊南來幾歲寒,追談往事漫心酸。云煙暮隔中原望,歸折梅花忍淚看。”[1]卷二○九九,23702趙善傅《寓居等慈寺感懷》:“欽從王命寄招提,寂寂荒階綠草齊。明月夜深接佛閣,看來不比汴梁時。”[1]卷二○九九,23703孫文昭《往浙西別王龜齡》:“中原回首尚胡塵,世事徒驚日月新。羈旅不堪頻作別,壯懷雖在已甘貧。南來求友傳三益,西去論心有幾人。別后夢魂何處是,祇應來往慎江濱。”[1]卷二○五一,23054面對河山破碎,雖有歸隱茍全之意,但也有收復河山的堅定決心,如岳飛《歸赴行在過上竺寺偶題》:“強胡犯金闕,駐蹕大江南。一帝雙魂杳,孤臣百戰(zhàn)酣。兵威空朔漠,法力仗瞿曇。恢復山河日,捐軀分亦甘。”[1]卷一九三五,21595
通觀宋代河南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無論是在題材的開拓方面,還是在表現(xiàn)手法和藝術風格的多樣化方面,都為宋代詩壇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這其中不乏視野開闊、境界宏大之作,亦有筆力清健、格調(diào)高遠之詩。單就山水景物詩而言,可謂曲盡物態(tài)、體物工細,拓展了詩歌的境界,彰顯了宋詩的精神風骨。但宋代河南詩人在創(chuàng)作上的缺憾又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兩宋詩人的通病,如因襲多而創(chuàng)新少,在一定程度上有著唯理化、議論化傾向,風格上追求典麗規(guī)整,但也不乏清新警譎之句。
在宋代社會文化變遷、詩人交游互動的過程中,詩壇呈現(xiàn)出了一種繁榮多元的詩學面貌。這并非少數(shù)著名詩人活動的結果,而是由眾多詩人共同創(chuàng)造出來的局面;這也不僅是文學自身傳承演變的結果,還與宋代社會文化變遷、士林風貌演變等密切相關。這樣一個龐大的詩人群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宋詩創(chuàng)作的走向,促進了宋詩的發(fā)展成熟,折射出宋王朝的政治變遷和歷史興衰,這是一個不應被忽視的文學群體與文學現(xiàn)象。但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這一詩人群體并沒有受到學界的充分重視。筆者以為,把宋代詩歌的語詞特征、意象特征、抒情特征與地域文化相結合進行研究,對宋代河南詩人群體做一個完整的全景式呈現(xiàn),是非常有意義且非常有必要的。因此,希望通過本文的粗淺見解,能夠拋磚引玉,期待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能夠致力于此項工作,尋繹出該群體所承載的多重文化內(nèi)涵和社會價值,從而反映出兩宋時期河南的獨特文化現(xiàn)象和社會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