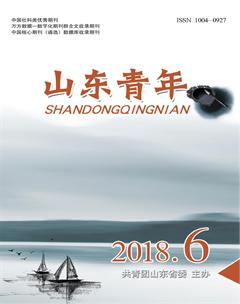正負相關證據的博弈
高維靜
摘 要:
司法作為維護人權的最后一道防線,應該深為公民所信賴。但是近年來發生的冤假錯案,使得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大大下降,對于這個問題很多學者都從冤假錯案的預防機制的角度出發去探討如何去防止錯案的發生,本文提出來不同的觀點,立足于冤假錯案發生的原因,從證據分類的角度,詳細從邏輯模型構建的角度,對有罪和無罪、疑罪證據進行重新分類,分為正相關證據和負相關證據。找出冤假錯案發生是由于證據分類的不清楚以及對于負相關證據的忽視。同時本文分析了幾個典型的冤假錯案中證據問題,以此來印證邏輯模型構建證據分類的可行性,為冤假錯案的預防提出了自己的反思。
關鍵詞:正相關證據;負相關證據;疑罪證據
一、問題的提出
在一起問卷調查中:證據問題出錯對于錯案的形成有沒有重大影響,對于這個問題,絕大多數的被調查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證據方面的錯誤會對錯案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其中認為有很大影響的為1031,占60.1%。認為影響較大的為538,占31.4%。[1]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很多冤假錯案發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證據問題,比如說有證據的偵查、證據的審查等等。
各種冤假錯案發生的原因在于偵查機關對于無罪證據搜集的忽視以及法官對于證據的審查和認定存在傾向性。由于控辯雙方所處于不同的地位,檢察機關掌握著更多的資源,因此獲得更多的可靠證據,所以對檢察機關提出的證據較持肯定態度,對辯護人提出的證據極其容易忽視。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對無罪證據或者疑罪證據的忽視,在何家弘教授所作的調研中得到了證明:在 50 起刑事錯案中,存在“忽視無罪證據”的情形就有 10 起,占 20%,成為僅次于存在“被告人虛假口供”(47 起,占 94%)造成刑事錯案的重要因素之一。[2]
在證據的分類上,我們將有罪證據和無罪證據作為一種分類,但是這種分類有一定的不足,因為在有罪證據和無罪證據之間還有一種疑罪證據,對于疑罪證據沒有做出很妥當的處理,在處理案件過程中很草率的將疑罪證據分到有罪證據中,這樣對于法官形成有罪判決的內心確信有很大的助推作用,冤假錯案的發生也很大一部分程度因為這個分類的混淆。
在刑事案件中,我們搜集到的疑罪證據往往會歸結到有罪證據的分類上,這也為很多學者所混淆疑罪證據和有罪證據的界限。例如在一起縱火案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直接證明整個案件的經過,所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為有罪證據即正相關的證據。但是周圍的可燃物與打火機一起作用發生了危害結果,這個可燃物不能作為有罪證據出現,當我們在案發現場發現可燃物的時候,我們不能據此就認定為縱火案,我們可以猜測有可能發生了縱火案。這樣可燃物就屬于疑罪證據。
雖然在定罪上我們遵從疑罪從無的規則。但是在證據的劃分上我們不能將疑罪證據劃分到任何一個里面,所以在這里提出新的證據分類方法為正相關的證據和負相關的證據分類。,這樣可以解決有罪證據和無罪證據這兩個極端的證據分類。
二、正相關證據和負相關證據的概念分析以及分類的合理性
對于正相關證據的負相關證據的分類,這里以是否能夠證明有罪事實,將證據分為正相關的證據和負相關的證據。
正相關的證據是指能夠單獨證明有罪事實的證據。其與有罪的判決結果之間具有正向相關性,并且其與有罪結果的相關強度很大。
負相關的證據是指不能單獨證明有罪事實的證據,這里包括無罪證據和疑罪證據。無罪證據與有罪的判決結果呈現出負相關關系,不能對有罪結果起到任何正向證明作用,而是通過反證法來反駁有罪判決,而疑罪證據雖然與有罪的事實可能存在一定關聯,但是這種關聯不大,并且這種證據需要與其他證據一起解釋,如果找不到其他證據,我們只能做出無罪判決。
提出這種分類方法,主要是對比有罪證據和無罪證據的分類。之前我們對證據最主要的分類就是有罪證據和無罪證據,這也給我們司法實踐帶來了很多弊端,在搜集證據和認定證據的時候,我們會將證據分類歸納為有罪的證據和無罪的證據,把很多疑罪證據當成有罪證據來對待,沒有注意到證據與證據之間的關聯。很草率的對證據進行分析從而做出有罪判決,這對犯罪嫌疑人是極其不公正的。
提出這種分類的合理性主要基于以下兩點:
(一) 促使偵查人員更多的去發現無罪證據和疑罪證據,更好的發現案件事實,更好的維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
偵查人員的職責為搜查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的證據。在實踐中,偵查人員更多的是搜查有罪的證據。在搜查到一些疑罪證據時,也直接歸為有罪證據,甚至有些時候將一些并沒有聯系的疑罪證據牽強聯系在一起。對于無罪證據更是視而不見,這樣就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這就在根源上形成了冤假錯案發生的契機。這樣的分類可以很好的促使偵查人員擺正自己的偵查方向,做到正相關和負相關證據一同偵查。
(二) 促使審判人員在認定證據的時候綜合考量各種證據,對于疑罪證據、無罪證據和有罪證據放在相同的分量上去考量,避免有所傾向性,做出不公正判決。
大多數的審判中,審判人員看到疑罪證據沒有進行綜合考量直接作為有罪的參考,就如同上述案件,當卷宗中出現可燃物時,審判人員就很有可能粗略的做出縱火罪的有罪判決。這個時候應當進審判人員沒有進行行綜合分析,深入考察,根據疑罪證據來做出有罪判決。在最后一道防線上做出錯誤判決。而正相關證據和負相關證據的分類,可以糾正法官對于疑罪證據的認識偏差,避免出現冤假錯案。同時,對于非法證據排除這一方面,在非法證據語境之下的非法證據應當為涵蓋有罪證據和無罪證據。[3]這里的有罪和無罪證據也是應該為正相關證據和負相關證據。
(三) 正相關證據和負相關證據的邏輯結構構建
對于一個證據是正相關證據還是負相關證據需依賴于于對證據的解釋,對于證據的解釋不能憑空臆想,需要借助于邏輯結構構建。首先一個材料能否作為證據使用,取決于這個材料是否與案件事實具有相關性,即是否能夠起到證明作用。那么對于正相關的證據是能夠對有罪的案件事實起到證明作用的,負相關的證據是不能對有罪事實起到證明作用的。從另一方面看就是這個證據與案件事實相關性的強度,如果證據與相關的有罪案件事實強度越大,我們就可以說它是正相關的證據,證據與相關的無罪、疑罪案件事實強度越大,與有罪事實呈現出負相關性,就為負相關的證據。邏輯構建分析如下:
證據H,有罪案件事實P,強度R,在這里將證據H與有罪案件事實P之間的邏輯推理轉化為因果關系推理。X表示與H一同作用的其他原因。Y表示導致P結果的其他原因。X是若干事件的合取:
X=X1∧ X2… ∧ Xn
強度R的值:
R<0
R=0
0 R=1 (1)正相關證據的邏輯構建 H是E的充分原因 公式H∨ Y←→ E,公式(2)表示H是E的充分條件原因,有H一定有E,無H也未必無E,這里強度R=1,這里證據H一定為得出有罪判決必不可少的條件,所以相關強度達到最高。這種證據我們成為正相關的證據。[4] (2) 負相關證據的邏輯構建 1、 疑罪證據的邏輯構建 H是E的貢獻原因 公式 (H∧ X)∨ Y←→ E公式(1)表示(H∧ X)∨ Y是E的充分且必要條件,這里的強度為0 2、無罪證據的邏輯構建 當證據H和P之間的相關證明強度為R<0時,即對于有罪事實起到反證明作用,我們則稱之為無罪證據。 3、 無相關性證據的邏輯構建 當證據H與P之間的相關證明強度為R=0時,此證據H由于其與案件實施沒有關聯性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四) 正負相關證據在案件中的具體運用以及給我們的反思 杜培武案件中證據疑點 (1)雖然證實當晚18-19 點、21 點以后杜培武在本單位,但沒有證據證實當晚19-21 點杜培武在哪,既沒有證據證明杜在單位也沒有證據證實杜出了單位,但辦案人員卻以認定杜培武有作案時間,這是極其荒謬的,偵查人員如果證實杜培武19-21在哪,這就是一個負相關證據中的無罪證據,那么就可以排除其作案時間,但是偵查人員卻因為沒有對證據進行實質性審查。 (2) 根據杜培武的供述手槍仍在昆明銀河酒家前面的垃圾桶里,但是偵查人員并沒有去查找此手槍,簡單定案。也就是說根本沒有找到作案工具,一個很重要的有罪證據都沒有找到,就判定杜培武有罪。偵查人員如果認真查找此證據,發現沒有這個作案工具,這就是一個無罪的證明。沒有作案工具的案件做出有罪的認定這是不可思議的,認真查找的話,可能冤假錯案就不會發生了。 聶樹斌案件中證據疑點 (1) 強奸致死案件,一個很重要的證據是在被害人體內提取出來精斑,在聶樹斌案件中,偵查人員對于從被害人體內沒有提取出來精斑這個無罪證據視而不見。 (2) 短袖襯衣照片是聶樹斌殺人案件實體證據中的唯一的所謂殺人工具。該襯衣根據聶樹斌的供述是從廢品店偷來的,偵查人員詢問廢品店的老板,老板說并沒有丟過襯衣,那么這個所謂的殺人工具應該是一個存疑證據,但是在這一案件中,偵查人員將其當做有罪證據。 (3) 在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法律文書上,僅僅只有聶樹斌的手印沒有簽名,由書記員代寫。偵查人員對此的解釋是犯罪嫌疑人帶著手銬,不方面書寫。在法官來認定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時候,對于這個證據由于偵查人員存在著不法行為,法官應當將其歸為無效證據,也就是負相關的證據,而在這個案件中,法官直接歸為犯罪嫌疑人口供也就是為有罪證據。 (4) 被害人的鑒定報告中鑒定結果為:頸部有衣服纏繞的痕跡,全身未發現創口和骨折符合窒息而死的。從而認定被告構成故意殺人罪。這里,被告代理律師提供的專家意見聲稱:被害人有肋骨骨折損傷,這是一個很強而有力的負相關證據,足以推翻死者的死亡原因,但是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對此證據視而不見。 趙作海案件中證據疑點 (1) 關于殺人工具,在趙作海案件中,警方并沒有找到殺人工具,也沒有確認所造成的傷痕是否與實體的傷痕相符合,在刑事案件中找不到作案工具,是不能定案的,在這個案件中,沒有這個重要的正相關證據也做出了有罪判決。 (2) 關于證人證言,有證人證明趙作海和趙振晌確實有經濟糾紛也曾打過架,在法官認定有關證據的時候,此證據應當作為一個疑罪證據,此證據需要和其他方面綜合考量,才能做出趙作海有殺人的動機,但是法官在認定此證據時直接作為有罪證據來認定。直接推定趙作海有殺人動機。 李懷亮案件證據疑點 (1) 關于證人證言,證人證明李懷亮曾到過作案現場,但是這個證人證言沒有其他能夠證明其與命案有任何關系的地方,并且這個證人證言是由被害人的親屬提供的,這個證據應當為存疑證據,應當去辨別其真偽,即使為真,也不是一定為殺人兇手。這個證據甚至是不是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都沒有認真審查,即使可以作為證據,也應當為疑罪證據。而在審理案件中缺作為一個有力的有罪證據。 (2) 在庭審過程中,李懷亮展示自己被刑訊逼供的傷疤,審判人員對刑訊逼供時間視而不見,將這個由刑訊逼供獲得的無效證據直接作為有罪證據來審理案件。 對于李懷亮這種情況在偵查中心主義訴訟模式下屢見不鮮,這對司法公正造成了極大破壞,也對犯罪嫌疑人對身心造成極傷害,案件審判過程不再信任司法機關更加崇尚自決。 一切冤假錯案的根源在于,有罪推定思想的先入為主,偵查人員對疑罪證據和無罪證據的忽視,法官對于偵查人員的過于信賴,對于檢察機關提交的證據不加以審查,將檢方提交的證據全部歸為有罪證據。而檢方由于其承擔著控訴職能,對于負相關的證據視而不見,造成整個案件正負相關證據失衡,正相關證據大于負相關證據。顯而易見,有罪判決就很容易形成。正負相關證據的確定其實就是邏輯因果關系強弱的確定。[5]這也是證據與事實形成鏈接的很重要一方面,處理不好冤假錯案就極其容易形成。 在近幾年來冤假錯案的多起發生對我國司法系統的公信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在證據問題上,我們應該有所反思,從證據的偵查到證據的審查都應該作為我們司法審判的重心,判決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說無罪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證據的收集和采納,而錯案的發生也很大程度上由于這個環節出現問題,對于正相關證據和負相關證據的平衡處理是得出公正判決的關鍵。 推進審判中心主義轉型,克服偵查中心主義的弊端,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當下,我國法治建設已經進入到深水區,很多方面都亟待改革,訴訟制度、訴訟模式都存在問題,面對這樣的現實狀況。不同法學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我認為法治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們著眼于他人的實踐,立足于我國自己的現實情況進行穩步改革,需要細致到每一方面,這就要求我們在證據改革方面提出我們的見解,證據是揭露案件真實情況的重要武器,如同李昌鈺博士說過:一個案件需要證據說話,故證據對于偵破案件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完善審判結構,就需要對證據進行有效對分類,促進向審判中心轉型。 從而形成系統的法治建設框架。從而為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模式打下基礎,加快法治建設的步伐。 [參考文獻] [1]何家弘,何然:《刑事錯案中的證據問題》,載《政法論壇》第26卷02期。 [2]薛歡:《論無罪證據在刑事錯案預防機制中的重要作用》,載《法制與社會》2013年04期。 [3]張偉:《論非法證據排除極其規則完善》,載《證據科學》2015年23卷。 [4]張繼成:證據相關性的邏輯研究》,載《廣西大學學報》第20卷06期。 [5]張繼成:證據相關性的邏輯研究》,載《廣西大學學報》第20卷06期。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