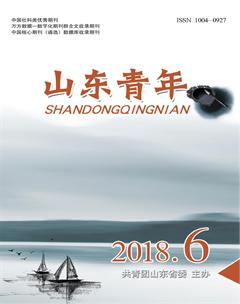法院訴訟調(diào)解化問題之淺析
摘 要:
法院調(diào)解制度是我國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在解決糾紛、緩解法院“案多人少”、提高結(jié)案率等方面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司法改革、民事訴訟審判方式改革及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理念的推動下,法院調(diào)解制度也不斷發(fā)生變化。本文針對法院調(diào)解制度在實際審判中出現(xiàn)的訴訟調(diào)解化問題進行深刻剖析,并針對問題提出規(guī)制措施。
關(guān)鍵詞:訴訟調(diào)解化;調(diào)審分離;訴訟和解
引 言
任何一項法律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由于政治和司法環(huán)境的影響,將可能或多或少地出現(xiàn)不適合司法發(fā)展的現(xiàn)象。法院調(diào)解制度也不例外,我們在充分肯定法院調(diào)解制度在我國民事訴訟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它在實踐審判中出現(xiàn)的的問題,其中訴訟調(diào)解化的問題就是其中之一。所謂的訴訟調(diào)解化是指訴訟調(diào)解的過分強調(diào)或調(diào)解強勢使得訴訟呈現(xiàn)出以調(diào)解為主、審判為輔的特點。[1]本文從法院調(diào)解的現(xiàn)實發(fā)展現(xiàn)狀入手,以法院調(diào)解制度的訴訟調(diào)解化問題剖析為著眼點,以規(guī)制和完善法院調(diào)解制度為最終落腳點,提出解決問題路徑。
一、回顧:法院調(diào)解制度發(fā)展之現(xiàn)狀
(一)調(diào)解升溫—緣于法律規(guī)制及政策引導
我國在不同階段對于法院調(diào)解分別進行不同程度的法律規(guī)定及政策引導,從2004年提出將人民調(diào)解和訴訟調(diào)解相銜接到2012年先行調(diào)解的確認,再到2016年特邀調(diào)解制度的建立,說明在法律及政策的大力引導下,各級法院對調(diào)解制度的過度運用,導致目前調(diào)解在法院案件審判中處于升溫狀態(tài)。
(二)強化調(diào)解—呈現(xiàn)以調(diào)解為主、審判為輔的傾向
在審判實踐中,各級法院將調(diào)解率、調(diào)撤率作為審判管理的“量化”指標,甚至作為衡量法官業(yè)務工作的硬性指標。同時為了緩解“案多人少”的現(xiàn)象,也大力推進法院調(diào)解的運用。對于法官來講,調(diào)解結(jié)案比裁判結(jié)案會減少大部分工作量,因此法官青睞適用調(diào)解結(jié)案。據(jù)統(tǒng)計21世紀初,在民事訴訟領(lǐng)域調(diào)解結(jié)案的比例已經(jīng)超過20世紀90年代以前,在之后,訴訟調(diào)解走在前列的基層法院幾乎是以每年5%以上甚至10%的幅度在提高訴訟調(diào)解的結(jié)案率,調(diào)解結(jié)案率已經(jīng)超過60%,有的甚至超過了70%。[2]過于強化調(diào)解結(jié)案,使審判實踐中出現(xiàn)了調(diào)解與審判的緊張沖突,出現(xiàn)了調(diào)解為主,審判為輔的態(tài)勢。
二、反思:分析訴訟調(diào)解化問題產(chǎn)生之原因
在真正的法制社會里,法院選擇符合法律正義要求的判決比不傷和氣的調(diào)解方式更加符合審判職能的要求。[3]法官是通過裁判文書的說理性對一個案件進行符合法律的判定,而不是體現(xiàn)在調(diào)解書上。因為調(diào)解案件不需要對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的過程進行闡明,使得多數(shù)案件不能通過法理分析、法律的適用加以解釋。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訴訟調(diào)解化問題產(chǎn)生的原因進行了剖析。
(一)調(diào)審合一的審判模式存在。目前我國訴訟調(diào)解是一種職權(quán)行為,是人民法院的一種審判活動,被歸入到法院審判權(quán)中。這種調(diào)審合一的性質(zhì)決定了訴訟調(diào)解具有如下鮮明特點:案件基準點是在法院受理案件后,審理終結(jié)之前,并有法官參與介入,調(diào)解協(xié)議經(jīng)主審人確認的活動。因此,在調(diào)解過程中調(diào)解人員的調(diào)判雙重身份是導致調(diào)解產(chǎn)生問題的重要原因,并且也是調(diào)解本身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得以爆發(fā)的導火索。這種調(diào)審不分的審判模式的確沖擊了調(diào)解自愿原則,弱化了審判職能,造成合意貧困化,為訴訟調(diào)解化的產(chǎn)生提供了空間。
(二)法院調(diào)解程序不完善。目前我國法院調(diào)解制度在程序設(shè)計上較為籠統(tǒng),對調(diào)解的基準點把握不清。在先行調(diào)解制度未被法定確認之前,法院調(diào)解就是案件立案后由法官介入的活動。后來特邀調(diào)解員制度的運用,使得法院調(diào)解在范圍上發(fā)生了變化。同時法院調(diào)解的時間截止點及次數(shù)也沒有明確規(guī)定,使調(diào)解主觀性和隨意性太強。
(三)自愿原則未充分得到保障。我國確立的調(diào)解核心原則是自愿原則,當前我國民事訴訟審判實踐中,還存在不尊重當事人意愿,片面追求調(diào)解結(jié)案率,久調(diào)不決,甚至采用不正當手段要求當事人接受調(diào)解的做法,使調(diào)解自愿原則未充分得到保障。在我國,法官在調(diào)解案件中起著主導作用,而不是律師。但在西方國家,對法官在調(diào)解案件中的中立性有著更高的要求,反而是律師在調(diào)解案件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三、規(guī)制:解決訴訟調(diào)解化問題之路徑
當下,我國缺失的是遵法、守法的意識,而這些意識源于我們對法律的理解和認知。案件經(jīng)過公開審判,法官對裁判進行說理性論述,是對學習法律最生動的教材。調(diào)解能夠解決糾紛、緩解“案多人少”、提高結(jié)案率,但這些都是短暫的成果,它無法做到公開裁判對社會的多方面、多層次的反射和影響。因此對于訴訟調(diào)解化的問題,應該通過多種舉措進行規(guī)制。
(一)構(gòu)建調(diào)審分離審理模式。目前,無論法律怎么確認法院調(diào)解的地位,都未將法院調(diào)解從審判權(quán)中分離出來,這使得當事人的權(quán)益未得到充分保障。同一案件由同一法官隨時決定是否采取調(diào)解還是審判結(jié)案,其結(jié)果是調(diào)解和裁判都受到了質(zhì)疑。案件進入訴訟階段應是以法官的裁判審理為中心,以法官對案件的法理分析、證據(jù)充分認定、法律適用的理解、裁判結(jié)果的分析,通過這些才能使當事人在案件裁判結(jié)果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存在。因此,推行調(diào)審分離是必要之舉。目前,我國正處于司法改革時期,加之司法基礎(chǔ)的完善,具備推行調(diào)審分離審理模式,單獨構(gòu)建調(diào)解機制及程序的前提條件。推行調(diào)審分離雖會增加新的程序,可能為當事人帶來不便,但與保障當事人權(quán)利相比利大于弊。同時設(shè)立調(diào)審分離審理模式,會充分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自由權(quán)。
(二)著力強化調(diào)解自愿原則。要解決訴訟調(diào)解化,保證調(diào)解的合理運用,關(guān)鍵還在于堅持民事訴訟法已經(jīng)確立的調(diào)解自愿原則。只要堅持這一原則,訴訟調(diào)解自然就會在合理的范圍之內(nèi)。[4]確實如此,調(diào)解自愿與調(diào)解強制是對立而言的,強化自愿原則,同時就要消除強制調(diào)解。由于我國實行調(diào)審合一制度,使得法官在案件的任何環(huán)節(jié)都可以啟動調(diào)解程序,為強制調(diào)解的存在提供了存在空間。所以針對部分類型案件可以推行調(diào)解適當公開原則,對法官強制調(diào)解及當事人惡意行使處分權(quán)起到雙向制約作用。
(三)確立民事訴訟和解制度。目前訴訟和解制度得到了很多域外國家的認可,我國《民事訴訟法》第50條雖然提到了雙方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但卻沒有規(guī)定訴訟和解的程序和效力。在目前確立民事訴訟和解制度,可以更好地維護自愿原則的實現(xiàn),同時也可以扭轉(zhuǎn)審判實踐中調(diào)解占強勢的局面。但訴訟和解制度的構(gòu)建涉及到程序等諸多方面的內(nèi)容,需要通過法律或司法解釋進行規(guī)制。
結(jié) 語
人存在,糾紛亦存在,就會出現(xiàn)解決糾紛的多種方法,無論選擇何種途徑解決,我們都希望是基于自愿公平的基礎(chǔ)上。法院調(diào)解制度具有公權(quán)裁判和私權(quán)合意處分的雙重屬性,不能達到當事人完全自愿及公平的社會效果,審判中反映出的訴訟調(diào)解化問題就是最有說明力的體現(xiàn)。目前,我國的訴訟程序及結(jié)構(gòu)需要發(fā)揮裁判對法律的闡明作用,對社會行為的指引作用。因此,我們更需要以審判為中心,而非以調(diào)解為中心。
[參考文獻]
[1]張衛(wèi)平:《民事訴訟法》[M],法律出版社2016年8月版,第316頁.
[2]此段涉及的數(shù)據(jù)來源于張衛(wèi)平:《民事訴訟法》[M],法律出版社2016年8月版,第315頁.
[3]孫永軍、王東風:“合意-判定”型調(diào)解程序結(jié)構(gòu)合理性之誠正—兼論法院調(diào)解訴訟化傾向的改革思路[J].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1年11月第32卷第6期,第51頁.
[4] 張衛(wèi)平:《民事訴訟法》[M],法律出版社,2016年8月.第317頁.
作者簡介:許春娟, 女 (1980.04-), 黑龍江省望奎縣人, 研究生碩士,研究方向: 從事民事訴訟法研究。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研究生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