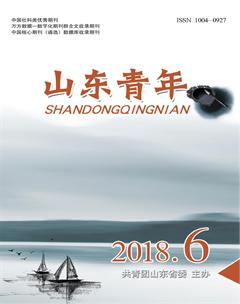班固儒學(xué)觀下的《漢書(shū)》著史宗旨
王秀妍
摘 要:
眾所周知,班固是一名徹頭徹尾的儒者。他的儒學(xué)觀源自于東漢初年今古文經(jīng)學(xué)的社會(huì)背景,其成長(zhǎng)過(guò)程中深受儒學(xué)思想文化世家的浸潤(rùn),豐富的師友交游經(jīng)歷也使其儒學(xué)觀更加成熟完善。受制于東漢初年的社會(huì)背景、儒學(xué)世家的思想淵源、豐富的師友交游經(jīng)歷,班固在著史中堅(jiān)守他的儒學(xué)立場(chǎng),極力推崇儒家“六藝”之文,以漢室為正統(tǒng),在著書(shū)立說(shuō)中秉承尊儒宗經(jīng)、尊漢擁劉的原則。通過(guò)認(rèn)識(shí)班固儒學(xué)觀下的《漢書(shū)》著史宗旨,有助于深入理解史書(shū)的內(nèi)涵。
關(guān)鍵詞:班固;儒學(xué)觀;《漢書(shū)》;著史宗旨
“司馬遷書(shū)《史記》,遂有紀(jì)傳一體。”(《四庫(kù)全書(shū)總目提要》)《史記》可以稱之為《漢書(shū)》成書(shū)的直接動(dòng)力,而斷代史之作《漢書(shū)》相對(duì)于通史之作《史記》,對(duì)西漢時(shí)期的歷史有了更為詳實(shí)的記載。馬、班二人雖然同是繼承了儒學(xué)精神,但是因所處時(shí)代背景不同,在著史過(guò)程中表現(xiàn)的思想傾向不同。司馬遷推崇儒家,但不以儒家學(xué)說(shuō)作為品評(píng)古今人物及諸子學(xué)派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班固則是完全被儒學(xué)理念影響制約。本文將追溯班固儒學(xué)觀的時(shí)代淵源、家學(xué)淵源和師友交游經(jīng)歷,考察并探究他的著史宗旨,由此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漢書(shū)》的深層內(nèi)涵,為當(dāng)代儒學(xué)發(fā)展提供參照物。
一
班固儒學(xué)觀的形成是多種因素交織的結(jié)果。東漢初年國(guó)力的強(qiáng)盛、今古文經(jīng)學(xué)的發(fā)展和班氏儒學(xué)世家濃厚的文化氛圍、班固讀書(shū)著史的交游經(jīng)歷等因素共同筑就了班固的儒學(xué)觀。
首先,班固所處的東漢初年,既是東漢封建王朝統(tǒng)治的鼎盛時(shí)期,亦是一個(gè)面臨著諸多尖銳矛盾的時(shí)期,因此緩和諸這諸多矛盾、鞏固封建政權(quán)成為東漢王朝統(tǒng)治者的當(dāng)務(wù)之急。加強(qiáng)思想上的控制也就隨之成為首要的政治任務(wù)。
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重建了統(tǒng)一的國(guó)家,并鞏固了東漢政權(quán),實(shí)現(xiàn)了初期國(guó)力的強(qiáng)盛,為后代明帝、章帝等人的統(tǒng)治奠定了基礎(chǔ)。這一時(shí)期,中央集權(quán)不斷加強(qiá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加快,社會(huì)環(huán)境日趨穩(wěn)定,處于明顯的上升成長(zhǎng)時(shí)期。在社會(huì)思想領(lǐng)域,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之后,儒學(xué)發(fā)展處于昌盛的局面。在今古文經(jīng)學(xué)兩個(gè)學(xué)派傳經(jīng)之風(fēng)興盛的大背景下,光武帝劉秀繼承了以往把儒學(xué)作為統(tǒng)治思想的做法,進(jìn)一步崇尚儒學(xué);明帝行尊儒大典,宣講經(jīng)義,表現(xiàn)了對(duì)儒學(xué)的高度重視;章帝主持了著名的“白虎觀”會(huì)議,講論“五經(jīng)”異同,作《白虎議奏》,制定出一套儒家經(jīng)義相關(guān)的標(biāo)準(zhǔn)和法則。由此可見(jiàn),東漢初年思想領(lǐng)域的景對(duì)班固的儒學(xué)意識(shí)形態(tài)具有非常典型的塑造作用,對(duì)其歷史寫(xiě)作秉承王朝大一統(tǒng)觀念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其次,班固出身于文化氛圍濃厚的儒學(xué)世家,這一點(diǎn)對(duì)其儒學(xué)觀的形成也具有直接的影響。正如鄭樵有言:“古者修書(shū),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學(xué),班馬之徒是也。”(凌稚隆《漢書(shū)評(píng)林·漢書(shū)總評(píng)》引)《漢書(shū)·敘傳》是當(dāng)下我們了解班固家世的第一手資料,也是唯一的資料。班固的家學(xué)淵源可以追溯至他的六世祖班壹,班壹為避戰(zhàn)亂到樓煩,懂得因地制宜,從而“致馬牛羊數(shù)千群”,發(fā)家致富,“以財(cái)雄邊”,成為當(dāng)?shù)氐暮栏弧0嘁贾影嗳鎰t是班氏家族最早登上仕途之人,之后的子孫也大多是頗有政績(jī)。漢成帝時(shí),班家之女班婕妤被帝王寵幸,班氏隨之成為貴戚順利獲得進(jìn)身之階,自班伯、班斿和班稚三人始,班氏家族成為儒學(xué)世家。正如班固所述:“家有賜書(shū),內(nèi)足于財(cái),好古之士自遠(yuǎn)方至,父黨揚(yáng)子云以下莫不造門(mén)。”(《漢書(shū)·敘傳》)因此從班固的祖父輩起,就為班氏家族的子弟們營(yíng)造了濃厚的學(xué)術(shù)氛圍,為班固的儒學(xué)觀塑造創(chuàng)造了環(huán)境條件。而對(duì)班固影響最直接的莫過(guò)于他的父親班彪,班彪深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的思想影響,“唯圣人之道然后盡心焉”(《漢書(shū)·敘傳》),完全以儒家思想為準(zhǔn)則,反對(duì)“崇黃老而薄五經(jīng)”,主張“依五經(jīng)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后漢書(shū)·班彪列傳》)。一言以蔽之,班氏家族的家學(xué)淵源對(duì)班固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班固讀書(shū)著史過(guò)程中的交游經(jīng)歷也對(duì)其儒學(xué)觀的形成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主要包括進(jìn)入洛陽(yáng)太學(xué)讀書(shū)的經(jīng)歷和作為蘭臺(tái)令史編纂《漢書(shū)》的經(jīng)歷。在洛陽(yáng)太學(xué)讀書(shū)的過(guò)程中,班固結(jié)識(shí)了同鄉(xiāng)扶風(fēng)李育、傅毅、魯國(guó)孔僖、涿郡崔骃諸人。其中李育被號(hào)為“通儒”,章帝時(shí)還在白虎觀與諸儒討論《五經(jīng)》,深受班固敬重;孔僖為孔子后代,固然是儒家思想的堅(jiān)定信仰者;崔骃通讀《五經(jīng)》,通古今訓(xùn)詁百家之言,與班固、傅毅齊名于洛陽(yáng)太學(xué)。明帝時(shí),班固奉命擔(dān)任蘭臺(tái)令史。在蘭臺(tái)期間,班固不僅與之前洛陽(yáng)太學(xué)的友人相遇,還結(jié)識(shí)新的友人,如尹敏、賈逵、孟冀等,對(duì)班固后來(lái)編撰《漢書(shū)》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其中尹敏、賈逵都精于經(jīng)學(xué)書(shū)籍,對(duì)《五經(jīng)》有專門(mén)的研究。以上班固在讀書(shū)和著書(shū)過(guò)程中結(jié)識(shí)交好的友人,大部分都是當(dāng)時(shí)知名的儒者文士,他們與班固一起讀書(shū)、工作,可以想見(jiàn),對(duì)于班固的思想影響必定根深蒂固。
二
在以上多種因素的交織影響下,班固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儒學(xué)觀。班固的儒學(xué)思想可以概括為“尊儒宗經(jīng)”,而在“尊儒宗經(jīng)”的前提下又形成了儒學(xué)化的政治觀“尊漢擁劉”和儒學(xué)化的天人觀“天人感應(yīng)、君權(quán)神授”。
班固在批判司馬遷《史記》時(shí)說(shuō)“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漢書(shū)·司馬遷傳贊》),由此可以充分證明班固“尊儒宗經(jīng)”的儒學(xué)觀。班固認(rèn)為儒家“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漢書(shū)·儒林傳》)班固將“六藝”之文視為王道教化的典籍和達(dá)成至治的成法,表明了班固對(duì)儒家學(xué)說(shuō)的極力推崇,主張用“六經(jīng)”加以教化民眾。
“尊漢擁劉”則是在“尊儒宗經(jīng)”前提下的重要政治表現(xiàn),隨著漢朝中央集權(quán)不斷加強(qiáng),班固自身又擁有正統(tǒng)的儒家思想,因此他在政治思想上便具有了“尊漢擁劉”的特質(zhì)。班固認(rèn)為劉邦建立漢朝是“得天統(tǒng)”,即“漢承堯運(yùn)”、“協(xié)于火德”,是“自然之應(yīng)”,也就是說(shuō)劉邦興漢是命中注定的事情;而王莽的行徑為“咨爾賊臣,篡漢滔天”(《漢書(shū)·王莽傳》),對(duì)王莽大加撻伐。從班固對(duì)劉邦興漢的認(rèn)同和王莽篡漢的貶斥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忠于一朝一姓的正統(tǒng)觀念和立足于大一統(tǒng)的政治立場(chǎng),體現(xiàn)了他忠君愛(ài)國(guó)的政治理念。
在《漢書(shū)》中,屢次可見(jiàn)班固旗幟鮮明地表達(dá)了以漢室為正統(tǒng)的政治思想。班固首先在《漢書(shū)·高帝紀(jì)》中闡述了劉氏得天下和建立漢朝的理論依據(jù),“漢承堯運(yùn),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xié)于火德,自然之應(yīng),得天統(tǒng)矣”,他認(rèn)為,劉邦興漢是“自然之應(yīng)”,遂“得天統(tǒng)”,即劉邦登上帝位是命運(yùn)使然。其次班固在《漢書(shū)·敘傳》中明確表達(dá)了以漢室為正統(tǒng)的思想,“項(xiàng)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zhàn)士憤怒”,批判曾經(jīng)與劉邦爭(zhēng)奪天下的項(xiàng)羽,其行為是大逆不道的。再如在《漢書(shū)·陳勝項(xiàng)籍傳》中,班固先是引用賈誼的《過(guò)秦論》來(lái)解說(shuō)秦滅亡和秦二世、子?jì)搿吧硭廊耸郑瑸樘煜滦φ摺钡脑蛟谟凇叭柿x不施”,因此必然導(dǎo)致國(guó)家滅亡的悲慘結(jié)局,批評(píng)項(xiàng)羽“背關(guān)懷楚,放逐義帝”,“自矜功伐,奪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guó),欲以力征經(jīng)營(yíng)天下”,最終卻演變成“五年卒亡其國(guó)”的下場(chǎng),班固認(rèn)為項(xiàng)羽之失在于“誅嬰放懷,詐虐以亡”。通過(guò)以上班固對(duì)于劉氏得天下和項(xiàng)羽敗亡的批判態(tài)度,可見(jiàn)其內(nèi)心所固有的以漢室為正統(tǒng)的熾熱的思想感情。
三
司馬遷著《史記》的宗旨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shū)·司馬遷傳》),著書(shū)立說(shuō),探索真理;而班固在《漢書(shū)》中弘揚(yáng)司馬遷實(shí)錄精神的基礎(chǔ)上,“緯‘六經(jīng),綴道綱”(《漢書(shū)·敘傳》),以儒家“六經(jīng)”為緯,維護(hù)儒家道統(tǒng)。
班固在推崇司馬遷史學(xué)時(shí),引用劉向和揚(yáng)雄對(duì)司馬遷的評(píng)價(jià):“自劉向、揚(yáng)雄博極群書(shū),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shí)錄”(《漢書(shū)·司馬遷傳贊》)。班固認(rèn)為司馬遷著史能使人信服,對(duì)歷史的描述不憑空增加好處,也不掩蓋其壞處,經(jīng)得起事實(shí)的驗(yàn)證。班固通過(guò)此評(píng)價(jià)寄托自己的著史志向,在宣揚(yáng)漢代功業(yè)的基礎(chǔ)上,以“實(shí)錄”為原則,秉筆直書(shū)。
綜上所述,《漢書(shū)》一書(shū)尊儒宗經(jīng),推崇儒家思想,在對(duì)儒家民本、忠君愛(ài)國(guó)等思想的繼承過(guò)程中,凸顯了儒家代表人物孔孟、儒家經(jīng)典《論語(yǔ)》《大學(xué)》《中庸》《孟子》、儒家思想學(xué)說(shuō)的地位。通過(guò)認(rèn)識(shí)了解班固儒學(xué)觀下的《漢書(shū)》著史宗旨,有助于深入領(lǐng)悟《漢書(shū)》的文本內(nèi)涵。
[參考文獻(xiàn)]
[1][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shū)》,北京:中華書(shū)局,1962年.
[2]梁宗華著:《漢書(shū)要義》,北京:光明日?qǐng)?bào)出版社,1996年.
[3]陳其泰、趙永春著:《班固評(píng)傳》,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
[4]安作璋著:《班固評(píng)傳——一代良史》,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5]劉厚琴著:《儒學(xué)與漢代社會(huì)》,濟(jì)南:齊魯書(shū)社,2002年.
[6]吳崇明著:《班固文學(xué)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xué) 齊魯文化研究院,山東 濟(jì)南 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