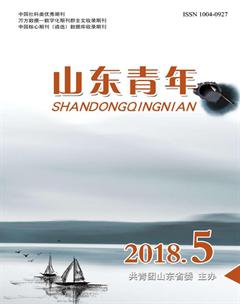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
徐己
摘 要:本文從201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出發,對著作權中有關條文進行分析并提出建議,同時結合學術界的觀點,結合國情,對一般條款的建立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提出建議。
關鍵詞:合理使用;著作權;適當引用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Blackmun曾指出,如若剝奪權利人的專有權,會降低其創作的誘因;如若賦予權利人完全的專有權,則會降低他人創作的能力。①《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在2014年通過,但是其中對“合理使用”的修改卻存在著以下不足。
一、出于個人目的的合理使用
關于“合理使用”制度,《修訂草案送審稿》第四十三條對《著作權法》中的條文做了以下修改:第一,不再把出于“個人欣賞”目的的使用視作“合理使用”。第二,將原本的“使用”改為“復制”。第三,將原條文中的“已經發表的作品”改為“已經發表的作品的片段”。
不可否認的是這一修改有合理之處,例如不再把出于“個人欣賞”目的的使用視作“合理使用”。《著作權法》頒布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勵作品的創新,而一般來說,相對于出于“學習、研究”的目的,“欣賞”可以說是對作品的“消極使用”,即出于“欣賞”目的的使用往往停留在吸收層面,而很難上升到創造價值的層面,這與為了創新的目的而對原作品進行借鑒的行為有很大不同。此外,隨著網絡等傳播媒體的飛速發展,人們已經習慣于將他人的作品上傳到新型的網絡媒介上,比如博客,雖然不能排除其中有出于“個人欣賞”目的,但是此類行為卻損害了原著作權人的利益,應當排除在“合理使用”的界限之外。
但同時,《修訂草案》無疑將著作權“合理使用”的范圍大大縮小,從某些方面來說,不利于鼓勵作品的創新和傳播,在某些詞語的選擇上的不嚴謹也導致條文的解釋不清。例如《修訂草案》中提到的“作品的片段”,按照通常理解,“片段”是相對于“全文”而言的,那是不是可以說只要使用的不是作品的“全文”就可以算作《修訂草案》中作品的“片段”?這樣說來,如果著作權人本身的作品有一萬字,那我使用了其中的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字,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使用作品的“片段”,進而認定為“合理使用”?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又如,將“使用”改為“復制”,也是不當限縮了“合理使用”制度的適用范圍。《著作權法》中的“使用”一詞,應當包括了復制、翻譯、改編等多種方式。在實踐中,為個人學習、研究而使用他人作品的方式也遠遠不僅限于“復制”,在閱讀外文資料的時候,通過翻譯等方式而進行的使用反而更為常見,如果只有“復制”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才能算作合理使用,那么使用者出于更易研究的目的將外文資料進行翻譯難道應算是侵權?“復制”是對原作品不做絲毫改動而加以照搬,“翻譯”通常只是對語言的差異而進行轉換,兩者在對作品表達的思想的引用方面實際上并沒有差別,沒有必要進行如此死板的區分。
二、對“適當引用”的界定問題
《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中提到的“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和《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六條中提到的“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向公眾提供的作品中適當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同樣存在上述“用詞不清”的情況。具體來說,就是對“適當”一詞的定義和界限不明,到底對原作品做何種程度的引用才能說是“適當”,而不是“引用過多”或者“引用過少”?在我國1985年頒布的《圖書、期刊版權保護試行條例實施細則》中對“適當引用”做了極為詳細的說明,甚至將作品做了嚴格區分,對“適當引用”以具體字數做了劃分,這一《實施細則》雖然對“適當”一詞的界限劃定的十分精確,但是卻過于機械和嚴苛,沒有對引用的目的進行區分,而僅僅停留在字數層面,對“適當”的定義非黑即白,完全剝奪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一《實施細則》現已被廢除,但是對“適當”又沒有提出新的界定標準,導致實踐中的爭議愈演愈烈。
2009年,陳少華訴音著協不當使用其歌曲片段②一案中,如果機械適用對“數量”的規定來判定是否構成“適當引用”,那么音著協的引用行為可以說是滿足“合理使用”要件的。但是陳少華提出,音著協使用歌曲的行為完全超出了適當的范圍,構成實質性使用。筆者認為,《著作權法》在對“適當”的標準進行界定的過程中可以借鑒美國有關合理使用的“四要件”其中的精神,即在界定時考慮“與該完整作品相比,所使用部分的數量和內容之實質性”。首先,在考慮是否構成“適當引用”時應當對使用的數量進行規定,作為一種輔助性的參考,而不能采取窮盡性的規定。除此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對所使用部分的“內容的實質性”做出判定,如果對原作品的實質性內容進行引用,即使可能沒有達到對數量的規定,法院也可以將這種行為排除在“合理使用”之外,但是這對法官的要求也應相應的提高。
三、一般條款的建立
如上所述,有關“合理使用”的規定主要有以下兩種不合理的現象:第一,某些條款中的用詞模糊不清,容易產生爭議。第二,某些條款中的用詞過于嚴苛,不當縮小了“合理使用”的適用范圍。
在我國現有的知識產權研究學者中,多數人認為我國《著作權法》應規定合理使用的一般條款,“為合理使用提供更多的規則性( rule) 法律規范,而不是提供標準型的( standard) 或原則性的規范”。③相對于中國《著作權法》中機械嚴苛的規定,應當承認這種賦予“合理使用”更大自由度的規范是更適合多變的現實的,畢竟對于現實生活中不斷變化的狀況,想要做出詳細完美、涉及社會各方面的定義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也應當結合中國現有的國情,認識到中國目前法官的素質和能力以及中國現有的執法水平還亟待提升,上述的自由裁量權對法官的要求極高,如果法官之間各執一詞,不能達成合意或者沒有把握好自由裁判權的限度,就很容易使法院演變為法官個人的表演場,法官自由裁判權的濫用和誤用極易導致現實中的各類案件的裁判發生不公,或者使某些存在爭議的案例被長久擱置。
條文的抽象化和體系化是著作權法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有關合理使用制度的一般條款的頒布也是必然。雖然法官的裁判能力暫時不能很好地適應自由裁量權,但是“規制法官的權力不是著作權法應當承擔的任務,而在于司法體制的改革”。事實上,一般條款的設立并不必然導致法官濫用權力,完全剝奪自由裁量權的行為只是出于對法官的不信任而做出的消極應對措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現狀。對中國的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應當進行靈活規定,一味地保留和改變都是不可取的,在現有的基礎上加以完善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
[注釋]
①參見吳漢東:《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 18頁。
②中國知識產權裁判文書網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9〕鄂民三終字第6號。
③梁志文《著作權合理使用的類型化》載于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2 年第 3 期( 總第 82 期)。
[參考文獻]
[1]吳漢東《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國知識產權裁判文書網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9〕鄂民三終字第6號。
[3]梁志文《著作權合理使用的類型化》,載于《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2 年第 3 期。
[4]黃玉燁《著作權合理使用具體情形立法完善之探討》,載于《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總第150期)。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