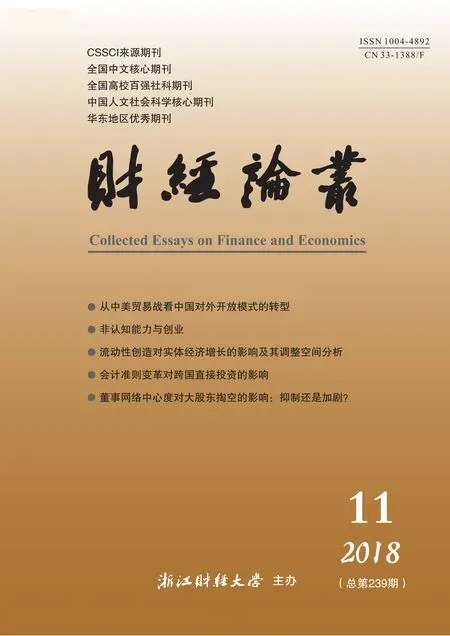通貨膨脹、產業政策與企業自主創新
劉向強,李沁洋,胡 珺
(1.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重慶 400715;2.海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海南 海口 570228)
一、引 言
通貨膨脹是現代經濟的一項顯著性特征,對宏觀經濟增長和微觀企業行為都具有重要影響。本文試圖結合產業政策,分析通貨膨脹下企業自主創新策略的選擇,以提供通貨膨脹影響企業微觀行為傳導機制的經驗證據。本文研究的第一個問題是當通貨膨脹相對上升時,企業是否通過自主創新的方式對沖通貨膨脹上升導致資產價值發生減損的風險;第二個問題探討在產業政策的影響下,通貨膨脹對企業自主創新的影響在不同行業之間是否存在差異,以及差異形成的原因。
20世紀30年代,著名經濟學家費雪最早揭示了通貨膨脹與股票市場的關系,認為通貨膨脹對投資于資本市場的貨幣收益存在重要影響,降低了貨幣投資的實際收益[1]。其后,Fama and Schwert(1977)[2]、Danthine and Donaldson(1986)[3]等相繼佐證了費雪的思想,劉金全和王風云(2004)[4]、肖才林(2006)[5]、饒品貴和羅勇根(2016)[6]等也證實費雪效應在中國同樣存在。通貨膨脹風險還對宏觀經濟增長同樣存在重要影響,Barro(1996)[7]、Andrés and Hernando (1999)[8]以及Erb and Harvey(2006)[9]等發現,由于通貨膨脹會導致商品價格明顯上漲,吞噬了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從而存在再分配效應。相對于富人而言,窮人資產結構中的貨幣資產占比更高,使得通貨膨脹對兩者的財產具有不平等的沖擊影響。在中國同樣存在西方國家類似的財富再分配效應[10]。
通貨膨脹風險傳遞機制具有隱形性特征,從而使得對通貨膨脹風險微觀效應的研究非常困難[11]。近些年來,通貨膨脹風險的微觀傳導機制引起了中國學者們的關注。當通貨膨脹相對上升時,企業會積極進行戰略調整,比如減少現金持有水平[12]、調整資本結構[13]、增加存貨準備[14]和提高資本支出規模[15]等,以規避或對沖通貨膨脹相對上升時潛在的風險。
選擇以自主創新作為企業行為的切入點,主要是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考慮:第一,創新是企業實現產品差異化、提高核心競爭力和獲得產品市場競爭優勢的內在動力,同時也是實現中國經濟升級、推動產業轉型和技術改革的重要源泉[16],研究通貨膨脹與企業自主創新的關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業創新行為的驅動因素;第二,面對通貨膨脹產生的貨幣貶值風險,企業會策略性地調整現金持有[12]、資本結構[13]、存貨庫存[14]和資本支出規模[15]等。與上述策略不同,自主創新具有不確定風險較大、資本回收期較長等特征。因此,當通貨膨脹上升時,企業是否會通過自主創新以規避通貨膨脹沖擊的風險尚無定論,而創新是否能有效對沖這種風險也有待實證檢驗。
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傳導機制一直是理論和實務界非常關注的一個話題。但受限于學科分布和數據可獲得性,相關研究才剛剛起步[17]。基于中國背景的研究發現,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的商業信貸[18]、現金持有水平[19]、外部融資[20]和投資規模[21]等方面都存在顯著影響。從企業的創新行為來講,一些學者分別從財稅政策[22][23]、產業政策[24][25]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因此,本文試圖研究的第二個問題是結合產業政策,考察通貨膨脹與企業自主創新的關系在產業政策的影響下是否存在差異,以及差異形成的原因。
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體現在:第一,通貨膨脹風險傳遞機制具有隱形性特征,本文以企業自主創新為切入點,研究了通貨膨脹與微觀企業行為的互動關系,進一步顯性化了通貨膨脹風險傳導機制的微觀效應研究,同時也拓展了已有文獻關于通貨膨脹風險傳導下企業行為對沖的方式研究[12][13][14][15];第二,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傳導機制一直都是理論和實務界非常關注的一個話題,但相關研究才剛剛起步[17],本文在微觀層面檢驗了產業政策與企業自主創新的關系和內在機制,進一步拓展了我國政府強干預背景下的產業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關系研究[14][16][17][18][19];第三,企業創新是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的根本動力,本文基于通貨膨脹和產業政策的角度,研究了企業自主創新的宏觀驅動因素,進一步豐富了企業自主創新的影響因素研究[25][26][27][28][29],也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效果提供了微觀企業的經驗證據。
二、文獻回顧與假設提出
本文的目的是結合產業政策,研究通貨膨脹對企業自主創新策略選擇的影響,以提供中國通貨膨脹風險傳導機制的微觀證據。因此,本文從通貨膨脹風險的微觀傳導理論機制和產業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兩個方面對已有文獻進行回顧和評述,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
(一)通貨膨脹與企業自主創新
通貨膨脹風險傳遞機制的隱形性特征使得對通貨膨脹風險微觀效應的研究非常困難[11]。近年來,許多學者試圖從微觀企業行為的視角揭示通貨膨脹風險的微觀傳導機制。饒品貴和張會麗(2015)首先從企業現金持有水平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由于通貨膨脹上升時,貨幣的實際收益率將降低,因此企業會策略性地減少現金持有水平[12];饒品貴等(2016)還從企業存貨管理的視角研究發現,當通貨膨脹相對上升時,企業會有針對性地提高存貨準備,以預防通貨膨脹招致的貨幣購買力下降風險[14];從股票市場的角度,饒品貴和羅勇根(2016)從債務融資的視角解釋了通貨膨脹導致股票收益率下降的原因,他們發現企業增加債務融資是通貨膨脹與股票收益率呈負相關關系的主要內在機制[6]。此外,李青原等(2015)從銀行債務融資的角度發現通貨膨脹是企業資本結構的重要決定因素,由于通貨膨脹降低實際利率,因此通貨膨脹率上升時企業會增加銀行債務[13];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從企業投資水平的角度對通貨膨脹風險傳遞機制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企業會增加通貨膨脹時的投資水平以避免風險損失[15]。
從理論上分析,通貨膨脹對企業自主創新的影響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通貨膨脹會影響企業貨幣性資產的持有價值,進而影響企業的自主創新水平。貨幣性資產貶值、商品價格上升是通貨膨脹最顯著的特征[9],這對企業的現金存款、其他流動和非流動資產的價值具有非對稱的影響,企業在通貨膨脹上升時持有過多貨幣性資產將不可避免地承擔貶值風險。當通貨膨脹率相對上升時,管理層會策略性地調整企業資產結構,如降低現金持有水平[12]和增加存貨準備[14]等,以盡可能地對沖通貨膨脹的貶值風險。因此,在通貨膨脹相對上升時,企業為對沖或規避貨幣性資產的貶值風險,可能將更多貨幣性資產投資于自主創新,采取更加積極的自主創新策略。
第二,通貨膨脹會影響企業債務融資結構和成本,進而影響企業的自主創新水平。通貨膨脹的上升會降低企業債務融資的實際成本,但由于通貨膨脹通常不容易被觀察到,從而導致對銀行和企業的放貸與借款利益具有非對稱的影響[13]。從銀行的角度來講,通貨膨脹率上升最直接的后果可能會導致中央政府削減未來的信貸規模[30]。但是,考慮到信貸規模與商業銀行的利益密切相關,出于維持信貸規模和規避中央政策監管的目的,商業銀行會傾向增加當期的信貸供給,為企業獲得貸款提供外部條件[15]。從企業的角度來講,由于中央銀行“反通脹”的貨幣政策調整存在滯后效應[31],且借貸合同的約定利率往往具有跨期性,中央銀行的貨幣調整行為可能并非充分及時[13][32],因此當通貨膨脹相對上升時,企業已有或新增的銀行貸款實際利率會出現下降。通貨膨脹上升時期,由于企業可獲得債務融資規模增加及融資成本的下降,可降低融資約束對企業自主創新的影響[33][34],因而企業可能會增加自主創新水平。
第三,通貨膨脹導致的宏觀經濟不確定性會影響企業的資產管理和投融資策略,進而影響企業的自主創新水平。通貨膨脹率上升可能導致宏觀經濟運行低效率、失業率上升和社會投資額下降等現象的發生[35]。由于通貨膨脹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沖擊,增加了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因此通貨膨脹率上升時期,通常也預示著宏觀經濟政策的高度不確定性時期[36]。在此背景下,企業往往會策略性地調整資產管理方式或投融資選擇策略。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指出,當實際通貨膨脹率相對上升時,政策不確定性程度的提高會增加企業投資成本,投資機會也會相對減少[15]。李鳳羽和楊墨竹(2015)、饒品貴等(2016)也發現,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較高時,投資水平會因此出現相對下降[37][14]。但由于自主創新更多是企業內部資源、要素和技術的整合與創造,其受到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影響也相對更低。企業在既定資源條件下,高通貨膨脹會減少投資機會,使得企業會相應增加自主創新投入。綜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設1:
H1:當通貨膨脹率相對上升時,企業會相應增加自主創新水平。
(二)通貨膨脹、產業政策與企業自主創新
近年來,關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效應研究已成為理論界關注的重要話題,已有文獻從企業投資、融資和營運資本管理等各方面都證實了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企業行為的重要影響[19][20][21][25][38]。從這些文獻來看,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企業行為的影響可以歸納為融資約束路徑和投資機會路徑兩個方面。
融資約束路徑方面,宏觀經濟政策可能改變企業所面臨的融資環境,從而影響企業外部資金籌集的能力。宏觀經濟政策一般都具有明顯的產業扶持傾向,當企業所處行業歸屬于政策支持性產業時,通常能在信貸等方面獲得更多的支持,更容易從銀行獲得貸款,融資成本也相對較低[20][21];與此同時,還為企業向資本市場傳遞了有利信號,以降低企業內部與外部投資者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幫助政策扶持性企業吸引更多外部融資。陳冬華等(2010)分別從上市公司首次公開融資(IPO)、股權再融資(SEO)和銀行貸款三個維度系統地考察了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外部融資的關系,他們發現當企業受到宏觀政策支持時,其IPO融資、SEO融資和銀行長期貸款能力都會顯著上升。黎文靖和李耀淘(2014)、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等的經驗證據也發現了類似的結論[21][25]。
投資機會路徑方面,宏觀經濟政策可能改變企業面臨的競爭環境,從而影響企業可獲得投資機會的能力。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整政策通常會為扶持性產業提供良好的成長和投資環境[19]。當企業處于政策扶持性產業內時,中央或地方政府一般會提供項目審批和核準的支持、稅收和土地的優惠等好處,從而使得這些重點扶持性企業可獲得更多的投資機會。比如楊繼東和楊其靜(2016)指出,在中央政府實施宏觀經濟政策下,存在保增長壓力的地方政府會出讓更多的工業用地[38]。與此同時,政策實施所帶來的行政管制放松和銀行信貸供給也降低了企業在擁有投資機會時的融資約束,有助于改善其把握投資機會的能力[20]。陸正飛和韓非池(2013)的經驗證據也表明,受宏觀經濟政策支持的企業獲得了更多的投資機會,提升了企業現金持有的產品市場競爭效應[19]。
結合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行為的兩條主要路徑,以及通貨膨脹與企業自主創新的關系來看,本文認為,盡管通貨膨脹相對上升時企業會相應提高自主創新水平,但這種關系可能受到產業政策沖擊的影響。一方面,從融資約束路徑來講,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在信貸、補貼等方面能夠獲得更多的支持,自主創新投入所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較低。因此,相對于未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產業政策的支持可能使企業在通貨膨脹上升時的自主創新投入更多。
另一方面,從投資機會路徑來看,由于創新投入的產出同樣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當企業面臨一個較好的投資環境或較多投資機會時,即當企業獲得產業政策支持時,企業會在這些投資機會與自主創新之間權衡,增加更多風險小、回收期短的項目投資,這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擠出企業自主創新。因此相對于未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由于具有更多投資選擇,在通貨膨脹上升時的自主創新行為相對較少。
綜上分析,依據產業政策的融資約束和投資機會路徑,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a:基于產業政策的融資約束路徑,相對于非扶持性行業,通貨膨脹上升時政策扶持性行業的企業自主創新相對更多;
H2b:基于產業政策的投資機會路徑,相對于非扶持性行業,通貨膨脹上升時政策扶持性行業的企業自主創新相對較少。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中國2003~2014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初始研究樣本。借鑒已有研究[12][13][6][14][15][25],本文按照以下原則對初始樣本進行了篩選:剔除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因為這些公司的財務數據結構和監管制度與其他行業存在很大差異;剔除公司當年被ST/PT的研究樣本,因為此類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都經過了一定處理;剔除財務數據存在缺失的公司樣本。經過上述處理后,本文共得到18218個公司-年度樣本。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采用研發支出和專利申請數量作為企業自主創新策略的替代指標,由于企業研發支出數據可獲得起始年份為2007年,故當用研發支出作為被解釋變量時公司-年度樣本值縮減為13225個。為降低數據極端值對研究結論產生干擾,本文對公司層面的連續變量在1%和99%分位處做了縮尾(Winsorize)處理。本文所用到的數據除通貨膨脹(INF)是根據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的CPI指標計算外,其他企業層面的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和萬德數據庫(Wind)。
(二)變量定義
1.通貨膨脹。借鑒已有研究[12][13][14][6],本文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每年度環比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為基礎,對每年度的通貨膨脹率進行計算,計算方法為:INF=(CPIt-CPIt-1)/CPIt-1,INF表示當年度相對于上一年度CPI的通貨膨脹率。為避免通貨膨脹率的度量偏差,在穩健性檢驗部分,本文還采用了以省級層面為基礎的CPI年度數據計算通貨膨脹率。
2.產業政策。中國政府近年來出臺了一攬子的宏觀經濟政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五年規劃”為核心的產業政策。本文借鑒已有研究[19][20][25],以上市公司所屬行業的三位代碼為依據,參考“五年規劃”中的產業發展計劃,以確定上市公司是否屬于長期經濟政策中的扶持性行業,并設置虛擬變量INDP:若上市公司所處行業屬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積極扶持發展的行業,則對INDP賦值為1;其他則賦值為0。
3.企業自主創新。已有關于企業創新的文獻等分別從創新投入(研發支出)和創新產出(專利申請)兩個方面衡量企業的自主創新策略[25][26][27][28][29]。本文同時采用研發支出和專利申請數量表示企業的自主創新水平。具體來講,為體現企業創新的絕對和相對水平,我們分別對研發支出取自然對數和使用總資產進行標準化;對專利申請數量我們以發明、外觀設計和實用新型三種專利加總后取自然對數,用PATE表示。為了與通貨膨脹指標的口徑相一致,我們對這三個指標進行了差分處理,變量符號分別用RD1、RD2和PATE表示。
(三)模型設計
借鑒已有關于企業創新的文獻[25][26][29][27][28],本文構建了以下模型以分別檢驗假設H1、H2a和H2b,即通貨膨脹、產業政策對企業自主創新的影響。待檢驗模型如下:
Innovationi,t=α0+α1INFi,t+αX′+εi,t
(1)
Innovationi,t=α0+α1INFi,t+α2INF*INDPi,t+α3INDPi,t+αX′+εi,t
(2)
在上述兩個模型中,模型(1)用于檢驗通貨膨脹對企業自主創新的影響,Innovation表示企業自主創新水平,分別用取自然對數后的研發支出(RD1)、使用總資產進行標準化的研發支出(RD2)以及取自然對數的專利申請數量(PATE)表示;INF表示通貨膨脹率。模型(2)用于檢驗以“五年規劃”為核心的長期性產業政策的調節作用,INDP表示企業是否受到產業政策扶持的變量,交互項INF*INDP的系數表示長期性產業政策對通貨膨脹與企業自主創新的調節作用。
在兩個模型中,X表示控制變量,參考已有關于企業自主創新影響因素的文獻[25][26][27][28][29],控制企業規模(SIZE)、財務杠桿(LEV)、資產凈利潤率(ROA)、前五大股東的集中度(STRU)、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GROW)、經營凈現金流(OCF)、財務費用(CWFY)及現金持有水平(CASH)等變量。變量的符號、名稱和計算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的定義
續表

符號名稱計算方法GROW企業成長性企業營業收入增加率,等于(當期營業收入-上期營業收入)/上期營業收入STRU股權結構企業前五大股東的持股集中度,等于前五大股東持股的赫芬達爾指數CWFY財務費用企業每年支付的財務費用,等于財務費用除以總資產OCF經營凈現金流企業經營活動產生的凈現金流,等于經營活動的凈現金流/期末總資產CASH現金持有水平企業現金持有比率,等于(貨幣資金+交易性金融資產)/期末總資產Year年度固定效應設置年度虛擬變量,當企業位于該年度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Industry行業固定效應設置行業虛擬變量,當企業位于該行業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四、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兩個研發投入變動的指標RD1和RD2的均值分別為0.9993和0.0012,專利申請變動的指標PATE為0.0728,都大于0,說明從平均意義上來講樣本公司的自主創新水平在逐年提升;標準差分別為4.6668、0.0085和0.7042,說明這三個指標在樣本公司間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通貨膨脹變動指標INF的均值為-0.0002,基本接近于0,說明在樣本區間內每年通貨膨脹率變化不是太大;中位數為-0.0005,與均值大致持平,說明通貨膨脹率指標基本服從正態分布。產業政策指標INDP的均值為0.6830,說明在樣本區間中,大約有68%的公司處于產業政策的扶持行業內,這與陸正飛和韓非池(2013)[19]、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25]等的研究中所報告的數值差別不大;標準差為0.4653,說明在每個“五年規劃”中,受扶持的產業對象存在一定變化。其他變量的分布均在合理范圍。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回歸分析
1.通貨膨脹與企業自主創新。表3報告了通貨膨脹對企業自主創新的回歸結果。其中,回歸(1)和(2)中使用RD1作為企業自主創新指標,但回歸(1)沒有加入影響企業自主創新的控制變量,僅控制了年度和行業效應,回歸(2)則進一步控制了如公司規模(SIZE)、財務杠桿(LEV)和盈利能力(ROA)等控制變量,此時INF的估計系數分別為24.8442和26.8020,且都至少在10%水平上顯著;回歸(3)和(4)使用RD2作為企業自主創新指標,INF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1906和0.1603,在1%水平上與RD2顯著正相關。回歸(5)和(6)將企業自主創新指標替換為PATE,INF的系數仍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上述實證結果表明通貨膨脹率的相對上升越多,企業自主創新水平提升越多,假設H1得到驗證。

表3 通貨膨脹與企業自主創新的回歸結果
注:在公司層面cluster,采用穩健(robust)估計;括號內為t值;*表示p<0.1,** 表示p<0.05,*** 表示p<0.01。下同。
2.通貨膨脹、產業政策與企業自主創新。表4報告了通貨膨脹、產業政策與企業自主創新三者關系的回歸結果。與表4的結構類似,在回歸(1)至(6)中,我們分別以RD1、RD2和PATE作為企業自主創新的衡量指標。同樣,在回歸(1)、(3)和(5)中,我們沒有加入控制變量,僅對企業所處行業和年度進行了控制;在回歸(2)、(4)和(6)中,我們還控制了公司規模(SIZE)、財務杠桿(LEV)和盈利能力(ROA)等因素。從各列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交互項INF*INDP的估計系數都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說明,以“五年規劃”為核心的產業政策為扶持性產業內的企業提供了更多投資機會,導致其對通貨膨脹與企業自主創新的正向關系具有擠出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通貨膨脹下企業的自主創新行為,假設H2b得到驗證。

表4 通貨膨脹、產業政策與企業自主創新的回歸結果
續表

變量(1)RD1(2)RD1(3)RD2(4)RD2(5)PATE(6)PATELEV-0.22570.0008**-0.0336(-1.1810)(2.1546)(-1.5788)ROA1.21550.0085***0.2900***(1.6353)(6.0102)(3.7526)GROW0.2015-0.0048***-0.0060(1.4523)(-9.5163)(-0.3303)STRU-0.7436***-0.00070.0509*(-2.6409)(-1.2601)(1.7056)CASH-0.5639**0.00000.0224(-2.1353)(0.0051)(0.6153)CWFY8.6620**-0.0225***0.1658(2.2979)(-3.1417)(0.3865)OCF1.1770**0.0007-0.0024(2.3349)(0.7808)(-0.0378)Constant-3.8949***-3.7118***0.0000-0.0017-0.3646-0.6560*(-5.4418)(-5.0231)(0.0219)(-0.8055)(-1.0801)(-1.9056)YearYesYesYesYesYesYesIndustryYesYesYesYesYesYesN132251322513225132251821818218F12.982411.925310.921210.44177.88577.9950Adj-R20.03340.03450.03040.05740.00590.0064
五、進一步檢驗
(一)通貨膨脹與企業自主創新的進一步分析
1.實質性創新還是策略性創新。前文的分析支持了研究假設H1和假設H2b,即通貨膨脹下企業會增加自主創新水平對沖通貨膨脹產生的風險,但產業政策由于為扶持性企業提供了更多了投資機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對通貨膨脹下企業的自主創新水平具有擠出效應。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提出[25],我國專利申請的三種類型——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從其中的技術含量來看,可以進一步歸納為兩類:實質性創新(發明)和策略性創新(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實質性創新的質量高、難度大,是企業形成核心競爭力的主要來源,而策略性創新設計的技術含量較低,更多體現企業在特定情境下的策略行為,如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就發現,在具有產業傾向性政策扶持下,企業為尋求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會增加策略性創新行為[25]。基于此,本文試圖分析在通貨膨脹相對上升時,企業是實施實質性創新還是策略性創新。從邏輯上分析,由于通貨膨脹相對提升,實實在在地增加了企業的流動性資產貶值等風險,此時進行策略性創新顯然不能對沖通脹風險,因此我們預期通貨膨脹與企業自主創新的正相關關系更多體現在實質性創新。
表5報告了區分實質性創新和策略性創新后的回歸結果。其中,PATE1表示策略性創新,PATE1=Ln(1+外觀設計+實用新型);PATE2表示實質性創新,PATE2=Ln(1+發明)。INF的估計系數在回歸(1)中不顯著,在回歸(2)顯著為正,即通貨膨脹下企業顯著增加了實質性自主創新行為,但對策略性創新不存在顯著的影響。我們進一步結合產業政策,對通貨膨脹下企業的自主創新類型進行了分析,如回歸(3)和(4)所示,當PATE1為被解釋變量時,交互項INF*INDP的估計系數為負但不顯著;當PATE2為被解釋變量時,INF*INDP的估計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說明產業政策僅對扶持性企業在通貨膨脹下的實質性創新具有擠出效應。

表5 實質性創新還是策略性創新
2.通貨膨脹、企業自主創新和企業價值。前文的回歸結果表明,當通貨膨脹相對上升時,企業也會相應增加自主創新水平以對沖通貨膨脹產生的風險。那么,企業基于通貨膨脹下的自主創新策略是否真的有效對沖了潛在的風險呢?基于此,我們以企業價值作為企業自主創新策略的經濟后果,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檢驗。

表6 通貨膨脹、企業自主創新與企業價值
表6報告了通貨膨脹、企業自主創新對企業價值的回歸結果。參考已有文獻[14][25],我們以Tobin’Q作為企業價值的替代指標。從表6的回歸(1)至(3)可以看出,交互項INF*RD1、INF*RD2和INF*PATE的估計系數都至少在1%水平顯著為正,這說明通貨膨脹下企業增加的自主創新水平確實對沖了通貨膨脹可能產生的風險,增加了企業價值。沿襲前文的研究思路,我們進一步將專利申請數量PATE分為策略性創新PATE1和實質性創新PATE2,回歸結果見列(4)和(5)。我們發現,INF*PATE1與企業價值的關系正相關但不顯著,INF*PATE2在1%水平上與企業價值顯著正相關。也就是說,當通貨膨脹相對上升時,僅實質性創新能對沖通貨膨脹的風險,并相應的提升企業價值,而策略性創新則不具有該效應。
(二)對產業政策影響路徑的分析
陸正飛和韓非池(2013)指出,產業政策對扶持性企業存在投資機會和融資約束雙重效應[19]。前文的實證結果表明產業政策主要通過投資機會路徑影響通貨膨脹時企業的自主創新,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產業政策的融資約束路徑。基于此,本文試圖對產業政策的影響路徑做進一步的檢驗。
1.以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為基準對樣本進行分組。以往研究認為企業產權為國有性質、當年具有較低的財務杠桿和企業發放現金股利更多時,其融資約束程度相對較低[19][39]。基于此,本文以這三個指標為基準劃分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具體來講,對于產權性質,以國有和非國有為基準進行分組,將國有企業歸類為低融資約束組;對于財務杠桿和現金股利,本文以財務杠桿(LEV)和企業當年發放的現金股利(DIVIDENT,總資產標準化)為基準將樣本分為3個等分區間,若企業的財務杠桿處于下3分位區間內或現金股利處于上3分位區間內,歸類為低融資約束組。對于融資約束低的企業而言,產業政策提供的融資扶持作用較低,其作用更多地體現在為企業提供了相對較多的投資機會。因此,如果在融資約束較低的組,產業政策能夠降低通貨膨脹上升時企業的自主創新水平,則認為產業政策主要通過投資機會路徑影響通貨膨脹與企業自主創新的關系。
表7報告了基于上述分析的回歸檢驗結果。這里仍以RD1、RD2和PATE作為企業自主創新變動的指標,可以發現,在各列回歸結果中,交互項INF*INDP的估計系數基本都至少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PATE作為被解釋變量的結果未列示,結果相似)。上述結果表明在控制融資約束路徑后,其投資機會路徑依舊存在,且在一定程度上擠出了通貨膨脹時企業的自主創新水平。

表7 產業政策如何影響通貨膨脹下低融資約束企業的自主創新
2.為得到更穩健的結論,本文還參照陸正飛和韓非池(2013)的方法,通過構建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指數,并作為控制變量放入回歸模型中,考察在企業融資約束既定的情況下,產業政策對通貨膨脹與企業自主創新的調節作用[19]。鞠曉生等(2013)指出,相對于其他指標,SA指數可能更加準確[33]。其計算方法為:SAINDEX=-0.737*Size+0.043*Size2-0.04*Age。表8報告了對企業融資約束程度的變量進行控制后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在控制了反映企業融資約束程度的因素后,交互項INF*INDP的估計系數在分別以RD1、RD2和PATE作為企業自主創新變量的回歸中,都至少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這進一步說明產業政策確實為扶持性企業提供了更多的投資機會,企業投資機會路徑是影響產業政策和企業自主創新的主要路徑。

表8 控制企業融資約束程度的影響
六、穩健性檢驗
(一)通貨膨脹的指標敏感性檢驗
在前文的檢驗中,我們采用了已有文獻普遍衡量通貨膨脹的方法,即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每年度環比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為基礎,計算每年度的通貨膨脹率[6][12][13][14]。為了保證結論的穩健性,本文借鑒饒品貴和羅勇根(2016)的研究,采用省級層面的CPI年度數據來計算每個省份的通貨膨脹水平[6]。在替換通貨膨脹指標后,回歸結果與前文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結論不受通貨膨脹度量指標的影響。
(二)回歸估計模型的敏感性檢驗
許多短期內不易隨時間而改變的企業固定因素可能對企業自主創新存在影響,比如企業文化等,從而造成本文的回歸結果估計偏差。基于此,為避免這些可能的遺漏因素,本文使用固定效應的估計方法重新對前文的模型(1)和模型(2)進行回歸。基于固定效應的回歸檢驗結果與前文實證結果一致,表明本文結論并不是由于這些遺漏因素所導致。
七、結論與啟示
通貨膨脹風險的微觀傳導機制具有“隱形性”特征,本文聚焦于通貨膨脹下企業的自主創新行為,基于2003~2014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研發支出與專利申請數據,結合以“五年規劃”為核心的產業政策,研究發現:當通貨膨脹率相對上升時,企業會相應增加自主創新水平,并且這種創新更多體現在創造發明等具有較高難度和技術含量的實質性創新,而非外觀設計等策略性創新行為。這表明在通貨膨脹風險影響下,企業會采用相應的對沖策略以積極應對該風險,同時本文的研究也表明企業基于自主創新的風險對沖策略確實能夠提升通貨膨脹上升時企業的價值;產業政策對通貨膨脹下企業的自主創新行為存在調節效應,在產業政策扶持下,企業可以獲得更多的投資機會,在一定程度上對企業自主創新行為具有擠出效應。根據以上研究結論,本文對于企業管理實踐和政府政策規劃具有一定啟示意義:
(1)從企業管理實踐的角度來講,流動性資產特別是貨幣性資產對通貨膨脹具有較強的敏感性,在高通貨膨脹時期,企業將因持有過多流動性資產而承擔價值減損的風險。因此,在通貨膨脹波動時,企業決策者應當意識到通貨膨脹潛在的貶值效應,重新權衡貨幣性資產持有與支出的比重關系。本文從企業自主創新的角度,進一步為企業管理者提供了有效對沖通貨膨脹貶值風險的管理方式以及經驗證據。
(2)從政府政策規劃的角度來講,目標通貨膨脹的宏觀調控和管理是中央政府經濟政策制定重要的參考指標,本文的研究結論為產業政策在通貨膨脹相對上升時的調控作用提供了經驗證據。產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企業基于通貨膨脹風險管理動機的自主創新行為。因此,政府部門的政策制定者在思考和籌劃產業政策時,不應忽略通貨膨脹風險傳導機制下微觀企業的風險管理行為,從而避免宏觀調控過激或不足。宏觀定向調控時應關注微觀企業預期行為,避免調控政策失效或出現政策風險,以更加有效地引導企業自主創新,從而實現產業結構升級轉型。
當然,本文的研究也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本文發現產業政策的投資機會效應是影響通貨膨脹與企業自主創新的主要作用路徑,但由于數據可獲得性,本文并沒有檢驗這些具體的投資機會是什么,也沒有深入分析產業政策為扶持性企業提供的投資機會中,哪一種投資路徑對于通貨膨脹相對上升時企業自主創新的擠出效應更強,后續研究中可以在此方向下繼續深入探討,以得到更為詳實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