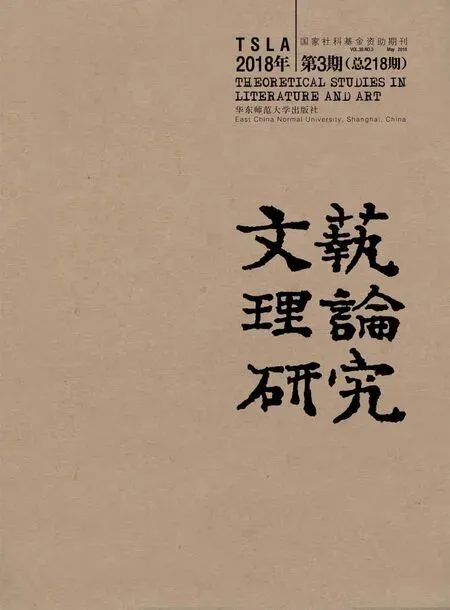賀拉斯詩歌與奧古斯都時期的文學秩序
李永毅
屋大維統治下的奧古斯都時期是古羅馬詩歌的鼎盛期。在這個歷史階段,詩歌創作變得空前復雜,詩人不僅需要忍受傳統的重負——延續千年的古希臘和泛希臘詩歌,而且還要適應新的文學秩序——由皇帝(國家)、權臣(恩主)、友人和公眾(敵對詩人與普通讀者)構成的龐大體系。該秩序的兩大核心要素則是贊助體制和流通機制,前者迫使詩人在藝術與權力之間周旋,后者以文學趣味和審美風尚的形式向詩人施加影響。這個體系之所以可稱為一種“秩序”,是因為羅馬國家這個決定性因素的加入,并且它有讓文學為皇權服務的強烈意圖。在古希臘和羅馬的共和國時期雖然也存在貴族對作家的贊助,但它主要體現的是個人影響力,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場,因而也不實質性地控制作品的流通。僅僅一代人之前,古羅馬詩人還有相當大的自由空間,以卡圖盧斯為例,他既可以置身贊助體制之外,毫無顧忌地奚落甚至辱罵愷撒等權貴,也可以斷然摒棄普通讀者,以驚世駭俗的方式挑釁流行的閱讀期待。奧古斯都時期的賀拉斯則不得不以現實的態度對待文學秩序中的各個環節,通過精心設計的寫作策略來保護作品的藝術性,避免淪為這個秩序的犧牲品。
一、終極恩主與國家的遙控
當賀拉斯在創作生涯晚期決定放棄抒情詩、改寫書信體詩的時候,他將自己比作一位退休的角斗士,并稱繼續寫抒情詩是將自己“困于原來的游戲中”(Horace:Satiresand Epistles 1.1-3)。“游戲”(ludi)在拉丁語中常指以角斗士對決、人獸搏斗、集體處決為內容的競技慶典。有論者認為賀拉斯這里不過是自嘲(Macleod 286),鮑迪奇卻敏銳地讀出了其中的深意。雖然競技慶典最初只是葬禮上的一種獻祭儀式,但到羅馬共和國晚期,它已經成為政客籠絡底層民眾的重要手段(Veyne 222)。當他們花費巨資舉辦這樣的慶典,邀請羅馬貧民無償觀賞時,扮演的是用禮物換取忠心的恩主角色。鮑迪奇指出,賀拉斯在創作政治抒情詩的時候,也是以對羅馬民族的忠心換取羅馬國家的賞賜。在此過程中,屋大維——羅馬國家的代表——就成了賀拉斯的終極恩主。于是,一個恩主經濟的鏈條浮現出來:羅馬皇帝(直接或通過臣屬)賜給詩人土地和財物,詩人則以作品相回報,而在更大的文化流通機制中,詩人的作品又成了羅馬皇帝贈予公民群體的禮物,如同角斗士表演一樣(Bowditch 2-3)。或許正因如此,與禮物相關的詞匯在這首詩中反復出現。這表明,賀拉斯對自己的文化角色有深切的認識,他后來轉向書信體詩也是擺脫束縛的一種嘗試。事實上,羅馬國家并不只是賀拉斯一人的終極恩主,奧古斯都時期幾乎所有的重要詩人都受制于屋大維的恩惠:史詩作家維吉爾和瓦里烏斯,愛情詩作家提布盧斯和普洛佩提烏斯,悲劇作家弗斯庫,喜劇作家方達紐,都是如此。拒絕順從屋大維的奧維德,則被流放黑海地區,逐出贊助制度的保護網。賀拉斯詩集中頌君之作(比如《頌詩集》第4部第5首、第15首)和奉命之作(《頌詩集》第4部第4首、第14首、《書信集》第2部第1首)都直接體現了羅馬國家對詩人的政治壓力。
根據吉拉爾(Girard 41)和鮑迪奇的分析,賀拉斯與角斗士的聯系尤其體現在他的羅馬頌詩(《頌詩集》第3部第1—6首)中。如果說角斗士的獻祭是為了平息地府諸神的怒氣,那么賀拉斯的這些政治抒情詩則融合了悲劇的因素,是一種象征性的公共祭祀,代表繆斯為羅馬內戰的屠戮贖罪,以恢復被內戰摧毀的和平以及等級秩序(Bowditch 27)。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是獻給羅馬國家、回報羅馬贊助的禮物。
贊助體制確保了賀拉斯在經濟上衣食無憂,在政治上受到保護,但它始終對他的創作自由構成了潛在的威脅。澤特澤爾等學者傾向于認為,賀拉斯沒有屈從于贊助體制的壓力(Zetzel 87-102),最終保持了創作的獨立。懷特等人則相信,賀拉斯是由衷認同屋大維的政治文化立場的(White 161)。戈爾德(Gold 66)和普特納姆(Putnam 147-53)等人雖然承認贊助體制是奧古斯都時期的普遍文學現象,但相信恩主對詩人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賀拉斯認可了屋大維羅馬救星的角色,但這種認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一方是有遠大文學抱負和獨立創作軌道的詩人,一方是睥睨天下、決意將文學納入帝國秩序的君主,兩人之間的關系注定是緊張而復雜的。總體而言,賀拉斯對屋大維的態度經歷了從警惕、懷疑到接受、崇拜的過程,但他自始至終都不肯做一位馴順的宮廷詩人。
《世紀之歌》標志著賀拉斯正式成為羅馬的桂冠詩人。這首詩作于公元前17年,是一首宗教頌歌,在世紀慶典(ludi saeculares)上由27名少男和27名少女演唱。世紀慶典的原型是瓦雷利婭家族向冥界諸神獻祭的儀式。公元前17年,屋大維已經作為國家元首統治十年,羅馬享受著和平與繁榮,屋大維有意把這個贖罪消災的儀式改造為祈福感恩的儀式,并將他認可的個人保護神阿波羅確立為羅馬的國家神,于是策劃了這個慶典,并命令賀拉斯創作一首頌歌。
這是一首典型的應制詩,又需在儀式上演唱,賀拉斯沒有多少自由發揮的余地,更重要的是,他不可避免地要對屋大維治下的羅馬做出評價。賀拉斯的應對策略一是借道維吉爾來稱頌屋大維,避免給人以阿諛的印象,二是刻意避免意識形態之爭,突出羅馬民族利益的匯聚點。直接涉及屋大維的內容主要是以下三節(49—60行):
愿安基塞斯和維納斯的杰出后裔
實現他用白牛向你們獻祭時祈求的
一切,用武力摧垮頑抗的強敵,
卻寬宥臣服者。
海上和陸上,我們強大的兵力
和羅馬的戰斧已讓美地亞震恐,
斯基泰和傲慢的印度也急于獲知
我們的命令。
忠誠、和平、榮譽、古時的純潔
和久遭冷落的勇武已經敢回返,
吉祥的豐饒神也重新出現,她的
羊角已盛滿。
“安基塞斯和維納斯的杰出后裔”指屋大維,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將屋大維和他所在的尤利婭家族塑造為埃涅阿斯之子尤盧斯(Iulus)的后代,而埃涅阿斯據說又是安基塞斯和維納斯的兒子。“用武力摧垮頑抗的強敵,/卻寬宥臣服者”顯然呼應著維吉爾《埃涅阿斯紀》中的一個著名段落,父親安基塞斯的鬼魂在地府向埃涅阿斯展示羅馬偉大的未來,強調羅馬統治世界乃是神的諭旨:“羅馬人,記住,用你的權威統治萬國,/這將是你的專長:確立和平的秩序,/寬宥溫馴之民,用戰爭降伏桀驁者”(Virgil 6.851-53)。維吉爾于公元前19年去世時,《埃涅阿斯紀》在古羅馬文學中的經典地位已經確立,成為古羅馬史詩的代表。賀拉斯的措辭無疑會喚起聽眾對維吉爾作品的記憶,在羅馬人看來,賀拉斯是以一種謙遜的姿態向這位已逝的同行致敬,從而沖淡了這首詩歌功頌德的味道。后面兩節直接描繪屋大維成就,突出了三個方面:羅馬強盛的軍力、奧古斯都時期整肅道德的努力以及和平局面帶來的經濟繁榮。即使反對屋大維的人也無法否認這些成就,在此框架下,共和與帝制的分歧至少在表面上彌合了,這首《世紀之歌》因而也具備了代表整個羅馬民族發聲的超越性。
一方面,賀拉斯以民族先知自命,因而無法真正避開政治話題,而他的政治見解與屋大維的官方立場存在相當距離,這使得他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必須慎之又慎。另一方面,他在詩學觀念上深受泛希臘時代詩人卡利馬科斯及其羅馬傳人——以卡圖盧斯為代表的新詩派——影響,極力強調技藝的重要,并試圖保持作品的私人化色彩,這進一步加大了創作政治詩歌的難度。然而,賀拉斯卻憑借精巧的構思和高超的文字駕馭能力,在政治意圖和詩學追求之間達到了艱難的平衡。《頌詩集》第1部第8首就是很好的例子。
呂底婭,天上地下,
諸神作證,為何急于用你的愛摧垮
敘巴里?他為何憎惡
明亮的原野,不再忍受曝曬與塵土?
他為何遠離了同伴,
不再一起馳騁,緊勒狼牙的鐵銜,
決意讓高盧馬馴服?
他為何害怕棕黃的臺伯河?為何畏懼
橄欖油甚于蝰蛇血,
那雙因練習投擲而瘀青的手臂為何
不再示人?輕松
越界的鐵餅、標槍曾給他怎樣的聲名!
他為何躲藏,就如
傳說中忒提斯的兒子,在特洛伊悲劇
揭幕前,擔心男裝
會將他推向敵人的戰陣,推向屠宰場?
這首詩寫給一位名叫呂底婭的女子。莫爾指出,就主題而言,這首詩或許只是希臘式的仿作或練筆,至少普勞圖斯就曾在戲劇中以相似的文字處理過這個陳舊的希臘主題——愛情讓青年人變得萎靡(Plautus 149 ff)。然而,這種理解忽略了作品的羅馬政治語境和詩末阿喀琉斯典故的意義。第4行的戰神廣場(“明亮的原野”)、第7行的高盧馬和第8行的臺伯河共同構成了這首詩的羅馬背景,體育鍛煉和軍事訓練不可避免地糾纏在一起。軍事訓練是為從軍做準備,而在羅馬,從軍是從政的必備步驟。如果這樣,敘巴里不僅為了愛情而荒廢了身體,甚至也放棄了政治前途(Dyson 164)。
詩的13—16行引用了后荷馬時代流傳的一個關于阿喀琉斯的故事。該故事的情節記錄在阿波羅多洛斯(Apollodorus)的《希臘神話》中(Apollodorus 3.13.8)。阿喀琉斯的母親忒提斯在特洛伊戰爭爆發前得知了兒子會戰死的命運,于是將他裝扮成女人,藏在斯庫羅斯國王呂科梅迪斯的女兒中間。在此過程中,他和其中一位公主代達米亞產生了愛情。后來奧德修斯化裝成小販前來,在貨物里混了一些武器,阿喀琉斯因為表現出對武器的興趣而暴露了身份(Ovid 13.162 ff)。詩中的“悲劇”和“屠宰場”等措辭突出了特洛伊戰爭的負面形象。奎因評論道,由于后文特洛伊典故的存在,4—7行的意象所表達的敘巴里對體育鍛煉的憎惡態度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體育鍛煉是軍事訓練的一部分,其終點是毀滅性的戰爭,那么避之不及就是正常的反應(Quinn 137-41)。不僅如此,正如阿喀琉斯躲避戰爭并非出于本意,而是由于母親擔心他會戰死,敘巴里躲避體育鍛煉(其實也是軍事訓練)也并不一定代表他的立場,而是反映了呂底婭的擔憂。如果這樣,她就并非用情欲消磨戀人陽剛氣質的壞女人,而是真心關懷他的好女人。和傳統的解讀相反,詩歌的中心不是敘巴里,而是呂底婭。
賀拉斯以這種獨特的方式,既利用了希臘傳統又顛覆了希臘傳統,并隱晦地提供了一種不同于屋大維軍國主義宣傳的視角。由于反戰的情緒是由不直接卷入戰爭、而且在文學傳統中一向反戰的女人表達出來的,賀拉斯就避免了給讀者直接反對屋大維的印象。
從上面這些作品可以看出,在不觸怒屋大維的前提下,賀拉斯始終堅定地維護自己的人格獨立和創作自由,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絕不甘心做一位御用詩人。在藝術上,他追求的是無可挑剔的技巧和完美的風格;在精神上,他矢志成為整個羅馬民族(而不是屋大維)的代言人。他永遠不愿為了政治而犧牲詩歌本身的價值。
二、直接恩主與贊助體制下的友誼
研究奧古斯都時期的文學贊助體制面臨一個難題,就是它與政治領域的贊助體制有很大不同,后者的恩主與門客之間的關系較為直接明顯,因而容易判定。詩人大多出身騎士階層,學識上的優越感讓他們恥于將他們與恩主的關系視為一種贊助體制。按照西塞羅在《論義務》中的說法,對于社會地位較高的羅馬人來說,“被人稱為門客,或者承認受惠于贊助體制,和死一樣難以忍受”(Cicero 2.69)。因此,文學贊助體制的雙方更愿意使用“友誼”(amicitia)和“朋友”(amici)這類軟性詞匯來掩飾二者在社會地位上的差異。不僅如此,從許多作品可以看出,在賀拉斯與麥凱納斯的關系中,彼此的尊重甚至敬愛是顯然存在的。懷特據此認定,“文學贊助體制”的說法并不準確,他經過仔細考證得出結論:無論羅馬政府還是權貴都沒有對詩人進行制度化的資助,也沒有刻意塑造其文學產品(White 155)。
然而,正如鮑迪奇所說,懷特的觀點只考慮了贊助體制的物理形態,未考慮其心理形態。作為一種禮物經濟,贊助體制更強大的驅動力在于負債的心理和感恩的心態(Bowditch 21)。高明的贊助人會竭力保持無償贈予的姿態,避免產生對等交換的印象,既為自己贏得慷慨開明的名聲,也防止詩人在強烈負債心理的驅使下表現得過分急功近利,從而降低他們的身價。贊助人甚至希望看到詩人保持獨立的人格,從而讓外人看來,這種關系不是基于利益交換,而是一種自愿自發的行為。這種態度為真實友誼的生長提供了空間,但仍不能消弭兩人關系的贊助性質。
薩勒看到了贊助體制的復雜性,指出它必須包含三重關系:“第一,它涉及物品和服務的交換;第二,為了與市場上的商業交換相區分,它必須是具備持續性的私人關系;第三,它必須是不對稱的,也即是說,雙方的社會地位不平等,他們交換的物品和服務也不對等——正是這點有別于平等者之間的友誼”(Saller 1)。賀拉斯與麥凱納斯的關系無疑具備上述三個要素。鮑迪奇提醒我們,麥凱納斯贈予賀拉斯的不僅有最重要的物質財產——土地,更賜給了他一種身份和地位,擁有土地本身就是獨立經濟地位的保證和獨立人格的象征,更不用說麥凱納斯的庇護促進了賀拉斯文學聲名的傳播。正因如此,賀拉斯在詩中不僅經常感謝麥凱納斯的慷慨,更稱他為自己的“堅盾”和“甜美榮譽的源頭”(Odes 1.1.2)。
對比前輩詩人卡圖盧斯,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贊助體制在賀拉斯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在愷撒內戰前,詩人在古羅馬社會中的地位遠更邊緣化,并未與權貴結成穩固的交換關系,至少還有選擇放棄贊助體制庇護的自由。卡圖盧斯毫不留情地鞭撻了愷撒集團通過戰爭聚斂財富、壟斷政府高層職位、縱容手下搜刮行省等行為。愷撒、庇索、瑪穆拉、龐培、瓦提尼烏斯都是卡圖盧斯攻擊的靶子。
賀拉斯與麥凱納斯的交往則綿延近三十年,幾乎貫穿了他的文學生涯。在他的全部162首詩里,直接寫給麥凱納斯的詩就多達16首,而且從早期的《諷刺詩集》到中期的《頌詩集》再到晚期的《書信集》里都有。麥凱納斯不僅是賀拉斯詩歌題獻的對象,也是欣賞其作品的知音,進行詩學探討的良伴。但賀拉斯始終清醒地意識到橫亙在兩人之間的社會鴻溝。在《書信集》第1部第7首里,他對麥凱納斯說,“你經常夸我謙恭,總稱你‘主公’‘前輩’,即使不在你身邊,我也不吝于贊美”(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 1.7.37-8)。“謙恭”(verecundum)一詞極少用來形容同等地位的人,如果說“前輩”(pater)還只是對長輩的一般尊稱,“主公”(rex)則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二者的尊卑位次。在外人眼里,賀拉斯與麥凱納斯之間也是不折不扣的門客與恩主的關系。
但是另一方面,在《諷刺詩集》第1部第6首里,賀拉斯竭力說服讀者,這段關系并非一種利益聯盟,而是以人格吸引為基礎的友誼(49—64行)。他首先為麥凱納斯的動機做了申辯,指出他“不屑收買人心”,詩人這里顯然批判了古羅馬政客盛行的做法,即通過禮物和賞賜來網羅門客,從而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他特別強調麥凱納斯擇友的嚴格而睿智的標準——不看財產和門第,而看“心地是否純潔”。然而,正因為兩人的私交甚密,要在這樣的關系中堅定地維護創作自由和人格獨立,而又不實質性地傷害到情誼,是非常困難的。總體來說,賀拉斯深諳拒絕的藝術,對作品的拿捏極其到位。
《書信集》第1部第7首的情境就直接威脅到了贊助體制的外在形式。賀拉斯在這年六七月間離開羅馬到山間度假,答應很快就回到麥凱納斯身邊,但后來卻改變了主意,于是麥凱納斯可能去信責備,催促他回城,賀拉斯便寫了這封信作答,稱自己要等第二年春天才回去。無論兩人的情誼多深,就地位而言,麥凱納斯畢竟是恩主,賀拉斯是門客,古羅馬門客對恩主最重要的義務便是在恩主需要時陪伴左右,這種行為幾乎是贊助體制的一個標志。賀拉斯在這里不僅拒絕履行這一義務,他還違背了羅馬人極為看重的另一義務——信守承諾。因此,賀拉斯在此詩里需要解釋的是對恩主的雙重冒犯。賀拉斯不想傷害恩主的感情,更不愿冒犯他的尊嚴,但同時也不肯犧牲自己的獨立。為了將自己的立場和理由闡述得更清楚,賀拉斯借助了史詩情節、寓言、故事和類比,委婉而堅決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從效果看,麥凱納斯顯然接受了賀拉斯的解釋,他允許后者公開發表這首詩,表明他認可其中的觀點,也容忍賀拉斯的獨立。賀拉斯敢于拒絕麥凱納斯的要求,并相信對方能夠原諒自己的拒絕,既表明了自己的真誠直率,也表明了對麥凱納斯人品的高度信任。如彼得森所說,這首詩在題材、主題、心理和意象的處理方面都實現了高度的統一,堪稱佳作(Peterson 309-14)。基帕特里認為,獨立只是作品的抽象主題,更具體的主題是恩主制度下的合適行為(decorum)問題,尤其是贈予與接受,西塞羅《論義務》中關于禮物的討論可以作為這首詩隱含的倫理框架。賀拉斯突出了自己的謙卑與感激,體現了作為禮物接受方的理想品質,他也稱贊了麥凱納斯的寬容與審慎,而這正是禮物贈予方的理想品質(Kilpatrick 47-53)。
按照西塞羅的說法,贈送禮物時,贈予者、禮物和受贈者三個元素都應恰當、恭敬。第一,禮物本身應當是受贈者愿意接受、并且對他有用的;第二,贈予者的態度必須審慎恭敬,不能草率傲慢(Cicero 1.14.49);第三,受贈者也應謹慎選擇,必須以品行為標準,具備各種美德,這樣禮物才得其所(Cicero 1.14.45-6)。如果麥凱納斯邀請賀拉斯在羅馬停留可以看作一種禮物,那么這個禮物本身雖然美好,對于此時的賀拉斯卻已經不恰當了,人過中年的他已經不喜歡繁華喧囂的羅馬城,“更愛空曠的提布爾、閑逸的塔倫頓”,他還給了一個謙卑的理由:“小地方適合小人物。”
賀拉斯的潛臺詞似乎是,如果自己在表面上遵守門客的義務,按期返回羅馬城,反倒會因為自己不再適應大城市而失去自己真心追求的生活,那樣就違背了麥凱納斯支持賀拉斯的初衷。所以,賀拉斯委婉的規勸后面也隱含了對恩主人格和智慧的贊揚。事實證明,他對恩主的判斷是準確的,這封拒絕的信其實也是巧妙的肯定,不僅沒有破壞兩人的關系,反而在更高層次上確認了一種基于友誼倫理的贊助體制。
三、詩友圈與創作共同體
賀拉斯將自己的作品獻給麥凱納斯,并不僅僅是作為門客向恩主表達忠誠,更是向這位知音傳遞深摯的感激之情。從賀拉斯的多首詩歌可以看出,麥凱納斯具備深厚的文學素養和高超的鑒別力,賀拉斯愿意和他討論高端的文學問題,也相信他的判斷。麥凱納斯的贊助對于他還有另外一重意義,因為在這位恩主身邊匯聚了奧古斯都時期最優秀的一群羅馬詩人,他們不僅用自己的創作和賀拉斯一起構成了絢爛的文學星座,也用自己的評論為賀拉斯提供了最有教益的參考。所以,麥凱納斯在為賀拉斯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的同時,也為他的才智創造了理想的生長空間。
賀拉斯在許多作品中都呈現了他與麥凱納斯的深情厚誼。兩人心照不宣的默契尤其體現在《頌詩集》第1部第20首里。賀拉斯邀請麥凱納斯來做客,卻友善地警告對方,自己沒有上等酒可以招待他,只有自己親自釀造的普通酒,但它的釀造日期對朋友來說很有紀念意義:
便宜的薩賓酒和樸素的陶瓶等著你,
是我親手藏進希臘的壇子,抹上
封泥,猶記當日人們正向你致意,
在寬闊的劇場。
麥凱納斯,我親愛的騎士,你先祖
居住的河流兩岸,還有梵蒂岡山,
那時都傳來快樂的回聲,仿佛
也把你頌贊。
你在家會喝凱庫布和卡萊斯榨酒機
征服的葡萄:可我的杯子,卻難讓
法雷努的藤蔓和福米埃的山谷親至,
賜給它醇香。
康馬杰指出,“羅馬的內容(酒),希臘的形式(酒器),簡樸的杯子,親身的勞動,所有這些都暗示,賀拉斯獻給恩主的真正禮物不是酒,而是這首詩本身”(Commager 326)。普特納姆也說,至少賀拉斯款待麥凱納斯的酒帶有詩的印記,詩中的許多用詞都兼有釀酒和作詩的雙重含義(Putnam 153)。古羅馬人通常用希臘的壇子盛放進口的希臘酒,賀拉斯卻把自己釀制的薩賓酒放在里面,似乎是為了吸收原來希臘美酒的味道,某種詩學隱喻呼之欲出。賀拉斯在這篇作品里實現了多重社交和藝術意圖。他真心感謝了麥凱納斯對自己的關心提攜,稱贊了恩主的輝煌功業和謙遜人格,并委婉地提醒這位摯友,財富、權勢之類的東西都是不可靠的,詩歌、藝術和美才是值得追求的。在此過程中,他也巧妙地表達了自己的詩歌理想。然而,這首詩最重要的一個前提是,賀拉斯深信麥凱納斯能夠理解自己在各個層面所傳達的信息。
賀拉斯并非不在意任何人的評價。他指明了自己心儀的讀者:“被自由的人們開卷展讀,多么歡愉”(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 1.19.34)。“自由的人們”就是不囿于成見、有獨立判斷力的讀者,這些讀者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麥凱納斯和圍繞在他身邊的一群詩人朋友。在他眼中,這是一個各得其所、各展所長的生態群落,而不是通常贊助體制下門客殘酷競爭、勢同水火的場面。在政治動蕩、戰亂頻仍的羅馬共和國晚期,能有這樣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學朋友在一起,讓賀拉斯倍感幸運。他是如此描繪自己與這些朋友的重逢的:
翌日的晨光尤其令人快慰,瓦里烏斯、
普羅裘和維吉爾在希努薩與我們會面,
世上從未誕生過比他們更純潔的心靈,
也不會有人與他們比我更親密無間。
多么幸福的擁抱,多么欣喜的重逢!
只要我不瘋,好朋友就是唯一的珍寶。(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 1.5.39—44)
維吉爾與賀拉斯的友誼自不必說,他被后者稱為“我的靈魂的另一半”(Odes 1.3.8)。普羅裘(Plotius Tucca)和瓦里烏斯(Lucius Varius Rufus)不僅是賀拉斯的好友,也在維吉爾死后編輯發表了《埃涅阿斯紀》,為后世保存了這部珍貴的史詩。在此之前,瓦里烏斯一直被公認為羅馬最好的史詩作家(Odes 1.6),此舉尤其顯示了他對文學同行的大度。阿里斯提烏·弗斯庫(Aristius Fuscus)也是賀拉斯的“密友”,他在《諷刺詩集》第1部第9首中被詩人幽默地暗比為阿波羅。
賀拉斯的詩人圈讓人聯想起前輩卡圖盧斯的朋友圈。卡圖盧斯的詩人朋友包括卡爾伍斯(Calvus)、欽納(Cinna)、法布盧斯(Fabullus)、維拉尼烏斯(Veranius)、凱奇利烏斯(Caecilius)、弗拉維烏斯(Flavius)、卡梅里烏斯(Camerius)、科爾尼菲奇烏斯(Cornificius)等人。這是一群寄情酒色、放浪形骸的人,然而他們之間卻有真摯的情誼,彼此分享快樂,互相欣賞才華,形成了一個“波希米亞詩人同盟”。卡圖盧斯《歌集》中涉及他們的作品總是與詩歌或詩學有關。在羅馬共和國晚期的新詩派時代(愷撒內戰之前),詩人群體更像現代主義藝術家的小群體,具有排斥大眾讀者的傾向,詩歌的私密性較強,正因如此,卡圖盧斯的許多此類作品都涉及讀者難以掌握的一些“內幕”信息,為后世留下了許多謎題。而在文學被納入國家秩序的奧古斯都時代,詩人卻需避免給人私密團體的印象,而要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發聲。所以賀拉斯雖有不少詩作寫給自己的詩人朋友,但在這些作品中(至少在表層)他們詩人的一面卻被淡化(Moritz 174-93)。《頌詩集》第4部第12首是一個極佳的例子:
春天的同伴,色雷斯的風已經吹來,
它讓大海恢復平靜,將船帆催動,
原野已不再被寒霜凝住,江河不再
浮滿冬雪,在喧響中奔涌。
燕子正在筑巢,這不幸的鳥為伊堤斯
悲泣,她成了刻克羅普斯家族永遠的
恥辱,只因她報復國王野蠻的淫欲時
手段過于殘忍邪惡。
鮮綠悅目的草地上,守護肥羊的牧人
用蘆笛吹奏著自己的旋律,喜歡牲畜、
喜歡阿卡迪亞幽暗山嶺的潘神
聽到了,心中也漾起歡愉。
季節帶來了渴的感覺,如果你期盼
喝到在卡萊斯釀造的葡萄酒,那么
維吉爾啊,你就必須拿香膏來交換,
你這年輕貴族的門客。
一小盒香膏就能誘來一罐上等酒,
此時它正在索皮契亞倉庫里安睡,
它會贈給你許多新希望,它也能夠
輕松洗去憂慮的苦味。
倘若這樣的快樂你已等不及,請火速
帶著你的貨物趕來,我不會打算
讓你白白在我的酒杯中盡情沐浴,
仿佛我真有家財萬貫。
但不要耽擱,不要追逐利益,別忘了
陰森的火等著我們,趁你還可能,
且用短暫的玩樂調劑思慮,適當的
時候,何妨扮一下蠢人?
和卡圖盧斯贈友之作不同,賀拉斯的這首詩至少在表面上突出的是世俗之樂。他和麥凱納斯經常都在作品里研討詩學問題,寫詩給維吉爾這位古羅馬第一詩人時,反而對詩歌只字不提(《頌詩集》第1部第3首也是如此),這未免讓人詫異。但如莫里茨所說,在文學趨于國家化的屋大維時代,結成卡圖盧斯式的遠離塵俗、秘密孤傲的詩人小群體已經是一種忌諱,賀拉斯需要刻意避嫌了。所以,讀者即使不知道賀拉斯及其詩友的任何背景,也能輕易理解和欣賞這首詩,而如果對新詩派作者和詩觀沒有相當了解,閱讀卡圖盧斯的相關作品則會遇到相當大的阻礙(Moritz 184-85)。
然而賀拉斯畢竟是卡圖盧斯隱秘的崇拜者,不會甘心自己的詩歌僅停留在“及時行樂”主題的表層。他的才能恰好在于,他既能被大眾讀者接受,又能在作品的深層像卡圖盧斯等前輩一樣,向自己的詩人同行透露秘密的信息。鮑拉在此詩中發現了多處模仿和影射維吉爾的表達方式,它們在賀拉斯作品中極其罕見,表明詩人是有心如此,以這種特別的方式向朋友致敬(Bowra 165-67)。 詩中的“風”(animae)、“催動”(impellunt)、“凝住”(rigent)、“鮮綠”(tenero)、“陰森的火”(nigrorum ignium)等詞都取自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農事詩》和《牧歌》,對熟諳維吉爾詩歌的讀者來說,賀拉斯的措辭表現了他對詩友的高度認可。
帶著這樣的意識回頭再讀,第四節香膏換葡萄酒的意象不也呼應了卡圖盧斯《歌集》第13首嗎?只不過角色調換了,作為主人的賀拉斯不再像卡圖盧斯那樣提供精神產品,而真地盡地主之誼提供葡萄美酒,作為客人的維吉爾卻需用“香膏”——詩歌的象征——來換取,這樣的安排暗示維吉爾的詩才在自己之上。因此,這首詩是賀拉斯詩歌圈友誼的見證。正是這種群體友誼最終超越了贊助體制下恩主與門客的雙向利益交換關系,形成了一個促進文學生長的良性環境,古羅馬詩歌在奧古斯都時期達到巔峰也就是自然的結果了。
四、評論家與匿名讀者群
古羅馬傳統的發表方式是朗讀和私下流傳,但在奧古斯都時期,圖書復制和銷售已經成為一項興盛的新產業,賀拉斯詩中數次提及的索西烏兄弟就是當時羅馬最大的書商。此外,隨著希臘化進程的加速和羅馬文學經典化的開始,文學成為奧古斯都時期主要的教育內容,專門講授和評論文學的老師(grammatici)也漸成氣候。所以,在贊助體制之外,賀拉斯需要應對的就是評論家和匿名讀者這兩個群體。
賀拉斯深知,在文學流通中,讀者永遠是作者不可控制的因素,因為讀者通常都懷著與作者不同的目的,雙方之間并非合作關系。《諷刺詩集》第2部第8首便體現了這一點。這首詩記述了一次失敗的宴會。主人納西丹精心準備了許多獨門秘制的菜肴,邀請麥凱納斯等人前來赴宴,但最后大部分客人沒吃完就溜走了。麥凱納斯是最尊貴的客人,他赴宴其實也是一種敷衍。在恩主和門客的利益交換機制盛行的古羅馬,在他看來,納西丹無非是另一個試圖巴結自己的富人而已。維比丟和巴拉洛是麥凱納斯的扈從,他們在社交場合永遠跟著麥凱納斯,不請自來,當然也不會尊重納西丹。客人中的瓦里烏斯、維斯庫、方達紐雖然是詩人,但在這個特殊的場合,他們并未把納西丹視為藝術家同行,而覺得他是一個一心往上爬的俗人。因此,自始至終,納西丹都未能將客人引入同情與理解的良性互動中,未能創造一個適合藝術鑒賞的環境。與納西丹相仿,詩人永遠不可能避開不被人欣賞的風險:“你的努力永遠/換不來與之相稱的名聲”(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 2.8.65-66)。在古羅馬尤其如此。在《書信集》第2部第1首中,賀拉斯辛辣地嘲諷了羅馬的戲劇觀眾缺乏起碼的藝術理解力,他們既不關注情節,更不能欣賞臺詞的語言,注意力都集中在服飾、布景等外圍元素上,幾乎把戲劇表演當作了他們熟悉的娛樂方式——競技慶典(194行—200行)。羅馬讀者甚至分不清生活與藝術的界限。他們之所以憎惡賀拉斯的諷刺詩,是因為他們習慣于對號入座,所以竟將揭示社會荒謬現象的詩人看成通過揭發他人而發財的政治告密者。
賀拉斯提醒讀者,自己詩中的人物只是類型的代表,更重要的是,詩人關注的是社會的道德水準和人生價值。如果這樣的作品羅馬讀者都無法接受,他就只能采用“強力”了。他幽默地威脅讀者:“如果你不肯容忍,一大堆/詩人會趕過來,做我的援軍(因為我們/人多勢眾),像猶太人那樣逼你就范,/直到你學會容忍我們這樣一群人。”他聲稱自己的諷刺詩是防御性的,但警告他人千萬不要故意冒犯自己,否則將“流芳千古”:
啊,眾神之主朱庇特,
愿我的長矛永遠廢棄,直到銹爛,
也別讓任何人傷害愛好和平的我!
可是如果我喊著“別碰我!”,還有人膽敢
挑釁,他會痛哭的,全城都將歌唱
他的美名。
對評論家的反駁,賀拉斯則采取了更專業的方式。不少人批評他的諷刺詩不如古羅馬諷刺詩先驅盧基里烏斯,賀拉斯卻指出,盧基里烏斯在道德和寫作方面缺乏自我控制(Anderson 9)。不僅如此,他還沒有分清藝術與生活的界限,這種觀念上的問題導致他在寫作時沒有篩選生活的細節,讓作品淪為日記。這兩個缺點恰好都是批評賀拉斯的大眾所犯的錯誤。通過這樣的辯護,賀拉斯為羅馬諷刺詩樹立了一種新的理想標準:理性、克制、詼諧、機智,而不沖動、放縱、尖刻、惡毒。在為自己的抒情詩辯護時,賀拉斯討論了一個重要的詩學問題:靈感與技藝孰輕孰重?他諷刺了過分相信靈感輕視技藝的“飲酒派”,而更傾向于以亞歷山大詩人卡利馬科斯為代表的“飲水派”(1—11行),這與他一貫諷刺人類的各種瘋狂、強調理性的道德立場是一致的。對于質疑自己的評論家,賀拉斯毫不退讓(35—40行):
你或許會問,為何有些人私下里其實
喜歡讀我的作品,出門就無節操地貶斥?
因為我不會追逐無常庸眾的選票,
請他們免費吃喝,送他們破舊的衣袍;
我是高貴文學作品的助選者、復仇者,
豈可屈尊去游說講壇上的評論家部落?
這里詩人借助古羅馬人所熟悉的選舉意象闡明了自己的立場。他“不會追逐無常庸眾的選票”,“無常”表達了賀拉斯對“庸眾”評價的蔑視。賀拉斯聲稱自己不屑于采用政客們的常用伎倆,請選民“免費吃喝,送他們破舊的衣袍”,也不會“屈尊去游說講壇上的評論家部落”,因為自己是“高貴文學作品的助選者、復仇者”。從擬人的角度看,高貴作品因為不受庸眾的歡迎而落選,現在賀拉斯要為它們贏得合理的位置,這樣的行為既可稱為“助選”,也可稱為“復仇”。至于“高貴作品”指什么,答案不難找,首先指賀拉斯崇拜的希臘詩人阿爾凱奧斯、薩福和阿齊洛科斯的作品,其次指繼承了這一傳統的賀拉斯自己的作品。
基于對評論家和讀者的了解,賀拉斯在《書信集》第1部第20首中對自己作品的未來做了不乏自嘲的展望。在這篇作品里,主角是詩集本身。賀拉斯把這部新詩集想象成一位年輕的家庭奴隸,他即將離開家,獨自到外面的世界闖蕩。主人警告他說,一旦出去,將沒有回頭路,他很快就會后悔。當他青春俊美的容貌消逝,羅馬公眾將不再關注他,他將流浪到遙遠的海外。年老體衰之時,他只能靠給小孩講課為生,或許會有一些聽眾對他主人的生平產生興趣。作品在此戛然而止。在這番描述中,賀拉斯灌注了豐富的詩學內涵。他想象自己的詩集不滿足于在他的朋友中私下流傳,而想被公眾閱讀,但從他反對這位“奴隸”離家的立場看,他并不愿意為大眾寫作,他心目中的理想讀者就是懂詩的朋友。詩集一度受追捧,但終于被冷落,再次印證了“庸眾”趣味的無常,從這個角度看,永恒的名聲恐怕只是妄想。蠹蟲啃噬詩集的意象讓我們想起《頌詩集》第3部第30首中無法啃噬紀念碑的雨水,新詩集在遙遠行省朽壞的遠景也與《頌詩集》第2部第20首中賀拉斯作品中被羅馬人世代傳誦的預言形成了對照。
這是一篇語氣戲謔的作品,賀拉斯沒有擺出一副自己將注定名垂千古的架勢,而是在輕松的調侃中切入了一個詩學的關鍵問題:如何面對讀者。任何詩人都必須知道,絕大多數讀者一定不會是他們心目中的理想讀者,一定不是知音。他們的趣味是多變的,不可預測的,所以作者不能奢望他們永遠鐘情于自己。詩中賀拉斯對奴隸(或者詩集)的警告表明,詩人不應迎合讀者,但詩人并非不能吸引讀者,如同作品后半段的奴隸所做的那樣。迎合與吸引的區別在于,是否犧牲自己的藝術原則,這也是弱勢作者和強勢作者的區別。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在奧古斯都時期做一位詩人是艱難的營生,這種艱難不是指生活境遇,而是指心理壓力。賀拉斯的應對既有原則,又充滿策略性。他的原則就是決不放棄藝術理想和精神獨立。面對強勢的皇帝和羅馬國家,他在小處妥協,大處則固守底線,總能以巧妙的手段發出自己的聲音。在處理與私人恩主的關系時,他語氣委婉,態度堅決,并以友誼的共鳴化解社會地位的差異。他善于向詩歌圈的友人學習,尊重他們的批評意見,不斷磨礪自己的詩藝。而對于羅馬的“庸眾”和敵對的評論家,他堅持自己的判斷,從不屈服,相信作品自我辯護的力量。文學秩序雖然對他有所束縛,但他最終以才華實現了相當程度的自由,并確保了詩歌的藝術價值和后世的聲名。
注釋[Notes]
①美地亞指帕提亞王國,斯基泰人是住在黑海以北的一個游牧民族,至于印度,雖然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曾遠征印度,但羅馬帝國和印度之間卻鮮有直接交流。蘇埃托尼烏斯曾記載印度派使者來羅馬(Aug.21.3),迪歐也講述了印度使團的故事(Dio 54.9)。
②rex字面義為“國王”,在變為共和制之后,羅馬人曾有幾百年時間憎惡rex這個詞,例如西塞羅就曾蔑稱愷撒等人為rex,但到屋大維時代,似乎稱恩主為rex已是習慣了,這反映了羅馬人心態的巨大變化。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nderson,William S..Essays on Roman Sati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
Apollodorus.Bibliotheca.Leipzig:Hirzelium,1891.
Bowditch,Phebe Lowell.Horace and the Gift Economy of Patron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Bowra,Cecil Maurice. “Horace,Odes IV.12.” The Classical Review 42.5(1928):165-67.
Cicero,Marcus Tullius.De Officiis.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74.
Commager,Steele.The Odes of Horace:A Critical Stud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
Dio,Cassius.Roman History,Volume VI:Books 51-55.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7.
Dyson,M.. “Horace, ‘Odes’ 1.8:The Love of Lydia and Thetis.”Greece&Rome,2nd Series 35.2(1988):164-71.
Girard,René.Violence and the Sacred.Trans.P.Greg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7.
Gold,Barbara.Literary Patronage in Greece and Rome.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7.
Horace[Quintus Horatius Flaccus].Horace:Odes,Epodes and Carmen Saeculare.New York:American Book Company,1902.
---.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New York:American Book Company,1909.
Kilpatrick,Ross S..“Fact and Fable in Horace Epistle 1.7.”Classical Philology 68.1(1973):47-53.
Macleod, C.W.. Collected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Moritz,L.A.. “ Horace’s Virgil.” Greece&Rome,2nd Series16.2(1969):174-93.
Ovid [Publius Ovidius Naso]. P. Ovidii Nasonis Metamorphoses.Leipzig:Teubner,1982.
Peterson,R.G.. “The Unity of Horace Epistle 1.7.” The Classical Journal63.7(1968):309-14.
Plautus,Titus Maccius.Mostellaria.Oxford:Clarendon,1966.
Putnam,Michael.Artifices of Eternity:Horace’s Fourth Book of Od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
---. “Horace c.1.20.” The Classical Journal 64.4(1969):153-57.
Quinn,Kenneth.Latin Explorations.London:Routledge,1963.
Saller,R.P..Personal Patronage under the Early Empi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Suetonius[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Suetonius:Life of Augustu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Veyne,Paul.Bread and Circuses: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Pluralism.Trans.B.Pearce.New York:Penguin,1990.
Virgil[Publius Vergilius Maro].Virgil’s Aeneid.New York:D.Appleton,1860.
White,Peter.Promised Verse:Poets in the Society of Augustan Rom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Zetzel,J.E.G..“The Poetics of Patronage in the Late First Century b.c.”Literary and Artistic Patronage in Ancient Rome.Ed.B.Gold.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