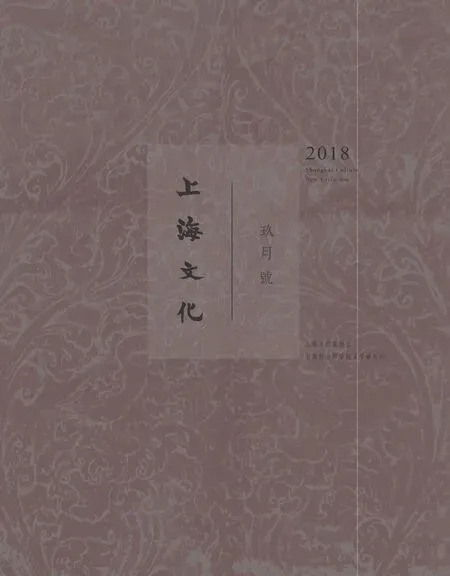由愛姑的“鉤刀樣的腳”論定《離婚》的主旨并非“反封建”,又由此論及魯迅的“身體記憶”
黃子平
魯迅的《離婚》,普遍被認為是“最難解的”,不好懂。魯迅自己很看重這一篇
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是“精讀魯迅”,直接違背了魯迅本人對如何讀書的建議。我們都記得魯迅的主張是“隨便翻翻”。此即陶淵明所說的“好讀書,不求甚解”。什么是“甚解”呢,就是如今說的“過度詮釋”。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穿鑿”。魯迅翻譯荷蘭人寫的“象征寓言童話”《小約翰》,將其中一個人物“科學研究的冷酷的精靈Pleuzer即德譯的Klauber,本來最好是譯作‘挑剔者’,挑謂挑選,剔謂吹求。……不如簡直譯作‘穿鑿’”。當然魯迅說了,“隨便翻翻”只是“作為消遣的讀書法”,真要正經做學問,也還是要“精讀”。陶淵明有一個理想化的建議,就是找幾個好朋友(“素心人”),晨夕相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這個研討會上相聚的素心人,在這兩天里“樂與數晨夕”,也正是在做對魯迅文本的“賞奇析疑”。
魯迅的《離婚》,普遍被認為是“最難解的”,不好懂。魯迅自己很看重這一篇,他編選的《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里選了自己四篇作品,《離婚》是其中一篇。又在《導言》里將《離婚》和《肥皂》作為“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微圓熟,刻畫也稍加深切”的例子,同時指出它們“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的一面。吳組緗說,“《離婚》比較難讀,跟他說的‘技巧圓熟’、‘刻畫深切’有關。外國的影響我看還是有的,可已經融化在我國傳統技法里面,形成了魯迅的獨特的風格,這是所謂‘圓熟’的意思。它的要點是:一心描寫情節和場面,把意思都從這些描寫表達出來,不直接說什么愛憎褒貶和解釋說明的話;這些場面和情節又經過精心的提煉和安排,彼此映襯著,相互呼應著,有豐富深刻的內容,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這是所謂‘深切’的意思”。
吳組緗本人是杰出的小說家,他對“圓熟”和“深切”的理解非常到位。我上大學的時候,北大中文系的幾位老先生還為本科生開課,林庚先生講《天問》,吳組緗先生開《古代小說選講》和《現代小說選講》。研究生,青年教師也來擠在本科生中間聽課,都知道機會難得。吳先生小說寫得好(如《官官的補品》、《一千八百擔》,夏志清的 《中國現代小說史》對之贊不絕口),(舊)社會經歷豐富(他當過馮玉祥的國文老師和顧問),講小說的時候經常提醒我們這些新社會長大的人注意不到的細節。譬如講《水滸傳》,魯智深沒怎么逼就上了梁山,為何林沖就需要一逼再逼,直到雪夜火燒草料場,才真的開始“夜奔”。魯智深“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嘛,林沖家有嬌妻,又有個小官職(“八十萬禁軍教頭”),有個“封妻蔭子”的盼頭,不容易造反。吳先生插了一句,說舊時節大戶人家子弟成年之后,怕他們在外頭闖禍,兩件事,第一給他們安排成親,第二讓他們抽上鴉片。有這兩條,就把他們牢牢拴在家里了,原來“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是這么回事。
讀《離婚》,吳先生提醒我們注意愛姑的腳,而且出現了兩次:
莊木三和他的女兒——愛姑——剛從木蓮橋頭跨下航船去,船里面就有許多聲音一齊嗡地叫了起來,其中還有幾個人捏著拳頭打拱;同時,船旁的坐板也空出四人的坐位來了。莊木三一面招呼,一面就坐,將長煙管倚在船邊;愛姑便坐在他左邊,將兩只鉤刀樣的腳正對著八三擺成一個“八”字。
船便在新的靜寂中繼續前進;水聲又很聽得出了,潺潺的。八三開始打磕睡了,漸漸地向對面的鉤刀式的腳張開了嘴。前艙中的兩個老女人也低聲哼起佛號來,她們擷著念珠,又都看愛姑,而且互視,努嘴,點頭。
吳先生說,幾個細節就體現莊木三在當地的地位不凡,如給兩個人讓出四人的空位,又如吸的“長煙管”(一般人吸短的竹煙管),但我們不管這些,單看愛姑的腳。為什么是“鉤刀樣的腳”?吳先生說,這是纏過又放了的小腳,又叫解放腳或文明腳。這就把小說所處的時代特點、地方色彩一起帶出來了,這是清末或民初,東南“得風氣之先”的沿海地區。不光這雙腳不符合宋明以來的審美,愛姑的坐姿也不雅。問題是老先生八三不以為意,且打瞌睡對著這雙腳張開了嘴。當然對愛姑不滿的人也有,但她們顯然敢怒而不敢言:“她們擷著念珠,又都看愛姑,而且互視,努嘴,點頭。”《離婚》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樣一個過渡的時代,曖昧的時代,將生未死的時代,到處都是多重性、曖昧性和過渡性,就集中體現在愛姑這個人物身上。
《離婚》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樣一個過渡的時代,曖昧的時代,將生未死的時代,到處都是多重性、曖昧性和過渡性,就集中體現在愛姑這個人物身上
以前正統魯學的解釋,說《離婚》是勞動婦女對地主階級一次不成功的反抗。從哪里看出愛姑是“勞動婦女”來了?唯一跟“勞動”相關的是黃鼠狼叼走了大公雞,“小畜生”怪愛姑沒把雞塒的門關攏,劈臉就是一嘴巴子。施家跟莊家門當戶對,應該也是殷實人家;請得起慰老爺當調停人,據說還送給了慰老爺一桌酒席,最后也不討價還價,一出手就按照“天外道理”加了十塊大洋。施家媳婦入夜關門閉戶、留心火燭,是應分的職責,說她是“勞動婦女”終歸有點勉強。但愛姑又不是我們熟悉的大家閨秀、小家碧玉,嫁過去后三從四德的小媳婦,更不是子君一流覺悟了的、反叛的都市新女性。愛姑亮著她的文明腳,站在新文學的小說文本邊緣,使我們的解讀面臨許多尷尬。
這些有意鋪排的陌生化敘述,正是作品的精華所在
吳組緗先生概括了愛姑這個人物的“典型性格的特征”:
她自己的事,連父親莊木三也不能替她作主,必得親自出馬表示自己的意見才能算數。她走出家門,毫不膽怯害羞,在陌生男子面前,在大庭廣眾中高談闊論,沒有顧忌。她勇敢直率向眾人申說屈辱和冤苦,控訴婆家對自己的壓迫,指斥丈夫的惡行,當面揭發并抗議婆家對權勢“鉆狗洞、巴結人”的卑鄙勾當(黃按:這不罵到七大人頭上去了么?);
她好像沒有什么封建禮教觀念。好像認為人活在世上都是平等的,你怎么來我怎么去。她滿口老畜生小畜生,把許多惡罵回敬給公公和丈夫,因為他們經常辱罵她。甚至對自己的父親也不留情面,當眾罵他見錢頭昏眼熱,罵他老發昏,因為她覺得父親有對不起她的地方;
她的潑辣放肆使人吃驚。她相信自已有理,相信自己的抗爭是正義的,她說話理直氣壯,義憤填胸。她敢于下決心要賭一口氣,敢于拚出一條性命,鬧得他們家敗人亡走投無路;
她畢竟很幼稚很脆弱,對統治權勢存著幻想,一面仰仗他們評理,一面很自卑。懷著絕望情緒,又缺乏歷煉,見識也有限。她作的一點個人反抗,處處顯出一種“放刁撒潑”、“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意味。這是她所依靠的家庭出身鑄成的。因此她經不起考驗,一到覺得大勢已去,就乖乖巧巧屈服了。
我們對愛姑的“反抗”,實在是有點期望太高。原因在于從第一場景(烏篷船)轉入第二場景(龐莊慰老爺家)之后,敘述者就采用了愛姑的視點,使讀者一直認同愛姑的語調和主觀感覺:緊挨著門旁的墻壁,站著“老畜生”和“小畜生”;慰老爺“不過一個團頭團腦的矮子”;圍著七大人的一群“干癟臉少爺”。但對七大人的敘述則完全采用了“陌生化”的處理,就是千方百計地有意不讓“鼻煙”或“鼻煙壺”這樣的詞出現,一切“東西”都是“第一次看見”:
木棍似的那男人也進來了,將小烏龜模樣的一個漆黑的扁的小東西,遞給七大人。……七大人也將小烏龜頭拔下,從那身子里面倒一點東西在掌心上;木棍似的男人便接了那扁東西去。七大人隨即用那一只手的一個指頭蘸著掌心,向自己的鼻孔里塞了兩塞,鼻孔和人中立刻黃焦焦了。他皺著鼻子,似乎要打噴嚏。……“呃啾”的一聲響,愛姑明知道是七大人打噴嚏了,但不由得轉過眼去看。只見七大人張著嘴,仍舊在那里皺鼻子,一只手的兩個指頭卻撮著一件東西,就是那“古人大殮的時候塞在屁股眼里的”,在鼻子旁邊摩擦著。
這些有意鋪排的陌生化敘述,正是作品的精華所在。否則,《離婚》的故事簡簡單單,其實就是鄉村士紳的民事糾紛調解過程。慰老爺調解了四回,沒有“圓功”,這回搬出了七大人。七大人大概是個退休的官員。中國前現代社會的治理成本是比較低的,全靠鄉村士紳維持底層的氏族和諧。萬不得已才打官司,喜歡打官司的人,官府并不待見。士紳在地方上的權威性,除了財雄勢大,還有“知書識禮”的軟實力或曰文化資本。一個撒刁放潑的愛姑鬧了兩年多,仗著家里有六個兄弟,砸鍋平灶,要鬧得施家“家破人亡”,實在是見出沿海地區鄉村紳權的衰敗。魯迅用七大人一個莫名其妙的“來~~兮”扭轉乾坤,既是士紳權力軟實力的“余威”,也是其強弩之末的表征了。緊貼著愛姑的惶恐、絕望和不解,我們還聽到另一個(元)敘述的聲音,處處嘲笑所謂“知書識理”的那一套文化資本(屁塞、水銀浸、洋學堂),正在勉為其難地搖搖欲墜,維護著即將土崩瓦解的世界。
在那個驚天動地的噴嚏之后,慰老爺的最后總結基本上是對的:“七大人也真公平,愛姑也真明白!……恭喜大吉!總算解了一個結。”三贏:施家擺脫了糾纏不休的媳婦,莊木三贏回了面子和錢財,慰老爺和七大人盡了士紳權威的職責。那么愛姑失敗了么?愛姑的目標是“賭一口氣”,“鬧得小畜生家破人亡”,本來就不是一個合理的訴求。說她失敗,完全是出于一個“啟蒙主義”的解讀框架,希望這個口口聲聲“三茶六禮”、明媒正娶的愛姑爭得一個人權、平權、女權的局面?所以小說的結尾,由愛姑來跟慰老爺說這些“拜年話”,才是作品的意味深長之處:
“我們不喝了。存著,明年再來喝罷。”愛姑說。
“謝謝慰老爺。我們不喝了。我們還有事情……”莊木三,“老畜生”和“小畜生”,都說著,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唔?怎么?不喝一點去么?”慰老爺還注視著走在最后的愛姑,說。
“是的,不喝了。謝謝慰老爺。”
為什么愛姑走在最后?也許是鉤刀樣的文明腳走不快,也許是證明愛姑也終于解了心中的結了?但我們還要問問魯迅心中似乎還有未解的結。有的研究者用魯迅寫《離婚》時的婚姻狀況來簡單對應,索解作品中的“無意識趨向”,把審美閱讀轉換為倫理閱讀,消解了“這篇小說分布在細節中充滿悖論的矛盾沖突,新與舊、善與惡的錯綜交疊,正義與荒謬的渾然一體”。然而我們仍然記得,魯迅在日本,聞得母親訂了朱安為妻時,只提出兩條要求:一是開始識字,二是開始放腳。不料朱安托人捎信說,一,不識字,二,不放腳。婚姻和纏腳放腳之間的關系,在清末民初是如此生死攸關地纏繞在一起。胡適寫信給他母親,也討論過江冬秀放腳的事情。蔡元培喪偶之后,有人張羅續弦,蔡先生提出的擇偶十條中,有一條正是“不纏足”。
魯迅學醫的動機,除了他自己提到的兩條(第一,恨中醫耽誤了他的父親的病;第二,確知日本明治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醫的事實),好友許壽裳揭發了第三條:救濟中國女子的小腳;要想解放那些“三寸金蓮”,恢復到天足的模樣。
后來,實地經過了人體解剖,悟到已斷的筋骨沒有法子可想。這樣由熱望而苦心研究,終至于斷念絕望,使他對于纏足女子同情,比普通人特別來得大,更由絕望而憤怒,痛斥趙宋以后歷代摧殘女子者的無心肝,所以他的著作里寫到小腳都是字中含淚的。
許壽裳舉了魯迅許多作品中提到小腳時的深惡痛絕:
“至于纏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裝飾法中,第一等的新發明了。……可是他們還能走路,還能做事;他們終是未達一間,想不到纏足者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體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殘酷為樂,丑惡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熱風·隨感錄四十二》)。
我這演講的題目,是由那篇經典的《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套用過來,卻不夠徹底
小姑娘六斤新近裹腳,“在土場上一瘸一拐的往來”(《吶喊·風波》)。
豆腐西施,“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系裙,張著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里細腳伶仃的圓規”(《吶喊·故鄉》)。
“……女人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寧可走不成路”(《南腔北調集·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示眾》里的那個老媽子有一雙“鉤刀般的鞋尖”;
《阿Q正傳》里阿Q嫌棄吳媽“腳太大”。
真可謂“念茲在茲”了。許先生還提供了一條有趣的材料,說魯迅赤足時喜歡盯著自己的腳看:
魯迅的身材并不見高,額角開展,顴骨微高,雙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帶著幽郁,一望而知為悲憫善感的人。兩臂矯健,時時屏氣曲舉,自己用手撫摩著;腳步輕快而有力,一望而知為神經質的人。赤足時,常常盯住自己的腳背,自言腳背特別高,會不會是受著母親小足的遺傳呢?
這位神經質的醫科生,怎么會疑心到小腳的遺傳呢?所以我這演講的題目,是由那篇經典的《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套用過來,卻不夠徹底。按照魯迅的思路,我應該“又由此論及魯迅先生的戀足癖”,但這對先生有點不恭,而我用了“身體記憶”這個不那么弗洛伊德的詞,是因為我還要從足部講到牙齒。
這是魯迅的學生孫伏園,揭發魯迅學醫動機的第四條:從小牙疼。魯迅自己也提供了證明:
我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齒不痛的正人君子們立異,實在是“欲罷不能”。聽說牙齒的性質的好壞,也有遺傳的,那么,這就是我的父親賞給我的一份遺產,因為他牙齒也很壞。于是或蛀,或破,……終于牙齦上出血了,無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無牙醫。
從生理又牽連到了倫理:
還記得有一天一個長輩斥責我,說,因為不自愛,所以會生這病的;醫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從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齒的事了,似乎這病是我的一件恥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長崎,再去尋牙醫,他給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謂“齒袱”,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醫費是兩元,時間是約一小時以內。
原來是受了中醫話語的“誣陷”:
我后來也看看中國的醫藥書,忽而發見觸目驚心的學說了。它說,齒是屬于腎的,“牙損”的原因是“陰虧”。我這才頓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來,原來是它們在這里這樣誣陷我。到現在,即使有人說中醫怎樣可靠,單方怎樣靈,我還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但怕也很挾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切膚之痛,——我們是從自己的身體開始認識這個世界的。正是人的身體而不是精神成為人在世的根基,并且成為人認識自我、確認自我的出發點。梅洛·龐蒂指出,“正是從身體的‘角度’出發,外向觀察才得以開始——如果不承認這一身體理論就不可能談論人對世界的感知。我們對日常生活的感知取決于我們的身體”。魯迅不斷提醒我們,身體是會痛的,不管文化以什么名義(審美的或崇高的)一再想讓我們忘記這一點。
而身體始終已經是“文化上勾繪好了的,它從不會以純粹的或未經編碼的狀態存在”。身體處在這種或那種的文化話語中被敘述被想象。身體不僅始終處于社會文化的建構過程中而不斷地被管控與形構,而且也時時呈現出性別的區隔與壓迫。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布萊恩·特納在《身體與社會》中指出的,“對身體的控制從本質上是對女性身體的控制”。
魯迅的“身體記憶”帶給我們的啟示,可以用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的一首詩來延伸。這首詩的英文題目是Tortures,香港詩人鐘國強譯成《折磨》,我想,譯成《刑求》可能更貼切:
什么也沒有改變。/身體是痛苦的蓄池;/它要吃要睡要呼吸;/它有薄膚其下是血;/齒甲供應不缺;/骨骼可打碎;關節可拉開。/用以折磨,這些都可以考慮。
……
什么也沒有改變。/或許除了規矩、儀式和舞步。/不過以手護頭的/姿勢依然。/身體翻滾,搖晃,拖拉,/被推撞時跌倒,翻仰,/瘀傷,腫脹,流涎,淌血。
……
2018年6月19日改定于北角炮臺山
? 《且介亭雜文·隨便翻翻》。
? 《小約翰》引言。
? 《移居兩首·其一》。
? 吳組緗:“《離婚》是比較難讀。”(《說〈離婚〉》,《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1期);藍棣之:“《離婚》是魯迅創作中最難解的一篇作品。”(《論魯迅小說創作的無意識趨向》,《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8期)。
? 楊聯芬《重釋魯迅〈離婚〉》,《邊緣與前沿》,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頁149。
??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