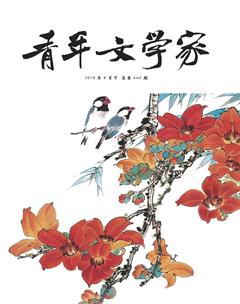時代的詩意孤獨:埃拉·惠勒與呂碧城感懷詩歌比較
上官書儀
摘 要:埃拉·惠勒·威爾科克斯(Ella Wheeler Wilcox,1850-1919)與呂碧城(1883-1943)分別是美國與中國同一時代具有理性思維與先進精神的杰出女性作家,由以詩詞作品見長。二人雖生活在太平洋兩岸,但經歷相似:年少成名,作品豐富,關注女性發展,受宗教影響,一人終老,身后蕭條。然而,受社會時代背景影響,二人的詩作風格卻迥然不同且各具特色。本文從平行研究的角度入手,對二人的創作背景、詩歌表現手法和風格進行比較分析,試探究二人在撰寫感懷詩歌時對個體“孤獨”這一主題不同的呈現,希冀讀者對此二位偉大女詩人再度關注,并對其詩作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及文化重新解讀,挖掘詩人的經典價值并于使之流傳于現世。
關鍵詞:呂碧城;埃拉·惠勒;感懷詩歌;孤獨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4-0-02
一、引言
“宇宙中有兩種可能性:我們要么是孤獨的存在,要么不是,無論哪種,都同樣可怕。”英國著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對于孤獨的存在如此說。古今中外,對于孤獨的認知一直都是詩人們懸在心頭的主題之一,雖不比憂國憂民、山水田園、思鄉懷人、愛情閨怨詩般備受矚目,詩人們卻無時無刻不表達著對個體孤獨的隱喻暗示和對自由美好的向往追求。
而文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它的興衰不可能是孤立的,在一種文化現象背后總是有著相應的其他文化現象。國家的統一,疆域的拓展,經濟的發達,社會的穩定,文化氣氛的開明、寬松和濃郁都是文學繁榮所必不可少的因素。19世紀,特別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人類詩歌藝術大變革的時代,也是世界文學“現代運動”的初創期。在19世紀末,盡管激情式抒寫的浪漫主義詩歌受到重視詩藝的詩人的質疑,但是仍具活力,尤其敢于創新的浪漫主義精神極大地影響著現代詩人,不但涌現出象征主義、超現實主義、未來主義、立體主義等詩歌流派,還在多個國家出現了“自由詩”運動。
美國19世紀文學發展迅速,尤其是詩歌,這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族文化的興起有著直接的聯系,戰后重生,自由的獲得,使人們迫切地想表達自己的想法,而詩歌恰恰是最好的表達方式。此時的中國社會正處于動蕩不安的裂變時期,戰爭與革命是這個時代的主題,種種進步社會思潮、民主思想、新文化運動等應運而生。不同的國度,卻都面臨著發展社會經濟和開放社會思想的難題,而各個國家、地區和民族又被納入世界歷史的總進程,雖有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等狀況,卻阻撓不了文人墨客對于不同文藝理論和寫作手法的吸收綜合。
二、詩歌創作風格及主旨比較及影響因素
埃拉發表《孤獨》一詩那年,呂碧城在安徽出生。19年后,呂碧城寫下了《踏莎行》一詞。這兩首極具代表性的詩歌,都嘆時光匆忙,卻在兩類迥異的文體中完整的代表了兩類極端的思考:在有限的生命中,是笑對百難還是愁眉深鎖?
《孤獨》開篇便借助兩個相當有力的情緒——“哭”和“笑”,以吸引讀者目光,將近結尾又以“一個接一個”“排隊”“穿越”等極具畫面性的詞語勾勒出時間流逝的緩慢和具象的孤獨。全詩除題目外并未提到“孤獨”,乍看,簡明輕快的詩歌韻律給人輕松的感覺,可慢節奏訴說卻帶給人們挽歌似的憂傷和安靜的思考。埃拉描述的是孤獨的路徑,從哭泣開始,經歷悲慟,直至痛苦和滅亡。其在用韻上十分考究,偶句押韻,并強調居中的定義詞,如“你哭泣,卻只能獨自黯然神傷(Weep, and you weep alone)”和“它的煩惱已經足夠(But has trouble enough of its own)”,alone和own,加強了讀者對于孤獨的感受。而這種用韻技巧也是全詩的隱喻,以外韻暗示人們的相聚分離。另外一種用韻技巧是詩人在每節第三,第七行都插入了內韻。內韻,也可以說是情緒韻。一首具有真情實感的詩,應是字字合情,字字合韻,情緒的復雜多變決定了韻律的復雜多變。此外,詩歌中不乏修辭手法的運用,如擬人,“只因古老而憂傷的大地必須注入歡樂(For the sad old earth must borrow its mirth)”,“你歌唱,山谷將與你合音共曲(Sing, and the hills will answer)”,“快樂之聲總能引起回聲陣陣(The echoes bound to a joyful sound)”。文學技巧的廣泛應用,詩歌旋律和節奏的把握,使《孤獨》一詩超越了個體孤獨的悲戚感,留給讀者的唯有對于時間和生命逝去的追思。
不同于西方的敘事長詩,中國的抒情短調醞釀了千年之久。呂碧城在《踏莎行》一開始就抓住“孤”這一主題,將許多鮮明的自然景物,無比巧妙地組織起來――近看“孤村”、“古道”,遠眺 “青山”、“長空”。不僅內韻、外韻協調,且情景融情。詩人同樣使用修辭來加強情感表達,如設問,“今宵何處駐征鞍?一鞭遙指青山小”;疊韻,“漠漠”、“離離”;擬人,“欲黃重綠情難了”;對比,“韶華有限恨無窮”等,加之一系列如“孤”、“殘”、“衰”、“愁”等形容詞,更加襯托出人生易老天難老,類李清照人生頓悟千古慨嘆般凄迷的氣息。
呂碧城與埃拉在對生命本體的追問與思考上都不約而同地融入了深邃的哲理,萬物雖有生有滅,但本質上趨于永恒;個體雖匆匆無常,但萬物有序,新舊更迭,連接不同的生命旅程。
三、結論
埃拉與呂碧城都是那個時代敢于為女性發聲的偉大詩人及作家,可不為新興力量所接受和不愿迎合新興力量卻不謀而合地阻撓了二人作品的流傳。她們是時代遺珠,孤獨的詩意著,在自己的詩詞創作道路上漸行漸遠,為切實的民生百態寫下洋洋灑灑的文字,令今人讀來仍覺意味深長。
埃拉的世界觀完全體現在她的詩歌題目上,“無論什么,皆為最好”。雖然她未有一部作品被二十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弗朗西斯·馬西森收錄至《牛津美國詩歌集》,仍無法抹去其詩歌的熠熠光彩。呂碧城早期詞作大多以傷春悲秋、念遠傷別為主題,繼承了傳統閨中詞的婉約風格;但至中晚年,多用佛道詞匯、典故,飽含哲理。不同于埃拉詩歌中顯而易見的樂觀情緒,呂碧城的詩詞中經常會出現“蕭條”、“哀頑”、“寂鎖”、“空憐”、“凄惻”、“苦吟”等消極的表達,雖然詩詞內涵思想激進明理,可用詞方式卻突顯強烈的個人情感特征。
“護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績忍重埋。匆匆說法談經后,我到人間只此回。”1943年1月4日,呂碧城于夜夢中得到啟示,作下最后一詩寄于友人,這是其對人生的總結和感悟,亦有遺憾。20天后,她在香港九龍孤獨辭世。在中國女性詩人由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中,呂碧城以一個先覺者的姿態走出了中國新女性之路,縱然這路孤獨。就像王忠和在《呂碧城傳》中寫著的:“呂碧城的離去,可能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吧。中國的教育界、新聞界、文學界、學術界、宗教界,尤其是婦女界都不應當忘記呂碧城”。同樣地,世人也不應忘記埃拉。
參考文獻:
[1]Ballou, Jenny. Period Piece: Ella Wheeler Wilcox and Her Times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0.
[2]Gardner, Martin. New Thought, Unity, and Ella Wheeler Wilcox [J]. Hypotheses: Neo-Aristotelian Analysis, 1993 (05): 8-11.
[3]Wilcox, Ella Wheeler. Drops of Water: Poems [M]. South Carolina: Nabu Press, 2011.
[4]郭延禮. 南社作家呂碧城的文學創作及其詩學觀——紀念南社成立一百周年[J]. 文學遺產, 2010 (3): 127-137.
[5]李保民. 呂碧城詩文箋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6]王忠和.呂碧城傳[M]. 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 2010.
[7]姚艷梅. 中西詩歌表現手法的比較研究[J]. 作家, 2010 (20): 1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