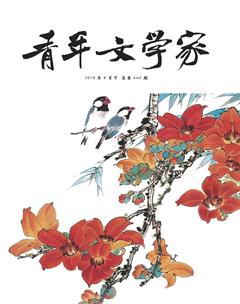電影《孕城》的結構主義分析
摘 要:2014年上映的《孕城》給長期低迷的湖北電影帶來了一點不一樣的色彩。本文將從結構主義學史學的角度,分別采用茨維坦·托多洛夫的敘事理論和A·J·格雷馬斯在敘事學的符號學的方法對電影文本進行分析。
關鍵詞:《孕城》;結構主義;符號矩陣
作者簡介:肖梓泉(1993.9-),男,土家族,湖北省宜昌市人,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在讀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4--02
一、敘事學分析
對文學作品的解讀,長期以來有各種角度可以切入,其中,結構主義是從“公式化”的角度來分析文學作品。從結構主義者的角度看,相同類型的文學作品,其內部公式都是固定的,文學作品的結構是定量,人物、背景、情節的要素是變量。普羅普認為人物本身在民間故事中的作用不是最重要的,更為重要的是這個故事中的各種功能。他說,“我們將功能理解為一個人物的行為,該行為是根據其在情節展開之中的意旨來決定的。”在普羅普的眼中,故事由不同的“功能”通過一種固定的模式組成,人們在創作過程中對不同的人物賦予相同的行為(“功能”)。角色只承擔這些“功能”,從而形成一個新的“小故事”。
在普羅普的觀點中,將敘事作品看作陳述句的擴展是一個核心,在對小說進行語法分析時,他和巴特都認為小說的基本結構和陳述句的基本結構類似,在“主語+謂語+賓語”的標準句中,小說人物對應主語,人物的動作對應謂語,行為的受者對應賓語。小說里人物的行為隨著情節推進會產生“橋接”和“轉化”,在起著不同作用的同時,改變原本情節的平衡,在失衡中構建出一個新的秩序,他稱其為敘事化。
筆者對電影《孕城》的故事情節做了一個陳述性的敘述,即:《孕城》講述的是清末年間,漢口地皮大王劉宗祥在得知朝廷想要修筑后湖大堤的消息后,各方運作,頂住各方壓力從總督張之洞手中取得了修堤權,卻在外國侵略者和本土社會幫派的聯手設計下釀出大禍,但是最終還是洗脫罪名,完成了“張公堤”的建造,為漢口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我們將這段敘述加以分析,可以將情節濃縮為如下五個單元:
(1)起初的平衡狀態
(2)劉宗祥得到修堤消息,平衡狀態被打破
(3)敵對勢力想要競爭,聯手施壓
(4)劉宗祥及家人多方運作戰勝對手
(5)最終修堤完成,回歸平衡
在上面幾個單元之間,各單元在因果關系和時間順序方面是“連接”的,但在內部邏輯中又存在轉換關系。在故事的開端,劉宗祥擁有的平靜生活,在“修堤消息”這一外來者進入后被打破,至此一個平衡的破裂成為了故事上升的支撐。隨著劉宗祥和管家八面玲瓏的運作,劉宗祥初步取得了修堤權,懸念進一步被打破,而外國殖民者和本地黑幫的敵對和各種陷害導致修堤出現事故,劉宗祥被捕,故事漸漸達到高潮,最后劉宗祥在家人各種辛苦奔走相求下洗脫罪名,重新獲得修堤權,故事的情感達到最高峰,而后,在排除敵對勢力的干擾后,修堤完成,生活又恢復到從前的平靜,建立起一個新的平衡。
二、格雷馬斯“符號矩陣”分析
在格雷馬斯的文學符號學理論中,“符號矩陣”是其中最著名的理論,它來源于對亞里士多德邏輯學中命題與反命題的解釋,格雷馬斯認為“結構主義語言學中意義只有通過二項對立才能存在”,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拓展和提出了對文本解讀的矩陣模式。該矩陣模式可以用一個關系圖直觀地表現出來。
符號矩陣基本模式如圖(一):
上圖中,A是被設立為主要元素,與其相對立的為反A,與A矛盾但不對立的為非A,與反A矛盾但不對立的為非反A,通過二元對立的行動元來解讀敘述的普遍模型和語法內含,“由此產生的行動素的矩陣模式雖很簡單,但可以在‘增補投資的壓力下生成任何可以想象的表達方式”。換句話說,一個故事都有一個固定的敘述模式,即開始于A與反A的對立,在情節推動的作用下,非A與非反A相繼出現,A、反A、非A、非反A這幾要素交織碰撞,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在電影《孕城》中我們首先來界定一下符號結構中的四項行動素。首先是劉宗祥。他在開始時就是事業有成,是漢口有名的地皮大王,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滿足,但是他一直覺得漢口應該有更好的發展。他在得知朝廷為漢口修堤的消息后,十分激動,認為不管是對個人還是漢口來說,這都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但是漢口是一個魚龍混雜的地段,外國殖民者也想要在修堤權上分一杯羹,于是在對待修堤事宜這個問題上,兩者形成了對立。劉宗祥開始尋求總督的幫助,殖民者開始聯合本地青幫的力量,二者產生了沖突,開始正面交鋒,三者關系的張力變大,再細細品味就能從中發現,貫穿這三者的因素就是利益。于是我們可以將故事中的要素組成下面一個矩陣:
影片表面上是在講一個“爭奪利益”的故事,拋開蘊含的其他要素:人性中善惡的較量;大愛與私利的沖突。劉宗祥是正義的一方,暫且設他為A項,他對于“修堤權”爭奪的出發點是為國為民,當然也為了自身利益,“修堤權”的爭奪,會給劉宗祥帶來傷害和壓力,以及個人利益的損失,這從禮儀角度來說于劉宗祥是不利的,但是“修堤權”又關系著國民之大利,所以“修堤權”可以和劉宗祥在上面的矩陣中形成一種聯系,既不對立又不相同,于是成了非A項。殖民者和青幫在片中是惡的一方,不管是殖民侵略還是賣國求榮從常理上說都屬于邪惡的一方,在爭奪“修堤權”這件事上,他們和劉宗祥有著鮮明的對立關系,這樣在矩陣中的沖突就更加明顯,殖民者是本能地想要搶奪這個利潤,青幫則是為了一己私利,他們也成了殖民者的助手,這正是格雷馬斯在《結構語義學》中提出的一個模式,即包含了六個行動元的模式。主體、客體、對手、助手、發者以及受者這六個行動元在某個事件中構成兩條主軸,一條主軸以主體客體的關系為核心,另一條主軸是以對手和助手的關系為主。在這個系統當中利益成為了事情沖突的總對象,在這場利益的爭奪中大家都付出的太多。
參考文獻:
[1]托多洛夫.敘述的結構分析.最新西方文論選.漓江出版社,1991年.
[2]杰姆遜(唐小兵譯).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3]拉曼·塞爾登.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4]普洛普.民間故事形態研究.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
[5]列維·施特勞斯.結構人類學.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
[6]特倫斯霍克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