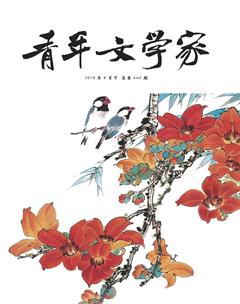《三國演義》“三分虛構”藝術探微
王茂竹
摘 要:羅貫中創作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是一部“有志圖王者”的啟示錄。“七實三虛”是作者所運用的主要藝術手法。在“三分虛構”的應用上,作者或遞換原有人物的歷史事實,移花接木,張冠李戴;或吸收《平話》、綜合各種民間傳說,充實點綴,提綱挈領;或采用歷史事實的一端,巧手鋪陳,大膽生發;或依據主題及人物塑造之需要,刪舍歷史事實……塑造出了形神兼備、個性鮮明、栩栩如生的一系列典型人物,創造了一個博大精深的藝術世界。作家以藝術的手段,表現了對歷史、社會出路、人生價值、社會道德的思考和判斷,極盡文學的情教功能。本文僅從其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粗陳管窺之見。
關鍵詞:羅貫中《三國演義》;三分虛構;藝術探微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4-0-03
中國古代歷史是一部周期性動蕩的歷史。羅貫中大致是元末明初人,今存羅貫中署名的小說大都以歷史上的改朝換代為題材,顯示了羅貫中對王朝盛衰過程和原因,政治軍事斗爭策略的成敗利弊的認識。由此可見,羅貫中是一個“有志圖王者”,不僅有政治抱負,也有豐富的歷史知識,更有深邃的歷史眼光。對歷史、社會出路、人生價值的思考和判斷,作者以文學藝術的手段,定位于不朽的杰作《三國演義》。這就是說:一、擁劉反曹,明正統,表明作者對明君仁政的渴望,對社會治亂的思考。二、對道德的思考。贊美忠義,重建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極盡文學獨特的情教功能。三、贊美智勇,表明作者的人才理想一一崇尚智勇。四、悲劇之歌。歷史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矛盾沖突。作者為了實現以上之目的,不惜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對歷史材料采刪加工,又廣泛吸收民間傳說,創作出了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長篇歷史小說《三國演義》。“七實三虛”也成為其最鮮明的藝術特色。就“三虛”的藝術特色,本文僅就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從四個方面作以探析。
一、移花接木、張冠李戴
《三國演義》中的許多故事雖說是實有其事,但是出于某種需要,將某甲的事,故意地安排在某乙的身上,使讀者以為事情本來是發生在某乙的身上的,這種藝術虛構手法叫移花接木、張冠李戴,《三國演義》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這種方法用得最多。
一般說來,《三國演義》中的人物屬于虛構的是極少數,多數都是歷史上的真人。但是作者為了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具有個性,形象更鮮明,經作者有意加工,和原樣已有不同。魯迅在談到人物的形象塑造時說:“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1]這對于取材于現實生活進行的創作,幾乎是個通例;就是有關歷史人物進行的創作,也是這樣。《三國演義》中在劉備形象的塑造上就是如此。劉備是作者著力塑造的“人君”典型,寬厚仁愛是作者附于他并著力刻畫的主要性格特征。在內容材料的選取上,作者都是緊緊圍繞這一主題嚴格篩選的。譬如“的駑妨主”一事。本屬于晉人庾亮的故事,作者為了表現劉備不做利已妨人之事,增加他的光彩,把它移到了劉備的身上,說成是他的行為。而有些事原本是劉備所為,作者怕毀損了他的人格完整就移到別人身上去。比如“鞭督郵”一案,實屬劉備所做,在《三國志》中寫得清清楚楚:“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系其頸著馬柳,棄官亡命。”[2]劉備區區一個衙門里的小官吏,敢于上公堂縛住平日作威作福,目空一切的省郡級大員一一督郵,并著力鞭打,沒有點勇氣是不可能辦到的,這說明劉備除了仁愛寬厚的一面外,有時也會金剛怒目一番。但此行為與作者附于劉備的性格特征不相符,有損于其仁君之形象。因此,在《三國演義》里,作者為了保全其形象,把劉備塑造成一個完整的仁人之君,就將這一故事移到了性格本來就爽直魯莽的張飛頭上。并對其動作、神態、語言作了傳神的刻畫,“環眼”“睜圓”,“鋼牙”“咬碎”,“柳條”卻是“攀下”,并罵道:“此等害民賊,不打死作甚!”[3]經過如此的傳神刻畫,張飛勇猛、敢作敢為的硬漢形象躍然紙上,其嫉惡如仇、魯莽、爽直、快人快語的性格特征得到了更充分的體現,而此事實經如此嫁接以后,本案的作案人,鞭督郵“兇手”的劉備,搖身一變,成了“急喝張飛住手”的勸架式人物,“真正”的好人。集仁愛寬厚于一體,富有長者之風形象的劉備如在眼前。經過這樣處理,張飛、劉備的所作所為更符合他們的性格特征,更合乎常理,更趨于人情,人物形象更貼近于實際生活,更使人覺得真實可信,達到了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有機統一。又如為了表現劉備的謙虛,莫須有地安排了一個“三讓徐州”。顯然,在《三國演義》中,劉備這個角色的虛構成分是很濃重的。有一些描寫所謂“反面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例是作者有意給“強加”上去的。
總之,羅貫中在塑造人物形象時,不是機械地把歷史人物每個具體細節原封不動地搬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而是根據主題和人物形象的需要,對歷史材料做了概括和加工。他為了突出地表現某個人物性格,不惜變更人和事物的原有關系,把個別事件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這種方法雖然違反了歷史的真實性,卻符合藝術的真實性原則,使人物形象顯得更逼真,更生動,更富有生命力。
二、綜合民間傳說,大量采入民間故事
在《三國演義》中,有一部分故事情節,如“桃園三結義”、“關張古城會”、“蔣干中計”、“華容道放曹操”、“孔明柴桑吊喪”等,都沒有歷史依據,是來自民間的故事,系民眾創作。作者出于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將這些民間故事大膽引入,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實,民眾是真正的創作家,他們往往依據某些歷史素材,加以改鑄、發揮,形成符合自己意愿的歷史故事。有時,民眾還會妙手生發,巧加鋪敘,敷衍成一定的歷史故事。《百川書志》認為,《三國演義》作者“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共中“采說”,“通好尚”,講的都是將民間創造的故事的吸收和采入。
《三國演義》一開篇即是“桃園三結義”。而“桃園三結義”則是來自于民間的創作。在這一回中,作者匆匆端出一個“義”字。而“結義”之“義”乃是全文說“義”的一個綱,以后所寫及的“關羽義釋曹操”、“張飛義釋嚴顏”等都是它的細目化。因此,“義”是人物鏈接的一個紐帶,是統攝三國人物靈魂的信條,是故事情節得以延升的跳板,是吸引人們、為人所樂道而又亙古不衰的緣由之所在。作者虛構引入的“桃園三結義”這一情節,是全文的一條線索,起著綴珠串玉、提綱挈領的作用。一是介紹了西蜀政權中三個極其重要的角色一一劉備、關羽和張飛。二是引出了全文之綱一一“義”。而“義”又是中國傳統道德中極為重要的內容,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準則。孔子曾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6]如引入關羽和張飛古城會之誤會一事,意在表明:情深如關、張,但如果在“義”這一點上出現了分歧,那往日的情義也就一筆勾銷了。由于關公重私情而忘大義,在華容道放走了曹操。作者所采入的這一民間傳說,在關羽身上是一個“美麗的錯誤”,有力地表現出他重情重義,為情義競置軍令于不顧,甘愿冒犯軍令而會遭嚴懲的危險。
羅貫中之所以要把關羽塑造為“義”的化身,其原因就在于:《三國演義》是一本寫亂世的書,作者又身處元末明初的大動亂之中。在亂世,人們為了保全自己,就極需要用“義”字來保護自己。正義,是行為的準則,用以告誡自己,使自己不沉入罪惡的淵藪;情義,是生命的保護傘,“出門靠朋友”,人們以“義”相聚才會有周旋于種種生活領域的能力,這就是《三國演義》大力倡言一個“義”字的緣由之所在,也是作者虛構這些情節的原因之所在。
三、妙手生發、大膽想象
《三國演義》中的某些章節僅僅是《三國志》中的一句話而已,根本無情節可言,作者即依據此資料,大膽想象,妙手生發,多方鋪敘,極盡形象思維之能事,在史實中插入虛構情節,使之實中有虛,虛中有實,真假難辨,融為一體,成為肯定和強化人物性格的重要材料。
在《三國志》的《武帝紀》和《呂布傳》中,陳壽都沒讓張遼這位將軍出場,只是說了一句,呂布手下“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7]張遼也是“諸將”中的一員,看來與呂布“異意”是無疑的了。可在《張遼傳》中,就明朗化了。文中有那么幾句話,“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于下邳,遼將其眾降,拜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8]因這里寫得很明確:一、張遼與呂布本合不來,只是迫于形勢跟了呂布;二、張遼是在呂布被擒之前“將其眾降”,帶著自己原先的部隊歸降曹操的。可是,在《三國演義》一書中,卻在“降”這件事的過程上做足了文章。如寫曹操,當武士擁張遼至時,先是“指遼曰”,接著是“笑曰”,其次是“大怒曰”,“擲劍笑曰” ……從這一系列的神態的刻畫中,非常傳神的描摹出了曹操的奸雄本色,活脫脫一具曹操的形象立于公眾面前。再比如寫張遼,雖是敗將,仍罵其為“國賊”。當曹操拔劍親自來殺時,“全無懼色”一副大義凜然至死不屈的忠臣形象。玄德見此,說是“此等赤心之人,正當留用”,用這一語刻畫出了一幅善 于權謀的梟雄形象。云長見此卻“愿以性命保之”,說明他是個極重情義之人,為情義而甘愿舍棄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見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魅力。在文中所述之事中,只有兩件事是真的:一、張遼是降了曹操的;二、張遼降操后受到了特別的優待,“拜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至于怎么降,降的過程中有些什么喜劇性的事,都是按人物性格生發出來的,即屬于藝術虛構的東西。經過如此一番虛構,把張遼之忠、劉備之仁、關羽之情義、曹操之奸詐,作了傳神的刻畫。再比如,在關羽降曹一節中,《三國志》和《三國演義》 更是天差地別。在《三國志·武帝紀》中,記述有:“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9]而《三國志·關羽傳》中的記述是:“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及羽斬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于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之。”[10]事實大致是清楚的:一、在四面被圍的情況下,關羽投降了曹操(或稱被擒)。二、曹操對降將關羽“禮之甚厚”。三、最后關羽還是走了,可能是不告而別(“亡歸”該是不告而別),也可能是告而別之(所謂“拜書告辭”)。而《三國演義》對關羽之降作了最大限度的潤筆。“關公約三事”,傳為千古美談。同樣寫的是投降,把關羽之降寫得頭頭是道,氣象萬千, 怪不得曹操也嘆道:“事主而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事也。”這是作者借曹操之口而生發出來的感慨。同樣是降曹,作者卻安排了不同的情節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特征,描摹人物的內心世界,刻畫人物的典型神態。遼是“操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而“感其意”“遂降”;關公是“操愿從三事”而降漢獻帝,不降曹操。一樣的事情,卻是兩樣的敘法。作者巧妙地使用了襯的藝術手法,對人物的語言神態作了傳神的刻畫,使人物形象更豐滿,更真實。這一個個的人物,使讀者時而歡欣、時而悲痛、時而同情、時而憤慨、時而顛三倒四、惶惑迷離,我們情不自禁為之振臂高呼,拍掌叫絕。這就十分明白地說明了其刻畫人物的藝術魔力。作者駕馭人物描寫的技巧之高超,更為世人所驚嘆,而其所刻畫的人物,更廣泛地為人們所樂于稱道,像一顆璀璨的明珠,久經歷史長河而不衰。
“貂蟬”也是作者虛構的典型形象之一。《三國志·魏 書·呂布》傳記云:“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11]從此資料所記看,歷史典籍中的貂蟬,只是一“侍婢”,一個若隱若現,似有似無,影子似的人物,與董卓、呂布無多大關系。而在羅貫中之《三國演義》中,貂蟬成了“自幼選入府中”的一名“年方二八,色伎俱佳”的歌伎。作者馳騁想象,把她置之于一場政治斗爭的漩渦。因此,把她塑造成了一名關心國家大事,有膽識,有智慧,有為正義事業而不計個人名節、安危且有獻身精神的優秀、完美的婦女形象,完成作者付于她的政治任務。最后,她成功地,甚至是創造性地執行了王允定下的美人計、連環計,較為順利地除掉了董卓。毛宗崗謂“十八路諸侯不能殺董卓,而一貂蟬足以殺之;劉、關、張三人不能勝呂布,而貂蟬一女子能勝之……女將軍真可畏哉!”此評本身就顯示出在封建社會中長期受輕視的婦女的強大力量。
總之,《三國演義》在充分占有歷史材料的基礎上,作家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匠心獨具地運用歷史材料,以藝術的手段,展示作家自己對歷史個性化的見解,對社會歷史的反思和思考,表達作家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對社會道德理想的渴望和追求,《三國演義》是杰出的歷史長篇小說,而“三分虛構”則是其最重要的藝術特色。
注釋:
[1]《魯迅全集》第四卷第289頁,第11行。
[2]《三國志·先主傳》第543頁,第1至2行。
[3]《三國演義》第16頁,第13行。
[4]《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第670頁,第6行。
[5]《三國志·吳志》卷二《孫權傳》注引《魏略》第 684頁,第32行;第685頁,第1行。
[6]《四書五經·論語·述而》第86頁,第8行。
[7]《三國志·呂布傳》第147頁,第5行。
[8]《三國志·魏書·張遼傳》第329頁,第9至11行。
[9]《三國志·武帝紀》第11頁,第22至23行;第12頁,第12行。
[10]《三國志·關羽傳》第582頁,第12至14行。
[11]《三國志·魏書·呂布》第142頁,第7至8行。
[12]《魯迅全集·中國小說史略》第104頁,第5至6行。
[13]《三國志·武帝紀》第5頁,第5至6行。
參考文獻:
[1]魯迅 《魯迅全集·中 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 九九七年·北京書號11029·5351。
[2]陳壽 《三國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 書號[SBN7-80518-485-2。
[3]羅貫中 《三國演義》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書號。
[4]陳其欣 《名家解讀三國演義》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8年 書號[SBN7-20902202-3。
[5]宋元人 《四書五經·論語》天津市古籍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