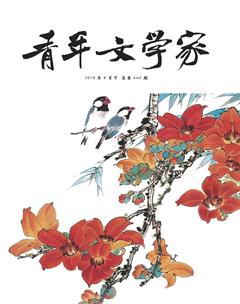辜鴻銘與理雅各英譯《論語》版本的對比分析
魏聰聰
摘 要:創造性叛逆在文學翻譯中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策略和手段,它是譯者充分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對原文所進行的二次創作,目的是使譯文更加符合目的語的表達習慣以及目的語讀者的閱讀習慣。本文將在語言和文化意象兩個層面,通過對辜鴻銘和理雅各版本英譯《論語》的分析,突出體現辜譯版本的創造性叛逆,深入探究在譯者所處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下想要傳達的文化信息以及《論語》的內涵和精髓。
關鍵詞:創造性叛逆;辜鴻銘;《論語》;理雅各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4-0-02
晚清時期,西方傳教士理雅各因將《論語》翻譯成英文版本而獲得巨大關注,這一做法為西方各國逐步開始接觸和了解中國文化構建了重要的橋梁。但在辜鴻銘看來,理雅各雖然對中國各類經典作品有廣泛深入的了解,但他只是一個不懂得變通的“權威”而已,他所使用的術語是粗糙、不恰當的,譯文中的不準確之處隨處可見,缺乏對文化整體的揣摩和把握。因此,以傳遞真正的孔子及儒家思想并使西方讀者更為徹底的理解文本內容為目標,辜鴻銘創造性叛逆地翻譯了孔子和他弟子的談話,盡可能消除西方讀者的陌生和古怪感,以期使其翻譯的《論語》能夠更加貼近目的語讀者。
創造性叛逆就是譯者在某個特定的創作動機和創作目的的驅使下運用某些技巧和手段,運用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對原作進行重構和再詮釋的一種翻譯行為。筆者接下來將從語言和文化意象兩個層面對辜鴻銘和理雅各英譯《論語》版本的創造性叛逆進行對比分析,希望對今后英譯《論語》的研究者起到借鑒作用。
一、語言層面
1、貫穿《論語》的核心詞——“仁”的翻譯
據統計,在《論語》中,“仁”大約共出現了109次,是一個使用頻率非常高的字,而且每一次的出現并非體現的都是同一種含義,這也就說明“仁”在孔子的心中具有豐富的內涵和與眾不同的地位。在辜鴻銘的版本中,他分別用“moral character”、“moral life”來解釋“仁”,更加傾向于從西方讀者所熟悉的哲學角度入手,以此代表儒家生活方式的理想局面。在《論語》中,“仁”的含義非常寬泛,從個人的品格培養,到治理社會和國家的手段都包含在“仁”這一體系當中,理雅各所給出的“virtue”、“perfect virtue”僅將“仁”界定在“美德”這一片面的解釋,“moral”一詞則是上升到了“道德”的范疇,涉及的層面更廣、層次更深,因此更貼近于“仁”的表達,同時也充分展現了譯者為迎合目的語讀者所發揮出的主觀能動性。
2、修辭格的翻譯
例: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辜譯: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理譯:Tsze-kung said, “What do you pronounce concerning the poor man who yet does not flatter, and the rich man who is not proud?”
本句辜譯文的突出特色就是體現出了原句中對仗的修辭手法,與理的譯文相比更顯文采。“To be…and yet not to be…”的翻譯不僅在句式和字數上完美符合,而且還精確地表達出原文對應的含義,言簡意賅,韻律和諧,使得譯文兼具原文的語言特色和美感,體現了孔子言語當中的智慧,也十分具備創造性叛逆的特色。
二、文化意象層面
1、專有名詞的翻譯
在《論語》提到了《詩》三百,亦稱《詩經》。《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因此,與理雅各將《詩經》籠統地翻譯為“the Book of Poetry”相比,深諳中國文化的辜鴻銘將其拆分譯成“The book of Ballads, Songs and Psalms”,并且辜還為其添加注釋:“Now called the Canon of Poetry, one of the so-called five Classics, in the Bible of China.”可以看出,通過將中國的《詩經》與西方的《圣經》做類比,會讓西方讀者更加了解《詩經》這類經典的文化古籍在中國的地位和貢獻。在此指出,添加注釋也是辜鴻銘發揮其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方面,很多時候他采用了意譯和歸化的方法,使譯文的表達向目的語讀者靠攏,增強了譯文的欣賞性和可讀性。
2、物質和社會文化名詞的翻譯
孔子在周游到衛國時,衛國國君衛靈公曾向孔子請教軍事策略,孔子將“俎豆之事”和“軍旅之事”分別來代替他想表達的“和平的藝術”以及“戰爭的藝術”,從而婉拒了衛靈公的請求。
“俎”和“豆”是中國古代祭祀時用于陳置食物的禮器,想要合適的翻譯出這類帶有文化內涵的器皿名稱并非易事,而且這一物品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說都很陌生,更何況是對中國古代祭祀禮儀不甚了解的西方讀者。因此,辜在譯文中省略了對這一物品的解釋,直接將其引申為“the arts of peace”。理雅各將“俎豆之事”和“軍旅之事”直譯為“sacrificial vessels”和“military matters”,很容易讓西方讀者摸不著頭腦,而辜譯的“the arts of peace”和“the art of war”就體現出了一種鮮明的對比,雖然省略了對這兩種文化物品的意象的解釋,但如此就更有助于西方讀者的理解,因此這一省略也是很有必要的。
3、宗教文化名詞的翻譯
例: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在古代中國,天是皇權的象征,而在西方“god”是神權的象征。在此句中,辜將“天命”譯成“Laws of God”是想讓西方人明白,中國人也有自己所敬仰和信奉的“上帝”,而且這個信仰在人們心中的地位是根深蒂固的,反觀理譯的“heaven”則是較為普通的一種譯法,并不會讓讀者產生相對應的聯想,因而在某些方面缺乏了創造力。另外,辜鴻銘將“圣人”譯成“holy men”,也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與理雅各選擇的“sage”一詞相比是完全西化的一種翻譯方法。盡管中西方宗教文化千差萬別,但辜采取的歸化策略使譯文更加平順,也想通過西方人所熟知的事物讓其更加認同中國文化。
《論語》中還有一處提及“天命”的典型例句存在于孔子劃分自己人生階段以及修行過程的一句至理名言中,即“五十而知天命”。該句的“天命”一詞的翻譯也被辜賦予了濃厚的宗教色彩:“the truth in religion”,而理僅譯為“truth”,可見,辜鴻銘在對宗教文化名詞的翻譯上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和風格,他的目的是通過西方人所熟知的事物讓他們更加認同中國文化,同時也更加能夠凸顯出創造性叛逆的特色。
三、總結
辜鴻銘《論語》英譯本秉持著一種讓西方讀者與中國傳統文化更為貼近的想法,更充分地發揮了譯者的主觀能動性,與理雅各采取的直譯、硬譯等策略相比,他的翻譯更具有創造性叛逆的特色。不能否認,辜譯本的出現不僅有助于西方讀者對《論語》進行深刻理解,還作為中西方文化溝通和傳遞的橋梁,將中國經典的文化作品推廣到世界,改變了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化的刻板認知,提高了中國文化的地位和影響力。作為第一部中國人自己翻譯的《論語》,在當時的環境下,辜鴻銘作為最具有開拓精神的譯者,為使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這在當時實屬不易。
參考文獻:
[1]辜鴻銘. 辜鴻銘講論語[M].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
[2]辜鴻銘. 論語(英譯)[M]. 黃興濤. 辜鴻銘文集[C]. 海南出版社,1996.
[3]丁莉. 從譯者主體性角度看辜鴻銘的儒經翻譯[D]. 西南財經大學,2008.
[4]富蘇蘇. 論辜鴻銘《論語》英譯本中譯者創造性叛逆的表現[D]. 河北大學,2011.
[5]劉婷. 辜鴻銘《論語》英譯本中的主體間性研究[D]. 寧波大學,2014.
[6]徐晴光. 對比分析《論語》英譯版譯者主體性[D]. 陜西師范大學,2013.
[7]張樂園. 《論語》辜鴻銘譯本文化意象的翻譯研究[D]. 曲阜師范大學,2014.
[8]孫建昌. 論翻譯的創造性叛逆[J]. 山東外語教學,2002,(6): 93-95.
[9]謝天振. 論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J]. 上海外國語學院院報,1992,(1): 3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