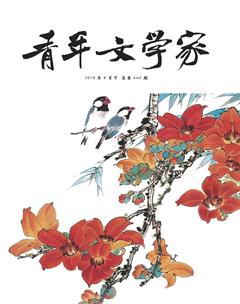淺析《逃離》對歐·亨利式結尾的繼承與發展
摘 要:《逃離》(Runaway)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麗絲·門羅的代表作,筆者研究發現:門羅在其短篇小說集《逃離》中大量運用了歐·亨利式的結尾,這一寫作技巧的運用是其情節更加引人入勝的催化劑。本文通過對比研究《逃離》的結尾與歐·亨利式結尾,旨在探析艾麗絲·門羅對歐式結尾的繼承與發展。
關鍵詞:《逃離》;歐·亨利式結尾;繼承;發展
作者簡介:林妮(1990-),女,漢,福建仙游人,碩士研究生,六盤水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英語教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研究和生態批評研究。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4--02
歐·亨利式結尾在小說結局時往往奇峰突起,令人始料不及,轉念一想,卻又覺得合情合理。它最大的特點就是讀者沒有讀到最后,永遠不會知道故事怎樣收場,它留給讀者的永遠都是期待和懸念。當底牌一張張慢慢揭開,故事的發展往往充滿變數——要么出其不意,始料未及;要么柳暗花明,豁然開朗;要么著力突轉,驚愕叫絕。但是,其小說敘事描寫都很流暢,絕不是為了“波瀾起伏”而單純地故弄玄虛、制造噱頭或者荒誕不經、胡編亂造,小說情節一定有其故事的合理性,往往能呈現一個特定背景下的深刻主題。這種在描述效果上符合人們的邏輯、在結局時卻又讓人大呼意外的寫作風格,正是歐·亨利式結尾獨特藝術魅力的根本所在。
門羅在《逃離》中繼承并發展了歐·亨利的這一寫作技巧。她為每個故事都設定了一個發展方向,當讀者深陷于故事情節的發展時,卻突然峰回路轉,出現顛覆性的情節與結尾,故事的最后總是讓讀者感到意外。
1、《逃離》中“歐式結尾”的繼承
“歐式結尾”是作品更加引人入勝的催化劑,門羅對這種歐式結尾的嫻熟運用在其小說集《逃離》中是比比皆是的——
在小說《播弄》中,門羅為主人公們安排了一個個浪漫的約會,卻依然安排了一個出其不意的結局。小說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年輕的女士——若冰,她“從來不曾有過一個情人抑或是男朋友”[2]255,因此她對愛情有著強烈的渴望。若冰與她那患有“嚴重的,持續不斷的哮喘病”[2]253的姐姐喬安娜生活在一起,為了能夠暫時的脫離喬安娜的控制范圍,她每年都會秘密地去鄰近小鎮看一出莎士比亞的戲劇。有一年,當若冰去看喜劇的時候,她的錢包丟失了,她被滯留在那個小鎮了。幸運的是,她遇到了善良的丹尼爾。這對年齡相差十歲左右的男女在偶然相遇后,進行了試探性的相互交往。這樣的邂逅,在讀者看來,必定會開啟一段美好的愛情。兩人約定一年后再見,這樣的約定為讀者帶來了憧憬和期望。一年后,女主人公如約前來,卻被男子生硬地拒絕,狼狽而歸,從此她不再相信男人的諾言,她覺得“穿褲子的東西沒一個可信的”[2]276。門羅就這樣粗魯地將讀者心中浪漫而又美好的想象打碎了,卻又不給讀者任何的解釋。直到四十年后,一份醫療檔案的出現說明一切只是一場誤會——那個生硬粗暴地對待前來赴約的若冰的男人,其實是丹尼爾的孿生智障兄弟。然而,四十年過去了,一切都無可挽回,甚至曾經發生的那次蓬勃的愛情想象也不再有意義了。生活已經在悄然之間改變了軌道,“現在已很難說得清楚,當日那番遭遇是幸或不幸”[2]285。通過突轉的結尾,門羅真正寫出了生活的那種無可奈何感,寫出了生活的本質。正是這樣反轉的方式、詭異的結尾,她給予讀者更多的思考空間,也使其小說更加有力量、有深度、有綿延回味的可能。
再者,門羅總是喜歡在故事的最后揭示人物不為人知、出人意料的身份或本質。在短篇小說《激情》中,門羅正是通過這一寫作技巧使得讀者更加清晰地了解故事人物性格。
格蕾絲是一個由舅公舅婆帶大的孤兒,高中畢業后本應接手舅公藤椅生意的她卻選擇到一家小旅店做一名女招待,以此“多體味一些人生經驗”[2]178。在旅館里,格雷斯遇到了應該說是完美的對象——工程師莫里,他不僅家境良好,而且秉性溫柔。因為莫里的“完美”,格蕾絲接受了他的求婚。正當讀者期待格蕾絲的婚禮時,故事卻駛向了另一個方向。感恩節時,格蕾絲的腳被劃傷,尼爾為她包扎傷口還開車送她去醫院處理傷口,她突然覺得尼爾才是她想要的人。于是,在那個下午,格蕾絲選擇逃離和背叛自己的男友,與尼爾開始一場探險與逃離。格蕾絲“以為那是接觸的關系。嘴唇、舌頭、皮膚、身體,還有骨骼上的碰撞。是燃燒。是激情。”[2]206正當我們要為格蕾絲的真愛之旅歡呼雀躍時,卻赫然發現那只是尼爾在酒精作用下的調戲而已,“那根本就是一場兒戲”[2]206。故事的最后,莫里原諒了格蕾絲,想與她重新開始,此時的格蕾絲悔不當初,本以為她已放棄尋求刺激與真愛,只會尋求一份穩定的婚姻,但是門羅又設置了一個“歐式結尾”——格蕾絲最終拒絕了莫里。
《激情》中的突轉幾乎都是不可究詰的。門羅沒有向讀者交代格蕾絲為什么喜歡尼爾,沒有說明尼爾為何酗酒輕生,也沒有解釋格蕾絲為何再次拒絕莫里并接受了內心覺得不應該接受的1000美元的支票,更沒有解釋格蕾絲為什么渴望“她的生活可以有一個新的開端”[2]209……小說中存在著許多沒有解決的問題,而且門羅也并不想要去解決這些問題。伴隨著重重疑問,故事的發展方向突然急轉,出現令人驚愕的結果,一切疑問便也就豁然開朗。通過這些著力突轉,門羅向讀者展現了一個全新的格蕾絲——她不是個傳統、可憐的孤兒,她也不是個安于舒適安穩生活的普通女人,而是一個敢于直面現實、向往真愛、對生活充滿希冀的勇敢女性。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逃離》的結尾與“歐式結尾”的相同之處在于二者都為故事設定了一個穩定的發展方向,而這個方向誘導讀者根據自身的知識積淀和文本的線索對文本做出預期反應和判斷,就在這時兩位作者卻將這一方向斬斷,使故事產生相悖的結果,使讀者始料不及。這一技巧的應用大大地顛覆了讀者的猜想,制造了出人意料的結果,并且塑造了更為全面的人物形象。
2、《逃離》對“歐式結尾”的發展
“歐式結尾”往往奇峰突起,徹底顛覆人物形象,或者人物的命運發生完全逆轉,其結局也是讓讀者大跌眼鏡。這樣的結尾對于讀者而言更具有吸引力和啟迪性,這樣的作品旨在告誡人們:意料中的事情往往只存在于人們的想象之中,意料之外的結果才是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
門羅繼承了“歐式結尾”這一寫作技巧,但她也進行了創新與發展:一是出人意料的效果是由主人公在已知的矛盾和掙扎中的選擇所造就出來的;二是門羅的作品將女性生活與“歐式結尾”有機的結合,使得女性的處境與地位更引人深思。
(1)主人公在矛盾與掙扎的選擇中造就出人意料的結果。
歐·亨利小說的意外結尾是在主人公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例如:想要改過自新卻意外被抓的蘇比、犧牲自我給彼此驚喜卻釀成“意外”的杰姆、德拉夫婦等,可以說主人公的態度幾乎沒有直接影響到故事情節的突轉。但是門羅短篇小說集《逃離》中令人驚訝的結果往往是發生在主人公的最后抉擇中的,換言之,令讀者感到訝異的是主人公的最后抉擇。
在門羅的同名短篇小說《逃離》中,故事的女主人公卡拉得到了鄰居西爾維婭的幫助,有機會逃離令人窒息的生活和令人窒息的老公。意外的是,她在逃離的路途中放棄了尋找自我和新生活的機遇,而是選擇了重新回到克拉克的身邊、回到那令人窒息的婚姻生活中。
在《匆匆》中,出人意料的結尾便是朱麗葉拒絕病危母親請求她再次回來探望她的請求。故事中,因為父母對埃里克的反對,朱麗葉21歲離家出走,與埃里克未婚同居,與父母十幾年不曾謀面。但當朱麗葉攜一歲的女兒佩內洛普回娘家,看到身患重病的母親時,她心中涌起無盡的憐憫與愧疚,她責怪父親對母親缺少關愛,對到家里來幫傭的艾琳沒好氣,對其苦難的身世毫無憐憫,甚至猜忌怨憤父親與艾琳的關系。就當讀者為這“冰釋前嫌”、“母慈女孝”的場景感動時,朱麗葉卻回絕了病重母親提出“待我將死之時,你要再回來看看我”的懇求[2]134。
而《激情》中的格蕾絲為讀者展現的意外便是——源于對愛情和激情的向往,她放棄了家境良好、秉性溫柔的工程師莫里以及他所象征的穩定舒適的婚姻生活,而選擇了與她未婚夫的哥哥尼爾開始一場探險與逃離。即使最后面對尼爾的玩弄、尼爾的死亡以及莫里的原諒,她依然堅定心中對愛情的憧憬,而拒絕莫里所提供的穩定舒適卻了無生趣的婚姻生活。
(2)女性生活與“歐式結尾”的結合。
將生活描寫與“歐式結尾”有機的結合,會使得故事情節更跌宕起伏、抓人眼球。然而,通過比較發現,歐·亨利的作品反映的是社會問題,關注環境對人的影響;而門羅的作品多描寫的是女性生活,關注的是文化對人的影響,如普通鄉村女性在婚姻關系、家庭關系和宗教關系中的處境與態度。
在《逃離》中,因為極度“需要一種更為真實的生活”[2]33,卡拉選擇與克拉克私奔,逃離了父母。然而,在短暫的新婚后克拉克的暴躁脾氣與惡習暴露無遺,這樣令人窒息的婚姻生活與她想要的“更為真實的生活”大相徑庭。她在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中苦苦掙扎,選擇了逃離這令人失望的生活,去尋找自我。令讀者失望的是,卡拉最終仍然無法擺脫父權制社會的掌控,她寧愿被暴躁、齷蹉的丈夫蹂躪在不幸的生活里,也不愿逃離丈夫去尋求新生活。
《侵犯》的最后展現了勞蓮戲劇性的出生秘密,為讀者展現了復雜的母女關系。勞蓮的父親哈里與母親艾琳水火不容,常常發生家庭戰爭。父親哈里告訴她,她曾有一個姐姐,因為勞蓮的到來,艾琳忍受不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負擔,想要墮胎,但勞蓮的姐姐最終死在艾琳親手釀造的車禍當中,因為愧疚的原因,艾琳對勞蓮忽冷忽熱。從父親那里知道的這一切“給予了她一種尷尬的感覺和特殊的哀傷”[2]220。然而,隨著德爾芬的出現,艾琳與勞蓮的關系發生了改變,艾琳開始害怕失去勞蓮并對她關懷備至。隨著故事的發展,門羅告訴讀者哈里和艾琳曾領養過德爾芬的女兒,并給她取名為“勞蓮”,就在讀者以為勞蓮是德爾芬的親生女兒時,故事的結尾突轉,令人驚愕不已——死去的那個嬰兒才是德爾芬的親生女兒,現在的勞蓮只是因為哈里夫婦對這個名字的喜愛而沿用了這個名字。門羅用“歐式結尾”的突轉展現跌宕起伏的情節,也表現了勞蓮與艾琳、德爾芬之間復雜的母女關系。
同樣,在《匆匆》和《沉寂》中的歐亨利式突轉表現了宗教對女性生活的影響。朱麗葉與母親薩拉的牧師唐恩就上帝的存在進行了一段激烈的辯論。朱麗葉“不信上帝”、“不相信有神的恩典”,她不想讓她的女兒佩內洛普“在上帝的謊言中長大”[2]127。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女兒佩內洛普在21歲的時候為了尋求精神的寄托離家出走了。這時,朱麗葉才開始思考宗教信仰對兒童成長的重要性。
通過以上的分析研究,不難發現門羅的確繼承了歐·亨利式的結尾,不過她用自己的方式闡釋了“歐式結尾”——她充分利用了女性在生活的矛盾和掙扎中將作出的選擇吊足讀者的胃口,然后給出與讀者期望背道而馳的結果來,而這些結果卻往往就是生活的真實寫照;再者,門羅的作品多描寫的是女性生活,關注的是文化對人的影響,如普通鄉村女性在婚姻關系、家庭關系和宗教關系中的處境與態度。
參考文獻:
[1]歐·亨利. 歐·亨利小說集[EB/OL]. http://novel.tingroom.com/html/book/show/42/, 2005.03.12.
[2]艾麗絲·門羅. 《逃離》[M].李文俊,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