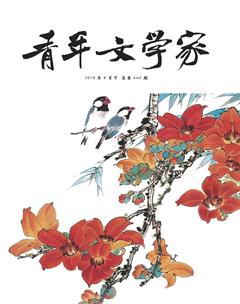中國傳統道、儒、釋生態倫理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馬勝男
摘 要: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人們常常習慣用“天人關系”來描述人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各家學派也用自己的學說觀點來闡述這樣一個關系,并提出一些相關的生態倫理思想進而涵蓋一些直觀樸素的生態保護做法。這些總體上都傳遞出我國古代人民尊重自然、要求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理念。中國自古就重視對環境的維護和對資源的合理利用,古代道家、儒家、佛家思想中都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智慧,能很好地給予現代生態倫理一定的啟示。
關鍵詞:天人關系;尊道貴德;兼愛萬物;萬物平等;生態倫理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4--02
隨著工業化的不斷深入,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的矛盾越發尖銳,如何更好地處理兩者的關系是一門生態的智慧,當下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不斷重視,國務院生態環境部的全新亮相,人們也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了生態環境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我們不妨放眼過去,回溯到中國古代傳統思想中去探尋古人的生態智慧,挖這些思想巨大的當代價值。
一、道家“尊道貴德”生態思想和“無為”的實踐尺度
在中國充滿智慧的生態文明體系中,道家學派的生態倫理思想最為豐富,它可以自成體系。道家的生態思想文化在先秦時期最初形成,莊子最早闡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對儒家甚至西方以及后來很多相關的生態思想等等都產生了比較深遠的影響。當代的人文主義物理學家F·卡普拉在他的《超凡的智慧》這本書中寫道:“在諸偉大傳統中,據我看來,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態智慧,它強調在自然的循環過程中,個人和社會的一切現象和潛在兩者的基本一致[1]。”
道家生態學討論人與自然的關系、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提出了“道生萬物”、“天人合一”、“尊道貴德”這三個最為基本的要素。
道家生態倫理思想以“道”為根本。老子第42章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意即獨一無二的“道”分化為“陰陽”二氣,這二氣相互作用形成“沖和”或者“中和”之氣,在這基礎上“三氣”、“五行”、“八卦”皆含道性[2],進而造就紛繁復雜的天地萬物。道家學說肯定了道和氣在萬物生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老子所描述的其實是一個樸素的有機整體論的世界觀,天地、人、萬物同根同源,是一體并且平等的,并無高低貴賤之分。
因此,“天人合一”是道教對人天和諧關系的一種最高追求。錢穆先生說:“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3]。”這里的“合”包含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意愿,世間萬物的天然狀態本身就是豐裕而且美好的,應該要追求和維護它本真的和諧美好狀態。
“尊道貴德”包含的是道教對天地、自然的一種尊重,是“天地父母”的杰出體現,像孝敬父母一樣去尊重天地萬物,不能肆意地去加以傷害,萬物本是同根同源,必須要重視萬物的興旺發達,人類并非是主宰者,天地萬物都值得人類去尊重。而且,父母能獎善罰惡,人類對自然環境進行破壞,必然也是會受到自然的懲罰的。道家學說要求人的行為順應自然,與自然協調,這與幾千年以后我們現在所倡導的生態價值觀是根本上一致的。道教對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深刻理解,無疑是有著生態學意義和跨時代的永恒價值的。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人與自然統一的趨勢越來越弱,生態文明的危機也需要我們重新審視道家這一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
當代很多學者探討動物權利論,受佛教文化影響戒殺護生的生態實踐觀,這些內容在道教戒律當中其實均有或輕或重的體現,值得后續更好地去挖掘。
道家的生態倫理思想在指導實踐中的核心體現就是一種自然無為的實踐觀。道家所說的“無為”意思是萬事萬物都有它自己運動的規律,人類不應該人為去干涉這些自然的運動規律,追求返璞歸真,反對人力加之于自然。這里的“無為”在指導實踐層面主要有三層含義:一、順著天然規律自然的行為,這種行為不違背事物的本性,讓事物生活自由自在。二、不私為、不利己而為。就是說“無為”之為不應該包含著明顯的私欲和利己的動機。不私為是一種善為。三、無為是一種不過度而為。任何事物都是有一定限度的。這些含義就要求我們在面對我們生存的地球生態環境時,要順應生物的生存法則和地球發展的普遍規律,不要去打破其原本的平衡,如果平衡已經不幸被打破了,那也要減少一些人類沒有意義的干預,自然界有自己平衡和修復的周期過程。放在中國現在的大環境來看,要在追求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還要兼顧到生態效益。按照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權衡好眼前暫時的看得見的經濟效益與長遠的摸不著的生態效益之間的關系。
二、儒家“兼愛萬物”的生態智慧和“養發有時、物盡其用”的行為標準
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對自然的態度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與道家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比如“天人合一”理念等等。在具體做法上,是有差異的。但追求的總目標都是人與自然的和諧,自始至終未曾改變。
孔子首先提出“仁民愛物”的主張,提出有仁智的人對自然界的山山水水也寄予了無限的愛。儒家將“仁愛”、道德關懷自人際拓展至自然萬物。正如《春秋繁露、仁義法》中記載道:“質于愛民,以下至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以謂仁?”孟子在這此 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言:“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荀子繼承并不斷發展這一思想,宋代張載更是將這種“利物”、“兼愛萬物”的思想推廣到了廣闊的非生命物質。
儒家仁民愛物的思想與環境倫理思想充分切合,保證每個生物獲得人類的尊重。而后來西方的環境倫理可能更多地從價值論這一角度去衡量和論證。儒家思想強調人類的發展不應該去威脅自然的完整,或其他物種的生存。人類應該適當地對待所有生物,保護它們免于殘暴、受苦和所有不需要的殺害[4]。
儒家學說看來,人類最高的道德責任就是尊重生命,愛所有的人和動物,而不是只把人類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自然界中的每一個生物的存在都有它的意義。儒家生態倫理主張的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發展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提供了寶貴的理論源泉。
儒家思想在實踐層面,更注重的是一種生態資源按時使用、節約使用的實踐觀,主張對資源合理開發。《管子·八觀》中有: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要求人們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要按照規定的時節,在恰當的時刻進行,“取之以時”而不是沒有節制。山林開采、水澤捕魚、采集狩獵等等都應當“以時禁發,一時養發”。尊重萬物生長規律,不該取之時不取。《論語·述而第七》中記錄說:“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意思是孔子捕魚不用網用的是釣竿,用帶生絲的箭射鳥但不射殺巢宿的鳥[5]。注意永續利用而不是一次兩次趕盡殺絕。這也顯示了生態資源節用觀。自然資源的使用是有一個限度的,不加以節制的濫用,自然資源終將會匱乏和枯竭,影響人類的繁衍生息和持續發展。孟子、荀子也進一步豐富發展了管子的思想,孟子認為“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在按照時令獲取資源的同時,還提倡生物資源的保護,荀子將資源保護和環境保護思想進一步系統化和具體化,這又是一大標志性的進步。這與可持續發展觀一脈相承。
儒家思想中以孔孟荀為代表的自覺有意識地去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思想,就是既滿足了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21世紀生態問題產生和擴大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和浪費式的運用。合理使用資源和保護資源的對策著實仍值得當下好好反思和運用,這些思想價值完全沒有過時。
三、佛家“緣起論”、“平等觀”的生態導向以及“不殺生”的道德規范
剝去宗教的神秘袈裟,佛教禪學對生態倫理學的貢獻也是巨大的。佛教研究“緣起”,這一詞的含義是“現象界的一切存在都是由種種條件和合而成的,都有其必然的因緣,而不是孤立的存在。[6]”由此看來佛教觀點強調生命和環境的整體性。佛家認為事物與事物之間相互聯系,不可分割。割裂了事物之間的關系就很可能導致對事物本性的錯誤理解,只有置于整體中,才可以充分確定事物的本真,確定事物的存在。佛教從善惡觀的維度觀察意識界,追求整體論,相互依賴相互依存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佛教用“獅子勝相剎,側住覆世界,如因陀羅網,或諸珍寶,”來比喻整體性的關系[7]。
佛教提倡萬物平等的生態倫理觀。在佛教神學當中,人類與自然之間是沒有明顯的界限 的。正所謂“依正不二”:“佛”是“依”即環境,“正”是生命主體,一切眾生都有佛性,而且他們都是平等的,這里不僅包含了人包含了各種生物,也囊括了一切無生命的存在,草木國土、山河大地等等。雖然佛教肯定佛陀是出于人間,肯定人類可以成佛,但是并沒有“唯人獨尊”。即便“無情之物”,也不能隨意處置,“無情有性”,都是具有佛性的。這一理論就從根本上奠定了世界上所有的存在物都平等的思想。佛教揭示的觀點是徹底的非人類中心主義,有情眾生具有價值與西方的生物平等論也有著共通的地方。在處理人與環境的關系中,現代環境或者生態倫理學也可以從中獲得體悟,對生態倫理學的構建有著啟發性的意義。天地萬物平等,包含著對萬物的關心關切,體現出了佛教的寬廣胸襟。佛教強調自然界萬物都是有生趣的,均值得我們去珍惜和善待,也遠已經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
從萬物平等的角度出發,佛教包含著一種“普度眾生”的慈悲情懷。佛法上的“與樂”稱為“慈”,“拔苦”叫做 “悲”。《大智度論》有言: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就是意味著給所有的人和生物快樂,消去所有生命的痛苦。不僅限于自己的愛人、親人,而是遍及萬事萬物,這種尊重生命、關愛生命、普度眾生的慈悲情懷在生態倫理學研究中有著重要的意義,更加值得稱頌。
佛教的生態倫理思想表現出境心清凈的生態實踐觀。兩個重要的表現就是食素和放生。“不殺生”是佛教的道德戒律之首,是佛教徒終身都應該恪守的道德信條。殺生包括了對人對所有生物的傷害。剝奪其他人和生物生命的權力是惡的,在轉世再生和因果報應的信仰基礎上,是絕對不允許傷害生命,給生命帶來痛苦的。佛教食素的傳統和生活方式以及不殺生、放生等行為對保護野生動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盡管佛教較少地能從現實意義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但是它對人心靈的一種調整也是在實踐中為建設美好的生態環境而不懈努力著。
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思想對倡導可持續發展的21世紀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從黨的十七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將“生態文明建設”明確作為我國戰略發展的重要主題之一。十八大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地位,十九大又把我們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認識提高了一個嶄新的高度。生態文明建設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下任重道遠[8]。“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思想早在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里積淀著。這些都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延續的道德基礎,更是現代生態哲學、環境倫理健康發展的無盡寶藏,于當代都有著重要意義,也必須有助于生態倫理學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余謀昌,王耀先,《環境倫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
[2]樂愛國,《道教生態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5月.
[3]錢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載劉夢溪主編《中國文化》1991年8月第4期.
[4]楊冠政.《環境倫理學概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9月.
[5]任俊華,劉曉華,《環境倫理的文化闡釋——中國古代生態智慧探考》,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3月.
[6]魏德東.佛教的生態觀[J]中國社會科學. 1995(5).
[7]李功錦. 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及其當代價值[D].渤海大學,2014.
[8]林建華. 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場綠色革命性變革[N]. 北京日報,2017-12-25(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