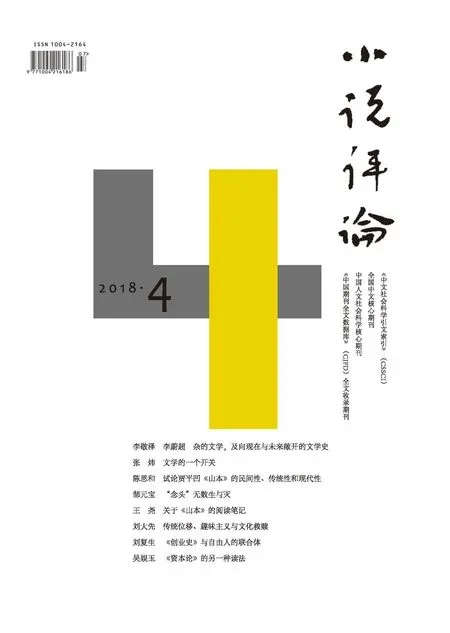論葉廣芩系列小說《去年天氣舊亭臺》的藝術成就
王麗麗
葉赫那拉氏的出身,使葉廣芩之往事追憶映襯著老北京的厚重歷史與沒落貴族情感的豐富意蘊。《去年天氣舊亭臺》由九個短篇組成,分別是《太陽宮》《月亮門》《鬼子墳》《后罩樓》《扶桑館》《樹德橋》《唱晚亭》《黃金臺》《苦雨齋》。從九個題目來看,每一個短篇均以三個字命名,又形成三組字面意義相對的鼎足對,整齊而富有匠心。九個短篇看似各自獨立,但其內在又相互聯系,是一個精心結構的有機整體。這種聯系既體現在人物的一脈相承上,如“我”、蘇惠、小四兒、大芳這些人物在幾個篇章中都有貫穿,也體現在作家情感與思想的融會貫通中。整部小說中篇目之設置亦有時間的先后承續性,從童年、少年到青年、中年,逐漸步入老年的時間序列中,呈現出一種流動性與整體性。本文試就葉廣芩《去年天氣舊亭臺》(以下簡稱《亭臺》)中諸作,從兒童視角、人性美丑、時代碰撞這三個角度去進行解讀。
一、兒童視角
所謂兒童視角,吳曉東認為,即“小說借助于兒童的眼光或口吻來講述故事,故事的呈現過程具有鮮明的兒童思維的特征,小說的調子、姿態、心理和價值準則,諸種文本結構、美感及意識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選定的兒童的敘事角度”。葉廣芩《亭臺》中的很多篇章都是從小時候的“我”切入敘述的。兒童視角的切入讓人感到小說中的“我”以一種不同于成人的新奇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兒童的視角如此美好,機敏活潑又意趣盎然,將散落于童年歲月的一顆顆記憶珍珠穿起來。用兒童的視角去感知世界和了解世界,使成人眼中有些平淡乏味的現實生活變得豐富而奇妙。
作家用兒童視角寫寂寞的童年,透過兒童的心靈世界,展示出人類精神狀態最底層的一部分。《太陽宮》中寫“日子過得有一搭沒一搭,挺憋悶,主要是沒有‘事情’可干。我的活動范圍就是院里,到胡同都得征得媽的許可。”沒有什么干的事就唱歌,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最后唱累了,就趴在臺階上睡著了。無事可做,就一直“看下雨,看下雨,看得我越來越困,眼睛睜不開了……砰!腦袋撞在玻璃上。”從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作者寂寞的童年,以及寂寞童年中飛揚的想象力。其實,人性中普遍有深刻的寂寞與孤獨感。也許,在成人的世界中會認為小孩懂什么,小孩不會寂寞。然而,小說正是從這樣的兒童視角,讓我們看到兒童的寂寞,仿佛是人類童年的寂寞,帶著一種對人類與生俱來即被疏離的深沉透視,兒童的天真單純與兒童的孤獨寂寞在小說中融為一體,令人回味與深思。
在《月亮門》中,作家從兒童的視角寫出了孩子對自己身體成長的懵懂與好奇。在兒童視角的關照下,對于胸罩、例假、生孩子這樣一些話題,充滿了新奇而又神秘的朦朧色彩。一幕幕的鬧劇讓人忍俊不禁,也展現出兒童世界的天真爛漫和純真活潑,會勾起很多人對童年的回憶。《月亮門》中孩子們對蘇惠媽媽的敬慕則體現出對美的向往與追求。在李立子看來,蘇惠媽媽比他漂亮的演員媽媽更美,因為蘇媽媽透露出嫻靜、淡雅、精致、從容的美,而且她總是對著他們微微笑著,有著孩子們喜歡的溫柔暖意。也許,在很多人的童年中,總有一些人會帶給他美的感覺,啟示他引領他去感受美追求美。這也是很多孩童世界中一種很重要的記憶。
在《亭臺》一書中,作家之所以采用兒童視角進行敘寫的原因,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思考。
首先,在葉廣芩小說中會較多運用兒童視角,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是作家寫作到一定階段后表達的一種內在需求和必然選擇。葉廣芩不是一開始就寫回憶性的家族小說的。在她的早期作品中,有《岸邊》《退位》《孿生》等一些表現農村和城鎮的小說。但正如作家自己所言,“我從80年代開始寫小說,我寫的很游離,是自己跟自己的游離,也就是說沒有寫進去自己生命的體驗,那時候我雖然寫了不少作品,但以北京文化為背景的作品從未進入過我創作視野的前臺,這可能與各種條件的限制有關,我回避了個人家族的文化背景,不光是不寫,連談也不愿意談,這甚至成為我的無意識。”但當她一旦碰觸到了兒童時代的經歷,作家終于以一種回望的姿態,找到了能夠融入自己生命體驗的適合自己的言說方式。所以說兒童視角的敘寫是作家對于自我和家族重新審視的一種途徑,是一次對自我和家國歷史進行觀照的心靈之旅。
其次,兒童視角也是展示作家詩意靈魂的一個窗口。從葉廣芩的很多自敘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敏銳、善感、孤獨、多思的自我形象。而童年的孤獨和善感也正是很多作家都會經歷的心靈體驗。通過兒童視角,讓我們看到作家童年的經歷與心靈觸角,展示出作家從童年時期即有的詩意心魂。
二、人性美丑
在《亭臺》中的很多篇章都對人性的善與惡進行了探討。作品呈現出對善的悲憫流露,對惡的痛快揭露,甚至包括挖掘出“我”的“惡”。小說將大歷史、小人物,人性的丑卑、光輝及復雜都展示得令人唏噓、感慨。
在《月亮門》中,作者塑造了郭梓仁這樣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小學教師形象。他的外號叫“瓜子仁”,堪稱一個人性惡的代表。在“文革”中,他成為一個上竄下跳的幫兇與小丑。他批判老七畫的畫時說,“什么都有階級性,人是這樣,花也是這樣,牡丹、芍藥代表了反動統治階級,菊花代表了逍遙派,水仙、蘭花是小資情調,喇叭花那是保皇派吹鼓手”。老七說怕曬太陽,因為對紫外線過敏,結果郭梓仁說紅太陽就是毛主席,害怕太陽就是和主席作對,給老七扣上了“大帽子”,最后被關進“牛棚”。通過這些事件,郭梓仁的卑鄙的人性之惡被揭示得淋漓盡致。一個卑鄙的人卻在那個時代如魚得水,可以宣判和掌握很多人的命運,更看出“文革”的黑暗與荒誕,也反映出作者對時代、世情、社會、文化的深沉思索。
《樹德橋》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敘述了歷史與人性。小說中的人物都是“牛棚”中的人,作者戲謔地稱這些“牛”都是從祖國的四面八方而來,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不遠萬里來到這片鹽堿荒地。這樣的戲謔里面有對荒誕歷史的無奈幽默與超脫審視。主管劉隊長生硬、粗暴;強大夫原來是獸醫,甚至還是喇嘛;牛樹德處境悲慘,飽受冤屈。牛樹德剛從海外歸來,中國話還沒完全學好,因為說話帶外國字,造反派就把他的聲帶用手術刀毀了,成為了啞巴。他雖是啞巴,不能言語,但他心里澄明如鏡。他解剖老鼠,認真研究,終于弄清了“五七”干校無端死人的罪魁是鼠疫,用英文寫出了病因,卻被無知的“我”“出賣”,最后被警車帶走。
小說中的主人公牛樹德是愛國的,他不留戀國外的優厚條件,學成毅然回國。盡管他深受迫害,但正直善良的人性卻從未泯滅,閃爍出一種高貴的人性之光。相反,“文革”的粗暴,很多人的愚弱 ,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在運動中缺乏理性與自知,對強權軟弱,對弱者殘忍,則顯示出荒謬歷史中的人性之惡。莫言說:“只描寫別人留給自己的傷痕,不描寫自己留給別人的傷痕,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揭示別人心中的惡,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惡,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悲劇,才能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憫。”葉廣芩的這篇小說,就具有這種“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度。
《唱晚亭》揭示了人性的貪欲。金家子孫為了金錢利益,把祖先留下來的一塊刻有“唱晚亭”的石頭千刀萬剮,等到郭老板說里面沒有玉,就大罵祖先是傻帽, “太陽的余暉中,‘唱晚亭’的石頭旁,同一個地點,同一個時間,一群金家子弟同樣在嘰嘰喳喳,與他們的祖輩比,沒了熱鬧的鑼鼓經,沒了悠揚的西皮流水,他們鬧騰的是另一個話題——錢。”在這兒,我們看到了后代的墜落,在精神上他們沒有了貴族的風雅追求,眼中只剩金錢利益。他們把祖宗留下來的一塊刻有“唱晚亭”的大石“碎尸萬段”。當他們見到這塊石頭時,想到的不是家族走過的風雨歷史,也沒有緬懷先人的悠遠情懷。他們粗暴地讓玉石廠一刀一刀切割這塊大石,只盼望切出玉來發財,而最后結果出來了,玉石廠說什么都沒有,而且要收一大筆費用時,他們個個都趕緊躲開了。在《唱晚亭》中,淋漓地展現了作者對一種庸俗淺薄人性的尖銳批判,他們滿嘴粗話,滿眼是錢。小說是對功利性生活態度的一種批判,也是對于一種矜持典雅的生活的追憶與眷戀。
不管是對人性之惡,還是人性之善的描寫,我們看到了葉廣芩目光穿越時代、歷史的睿智,也看到了作家用心魂去感悟和觸摸生命與人性的情懷。
三、時代碰撞
葉廣芩在《亭臺》的寫作中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將兒童的“我”與現在的“我”對接起來。兒童的“我”遇到的人與事,多年以后,再次出現。作家讓兒童時期隔著歲月的迷離回望和成年時期的理性審視、直面現實相遇合。不似當下很多回憶性的寫作,更多的是僅停留在回憶,從而容易形成一種牧歌式的贊美或傷感。葉廣芩作品的故事不停留在過往,透露出一種直面與逼視的勇氣與態度。在某種程度,這既體現出作家的一種寫作態度,也體現出一種生活態度,令人深思。
首先是景物的變化。在《太陽宮》中,兒時的太陽生氣勃勃,作家用“跳”出樹枝,“升”上天空這樣的詞語來形容那時的太陽。太陽給大地染上金色,風中的樹葉也有了金屬的聲音,人在陽光與微風中,變得澄澈透明,飄然如仙。在小說中可以看到在兒童眼中的萬物光輝,充滿了一種圣潔、光明、詩意的生命體驗。然而,幾十年后再次描寫北京又是另一幅圖景。滄海桑田,變化迅速。“提著一兜菜我站在汽車站,周圍林立的高樓讓我不知身在何處。太陽從東邊升起,太陽宮,太陽的宮殿,如今又有誰還知道它曾經的模樣?我想起了我要為太陽宮而寫的詩,幾十年了,一直沒有完成它,關鍵是再沒有看過那樣的日出,沒有過那樣的心情和感動。”
從前的日出那樣壯觀,那樣充滿詩意,而今的太陽放佛連自信都失去了,一切景物都失去了童年視角中的渾然天成與光輝動人,也許這不僅僅反映的是景物的客觀變化,更是多年以后,對物非人非的一種嗟嘆!而《太陽宮》最后的一句:“曹太陽,你是否還在人間?”也已經不僅是景物的變化,更是寫出了作者對兒時玩伴的一種深情呼喚,對純真的人與人之間情感的眷戀,對人事變遷的感慨。
在《黃金臺》中也有時代碰撞。有富商看中了黃金臺的名字和風水,要在那里修建大型的商場會所。這些有著赫連勃勃英武祖先的劉姓后人,有的已經拿著錢走了,一部分還在高舉風中飄蕩的黃旗,為這美麗的村莊做最后的堅守。在這里,文化與商業對抗,祖先與后人對照,光榮與金錢決斗,展示出作家直面時代碰撞時關于英雄、榮譽、夢想、村莊式微的一種深思與憂慮。
在葉廣芩的小說中,因為要寫出這種碰撞,所以在很多篇什中,除了兒童視角,又會有一個成熟女性視角的展現。這樣的從過去直至現在的復調視角的運用,使作品因為經過了時光的過濾,產生了厚重感與豐富性。過去與現在相碰撞,展示的依然是作家心底對于真善美的質樸追求,對于歷史、對于現實、對于人性的直接面對與深沉思索。
《苦雨齋》是《亭臺》中的最后一篇。雖然表面上是寫有手機有現代的生活,沒有很明顯的對過往的描繪,但實質上它是一種尋根,是受父親的指派,尋找一個多年失去聯絡的人,因此它依然是試圖完成過去與現在的一種連接,依然是一種時代碰撞。
作品中所體現的這種讓時代碰撞,直面現實的風格也是有原因的。在作家的生命歷程中,目睹了歷史與家族的巨大變遷,父親于1956年去世,她1968年離開北京,當過護士喂過豬,經歷過“中年待業”,這些生活的歷練與磨難,都化成了作家生命內在的一種獨特力量。她將幽默、大氣與深沉、哀婉融為一體,透露出直面生活、生命的能力,也形成了其作品獨特的美學風格。
注釋:
①吳曉東、倪文尖、羅崗:《回溯性敘事中的“兒童視角”》,《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1期。
②③⑤⑦⑧⑨葉廣芩:《去年天氣舊亭臺》,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5 頁、7-8頁、97頁、300頁、51頁、51頁。
④周燕芬、葉廣芩:《行走中的寫作——葉廣芩訪談》,《小說評論》2008年第5期。
⑥陳莉:《〈人生〉距離悲劇經典有多遠》,陜西學前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