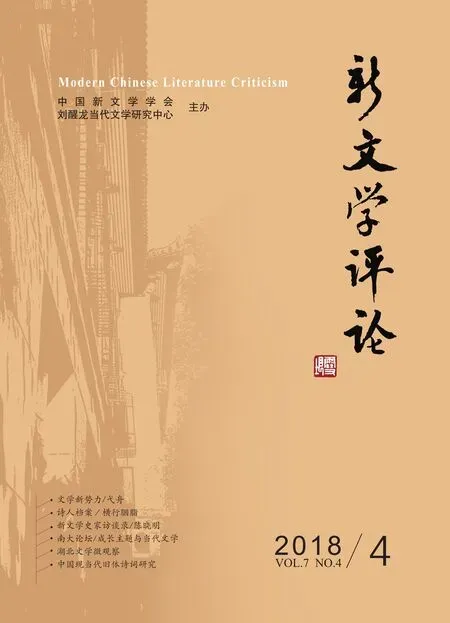“無法終結的”當代文學
———陳曉明先生訪談
◆ 陳曉明 李 強
一、 理論的新奇感與挑戰性
李強
(以下簡稱
“李
”):在最近出版的《無法終結的現代性:中國文學的當代境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中,您將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文學創作置于現代性的視野下展開討論。我注意到,現代性理論,其實貫穿著您的當代文學研究。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您就有意識地從現代主義、后現代性的角度去把握先鋒文學。當初您是怎樣接觸到這些西方現代理論的?陳曉明
(以下簡稱
“陳
”):這跟整個1980年代社會思想的現代化渴求有關系。當時社會最大的動力是“實現四個現代化”,所以徐遲先生寫了《現代派與現代化》(《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1期)來論證現代派在中國的合法性。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學習借鑒西方比較新的、先進的東西。文學上要實現現代化,就是“現代派”了。在理論方面,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理論都是以“現代”的名義涌入的。李
:您個人是如何接觸到這些理論的呢?陳
:那時的青年群體,特別是“老三屆”都非常關心新思潮。像薩特、弗洛伊德,包括現象學、結構主義,也陸續傳入。我讀碩士博士時的專業方向是文藝理論。早在1978年,我在福建讀書時,朱祖添老師借給我一本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那時書都是非常難得的,厚厚一本,我就一邊讀一邊抄,做了幾大本筆記,對里面基本理論的掌握還是比較到位的。我們當時文藝理論專業的知識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做基礎,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賀拉斯貫通下來的。讀的主要是西方經典理論。那時讀得較多的是伍蠡甫的《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上下卷的。我托了當時在廈門大學中文系的同學李建敏從廈大圖書館借了寄給我來抄。還有朱光潛的《美學》,也是一邊讀一邊做筆記。李
:無法想象,那時讀理論都是需要把書抄下來的。這些書本身的體系性也比較強,可以當入門基礎吧?陳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我的讀書訓練,一開始都是抄書。那時打下的理論基礎可以說是我一生學術的基礎。所以我和你們討論問題的時候,包括在北大上課,也非常注重基本理論的梳理。我多次開設“現代性理論導讀”的課,就是想通過“現代性”把西方這套理論譜系教給大家。我還開過德里達解構主義的課,也是試圖把理論的譜系介紹給大家。李
:我們今天學習理論常常感到茫然無措,可能就是因為缺乏體系性。陳
:像我們這一輩學文藝理論出身的,談什么問題,都會問“這個概念是從哪里來的?”你認為你是天才,提出的內容有創造性,但我知道你這個問題,可能是柏拉圖到康德、黑格爾等人都談過的,至少內容是相似的。西方學術,非常注重知識譜系的梳理。你的概念和前人的概念有什么差異?沒有根基,沒有對話性,憑空出來的“創造”是沒有意義的。在譜系之中,你的論述可能只比前人多了那么一點點,就已經厲害了。站在巨人肩膀上,你的貢獻不是憑空出來的。而我們在中國古代文論方面,相對欠缺譜系性。多是“微言大義”,有范疇,但很難形成核心概念。在西方,不斷討論經典,把一套譜系都理得非常清楚了。我較早接受了西方這套文藝理論體系,為后來把握現代理論打下了一點基礎。李
:您是當代文學批評家中很早就有理論自覺的,現在也時常教導我們要有理論的視野,要有超越文本和材料的能力。當然,這對現在的我來說仍是難事。我一直認為,學術興趣,乃至與之相關的學術進路的選擇,應該都跟個人性情相關。我比較好奇,您對理論的癡迷,與自身經歷有關嗎?陳
:我可能從小就是這種心性吧,對新的東西很好奇,對自己不理解的事物特別感興趣。我十歲跟父母下放到鄉下,父親是下放干部,有一套理論書,比如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封面都是白皮紅字的那種。說起來可能都覺得是笑話,我對《反杜林論》特別感興趣,經常端著它坐在那里看。我當時搞不清楚《反杜林論》這個書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來,“杜林”是個人名!小時候對我影響比較大的讀物是《參考消息》和《人民日報》(海外版),我經常是從第一版讀到最后一版。那時候崇拜周恩來,只要從報紙上看到周恩來的照片就非常激動。李
:這些經典文獻雖然讀不懂,但讀多了,會不會隱約對那種超越眼前去思考世界和全人類的命運的宏大敘事有一種親近感?或者說,是有了一種富有超越性的意識,一種宏觀的視野?陳
:那時還沒有這種宏觀感受,主要還是看那上面的人,了解國際上發生的事情。當時倡導的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嘛,看“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態勢。《參考消息》、《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登的很多也只是“蘇修批判”、非洲革命。看這些內容,看到外面的世界,甚至有整個世界的事情都盡收眼底的感覺。宏觀視野這一點,也許是受到了那些內容影響后來才慢慢有的。我后來對文藝理論這么感興趣,可能跟《參考消息》這些文章有關系。從那上面,我慢慢體會到馬克思主義的神秘感和崇敬感。像《哥達綱領批判》這些,名字聽起來就非常嚇人了,它是高深莫測的。對這種自己未知的玄奧的東西,我非常感興趣。讀文學作品,就覺得還是比較淺顯,誰都讀得懂啊。我想讀那些別人讀不懂的東西。當然,我也不太可能讀懂,說實話也是一知半解的。后來教書了,才認真去讀。李
:這種對新事物的好奇心,從整體上把握世界的意識,后來都貫穿到了1980年代?陳
:對,1980年代的中期的現代主義,是新奇的,是不在眼前的和可能到來的東西,讓人憧憬。記得當初讀到結構主義、解釋學就非常興奮,它比德國古典哲學更靠近我們,能夠幫我們理解現代和當代。整個80年代上半期,我都在讀理論。我做碩士論文的時候,受英伽登的影響。最后有了自己的領悟,想用結構主義和存在主義去糅合英伽登的“客體”,提出了“情緒力結構”。寫的論文叫《論藝術作品的內在決定性結構——情緒力結構》。答辯還挺費勁的,因為老先生很難理解:文學作品怎么會有內在決定性結構?在當時這是很新的東西,后來李聯明、孫紹振等先生保駕護航,涉險通過。碩士論文大概6萬字,后來寫成了一本書,就是《本文的審美結構》。我讀博士3年時間,寫了3本書:《本文的審美結構》《無邊的挑戰》,還有博士論文《解構的蹤跡》。當然都還是草創性的,但也都不算太差吧。20年之后,那幾本書還有出版社要再版。我做理論是要探討比較新的、有沖擊力和挑戰性的內容。所以我的博士論文又一次面臨困難,我寫的是解構主義。后來導師希望我能夠把解構主義中國化,就加入了一些創作實踐的內容,所以它是綜合性的。李
:當時是怎樣把解構主義和先鋒小說結合起來的呢?陳
:我是1983年在《外國文學報道》雜志中讀到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理論,如獲至寶。我有一點康德、黑格爾美學的底子,憑一點悟性,接受這些相對就比較容易。我在討論先鋒文學,特別是馬原、莫言、蘇童、余華、孫甘露他們的作品時,覺得它們超出了以前文學中的那種完整性和內在統一性。我在1987年左右寫過不少文章,認為這一批作家和“85新潮”不是一回事。我反復強調中國文學在1987年發生了變化,這一批作家的作品走出了“新時期”,我把它們命名為“新時期后期”“后新時期”。這些概念還有一些爭議,但我就是為了把1987年和1985年的現代派做出區別。我應該是最早賦予先鋒派以后現代性特質的研究者。隨著后現代視角的介入,先鋒文學的討論打開了一片新的論域。二、 先鋒文學:是其所是,在其所在
李
:您的《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后現代性》(1993年)是國內最早系統分析先鋒文學的著作,從后現代性的角度切入先鋒文學,既領時代之先,又是有效而精當的。在多年之后的今天回頭去看,您如何評價先鋒文學?陳
:從現代派到后現代主義,當代文學展開了超越性的創新。此前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實際上是與官方主流意識形態保持一致的。它們是在反“文革”的人道主義,“實現四個現代化”等體系底下,是需要現實感的,有現實依托的。朦朧詩最初和思想解放運動有契合的地方,但很快就有差異了。那時有所謂的“意識流”,但也是很有限的。當時在創作上介入現代派比較多的是高行健,據說那時高行建的小說總是很難發表,人家說他不會寫小說。他一氣之下就寫了《現代小說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王蒙、馮驥才、劉心武他們讀了之后很興奮,所以有了“現代派的四只小風箏”的說法。整個現代派的雛形是“85新潮”,但中國的現代主義準備并不充分。但先鋒派的出現,他們的話語中沒有多少現實的緣由,它們是“沒有歷史”的。當然,他們的創作中也涉及歷史,但都被轉化成了一套新的話語體系了。他們的視野更大,而且展開了更具有形而上意義的思考。蘇童的《1934年的逃亡》,談的是逃亡的問題,是鄉村對城市逃離。《罌粟之家》確實寫了一段歷史,但它的歷史跟性和生命的頹敗聯系在一起,寫出了生命的困境。余華的《四月三日事件》,里面有現實,但它是肉體與自我的問題。孫甘露的作品更離奇,《信使之函》《請女人猜謎》完全是在形而上的沖動當中展開的。這些作品是中國文學第一次能夠跟現實剝離開,在現實之上或之外去討論一些問題,這對中國文學的意義非常大。盡管很多人說先鋒文學缺乏現實感,但他們不理解這種現實感,先鋒文學寫的是超越性的現實,有那種更加強大的、敢于勝過現實的現實感。李
:但是不是也可以說,先鋒文學表現的其實是現實的情緒,或者是把某些現實的想法投射到小說中了?陳
:還是高于現實的,可以說是“來源于現實又高于現實”。李
:《無邊的挑戰》“導言”結尾的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后現代’并不像利奧塔德所構想的那樣——是一個充斥著‘稗史’的時代,也并不是一個僅有著并列排法、反論和悖理敘述的時代。后現代時代也有著某種歷史的真實感,我的這些敘述意在打開某個精神地形圖,某個群落的集體無意識,某代人的內心生活。”從這段話里,我意識到,你所說的“某個精神地形圖”“某個群落”“某代人”,其實就是您自己這代人。您和先鋒小說家們是同代人,也有深入交流,您的先鋒文學研究可以說是一種“現狀研究”。在這種研究中,您是如何保持“當代性”的?您是從何種意義上把握自己的“同時代人”?阿甘本所說的,“同時代性也就是一種與自己時代的奇異聯系,同時代性既附著于時代,同時又與時代保持距離。更確切地說,同時代是通過脫節或時代錯誤而附著于時代的那種聯系”。您如何處理“附著于時代同時又與時代保持距離”的緊張關系?比如說,您當時寫他們作品的后現代特征,那些超越于時代的特征。但作為“同時代人”,您對于先鋒派這種超越性的局限有沒有明確意識?陳
:阿甘本說的“同代人”,主要是和大的時代的疏離感。這種疏離感當然并不是某個絕對的個體所有的,可能極少數個體能夠體會到。阿甘本是有著西方馬克思主義背景的理論家,他的理論包含了批判哲學的態度,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異質性精神。對于當時的我來說,先鋒派在美學理念上與我是有相通性的,我覺得有這幾個先鋒派已經很稀少,很難得了。對于新的有挑戰性和超越性的東西,我不太愿意去談到其局限性。按理說,局限是永遠存在的。看我們以什么尺度去把握它了。只要我們拿時間尺度,拿某種觀念,比如說完整性的觀念去看,事物永遠都是有局限的。這種局限性,就在于個體形成自我的時候,永遠不可能企及“完滿狀態”。所以這么強求它,就變得沒有什么意義了。老子說的“大成若缺”,其實沒有完整的“大成”,沒有所謂的完整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企圖去表述的所有東西都有其局限性,都不完整。當然有一些是明顯的、致命的局限,這當然可以指出來。但是我們在認識事物的時候,看到它能完成到如此地步,就已經非常好了。在某個時間點上,有些事物有它的意義。李
:需要在歷史情境中,歷史化地把握它。但是這個時間點的界限或者說限度在哪里?陳
:“歷史化”是我們建構并賦予其意義。如果我們在純粹時間的意義上來說,它就是其所是,在其所在。很多作品都具有相對性,例如回頭去看《白鹿原》《廢都》,當時的很多問題它們也沒觸及,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們都可以再回去討論。但也恰恰因為它的不完整性、局限性,才成就了自己。它們在歷史和現實方面的極端表達,把1990年代初的某種情緒、觀念表現了出來。如果沒有這些,它們可能什么都不是。恰恰是這些,讓其是其所是,在其所在。我們對任何事物的理解都是這樣,否則都會沒有意義,今天大家不會去討論它。對嗎?李
:對,如果他們不是把性和歷史寫得極端,今天可能沒有多少人會去討論其意義。陳
:30年過去了。我在1980年代后期把先鋒派的那些作品的特征命名為“后現代性”。吳亮說“向先鋒派致敬”,如果他們當年不是在語詞、敘述方面那么絕對、激進,我們今天不會討論的,它跟其他所有的作品一樣沒有意義。三、 “現代性”的討論,是后現代視角的產物
李
:您在《無法終結的現代性:中國文學的當代境遇》開篇就指出了您的思考起點:1990年代之后,“盡管有一部分作家依然把后現代的歷史觀及美學觀念深藏于其內,但整體上看,卻是現代性回潮,作家習慣于在宏大的歷史編年體制中敘事,在藝術表現方法上,也習慣于用有時間長度和持續性的命運邏輯來結構故事……”也就是說,雖然經歷過先鋒派的洗禮,但中國文學仍然呈現了“無法終結”的現代性的特征,這是1990年代文學再次發生轉變的產物?陳
:對,這個問題非常關鍵。在1990年代初,我們的歷史發生了巨大的變革,現代派、現代主義這套東西難以為繼了。在文學上出現了現實主義的回潮,具體表現,一方面是新寫實小說,另一方面是“陜軍東征”。當時在理論上弄出“新寫實”的說法,在當時看是后撤,但這種后撤是權宜之計。它們也因此使中國文學多樣化,也更具有開放性。《白鹿原》《廢都》重新展開了現實主義的對歷史和現實的關注。本來先鋒派完成了對現代派的超越和升華,通過形而上的東西來反過來完成對現實的超越。我們也看到,這本身也使得現實主義更加強大。現實主義確實可以找到新的表現方式。《白鹿原》《廢都》也好,還有王朔的作品,它們和之前的先鋒小說相比,雖說故事和人物又占據重要位置了,語言也變得更加明晰,更有親和力了,但是它們本身包含了更加豐富的內涵,和傳統的現實主義是不一樣的。只不過,我們當時還很難用“現代性”的概念來捕捉它們。李
:您在《現代性有什么錯:從杰姆遜的現代性言說談起》(《長城》2003年第2期)、《現代性:后現代的殘羹還是補藥?》(《社會科學》2004 年第1期)等文章中都指出,關于現代性的論述其實是一個后現代的問題。關于現代性的討論,是從“現代性終結”的理論預設開始的。在最近出版的《無法終結的現代性:中國文學的當代境遇》中,您延續了這一觀點。您一開始就有意識地強調要從后現代的角度去把握現代性問題,這為您觀察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視角。這場關于現代性的討論源自西方,您當時是怎樣將其與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變革聯系起來的?陳
:在1990年代,西方從學理上討論了現代性的問題,主要就包含了對現代性的反思。關于現代性的問題,本身就是后現代視角的發現,現代性的討論基本上是在反思現代性自身。我們過去認為后現代是對現代性的拋棄,是對現代性整個話語的超越,實際上并不是這么簡單。后現代本身是在對現代性的反思而不是順承中,才有其超越意義的。先鋒派意義上的后現代,確實是更加偏向于超越現代性的,在美術領域也是這樣。但是在社會學上,在其他的理論領域,后現代對現代性的批判,是將其包含在內部的。也只有把現代性包含在后現代里面進行反思,才有其意義。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當出現現代性話語的時候,其實都是后現代的表達。可以說,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只是同一種話語的兩種表述而已。這樣一來,后現代性就不再只是在理論方面的,而是在歷史之中的。因為只要進入歷史維度,后現代就會變成現代性。所以后現代性的論述,它主導的內容就必然會是現代性。李
:也就是說,要進入歷史之中討論后現代性,就需要把它建構成體系、脈絡。要展示出具體語境,才能夠討論后現代性,這樣它就只能借助現代性的話題才能表述自身。陳
:實際上,對歷史的想象和敘述,如果它本身是完整的,充分的,不需要反思的,你的視野和它是唯一性的重合,你就不需要用“現代性”這樣的概念了。一旦用現代性去表述,就表明這種歷史的表達是不完整的,不充分的。因為它是需要被反思的,或者說它是已經被反思的,它的歷史本身會包含著裂隙、分歧或者差異。比如,我們說《白鹿原》是現實主義作品,但是我們也會看到它里面包含著對歷史的反思,是現代性問題的體現,反思了歷史本身的不充足、破裂。李
:這讓我想起了《白鹿原》里朱先生所說的“白鹿原的歷史是翻鏊子”,這段歷史是翻來翻去的歷史,包含著重復、顛倒,是破碎的,偶然的。這對那種線性的進步史觀展開了有力質疑。陳
:這種歷史觀的變化背后,是現實主義美學原則的轉變。當歷史被視作單一的線性的時間觀念而被完全肯定的時候,就誕生了經典的現實主義,或者說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當歷史不再被作為線性的和合目的性的時間的產物時,它是在反思現代性的,是一種全新的現實主義觀念。這種現代性表述本身包含了后現代對整個現代性的歷史進程的思索,這種思索包含了內在的悲劇,有著強大的歷史的創傷。這種歷史的創傷,在過去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說是必需的,是偉大的。因為歷史只管目的,目的是向著人類進步未來的。而那些個人的、破碎的傷痕都是可以碾壓過去的。李
:一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敘述里,經常把《白鹿原》歸置到“新歷史小說”中。但我覺得“新歷史小說”這個命名本身,是傳統現實主義試圖將對歷史的反思回收到之前的歷史小說脈絡中。但這也只是一個權宜之計。今天看來,“新歷史”里面包含的對現代性的反思,是1980年代先鋒派的探索的結果之一。“新歷史”的這種“新”,其實是轉化了1980年代后期的先鋒派作家們對于歷史的討論,是把它們內化在了現實主義之中。陳
:對,處理得比較巧妙。你看《白鹿原》中重要的人物,鹿兆鵬是沒下落的,白孝文的命運也是不清楚的。作者并沒有給他們結局。結尾在鹿子霖那里,只是呼應前面“風水寶地”的意義。里面的主要人物是沒有真正下文的。無法終結,言外之意就是,一切你們都可以自己去想象。李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白鹿原》也是寓言,寫的是“無法終結的當代史”啊。陳
:當然,這些都是1990年代以后的變化。我說“無法終結的現代性”,是因為先鋒派在中國的探索很短暫,那樣的藝術探求,確實也難以為繼。更多的作家,追求的還是現實感、完整性和內在的力量感。我所理解的文學藝術的高妙之處,在于能呈現各種細微差異。在細微差異中,歷史、現實和生命的三元關系能夠讓我們看到這個世界上的新質。我當年確實是在《鮮血梅花》《罌粟之家》《迷舟》這些作品中看到了新質。李
:要感悟到作品中的新質,需要對世界有新的看法才行,當時需要更新自我經驗吧?今天回頭去看這些表達經驗,可能有些陌生了。陳
:現在去理解這些經驗可能存在困難,現實經驗、閱讀經驗都會有所限制,造成了某種理解上的難度。當然,先鋒文學本身也確實很難成為大眾化的文學。四、“新世紀文學”與當代中國文學的“晚郁風格”
李
:您的《無法終結的現代性:中國文學的當代境遇》中所討論的多是21世紀十多年來的作品,這部書也可以說是您基于現代性視角所作的“新世紀文學概觀”。您如何看待“新世紀文學”這個概念?在現代性視域下,19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這種“世紀轉折”是否有其獨特的理論意義?陳
:關于“新世紀文學”,《文藝爭鳴》的前主編張未民先生發起過討論。這個概念是在強調時間點的意義,“新世紀”,還有“世紀末”,其實都是基督教的概念(后來也變成了革命的概念),有末世論和彌賽亞降臨的意義。新世紀就是新的世界的降臨。但對于我們來說,新世紀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意味著時間的節點。我們在2000年的時候,確實有對未來的憧憬,但不是很強烈。變革現實的可能性,已經變成了事務主義、程序主義。重建的努力也變得非常困難。我們知道歷史不會有太大的變化。1990年代,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因為當時世界歷史發生過一些大的變化,“蘇東劇變”等等。21世紀的到來,并沒有多么劇烈的變革,但還是在發生一些深刻變化。新世紀之后,中國經濟有了更快的發展。2001年中國加入WTO,全球化以及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加速,與此同時,三農問題更加凸顯。在文學上,知識分子有了更強的現實關照,在創作中的現實感加強,對現實的反思性也被凸顯出來。新世紀的文學中反倒出現了書寫苦難的趨勢,底層的苦難敘事,它其實是繼承了左翼傳統。左翼文學傳統,是革命的傳統。這種革命就在于它是要改變世界的,真正地呼喚新的世界的到來。李
:這個意義上,左翼書寫反倒是呼喚著新世紀的到來。陳
:對,新世紀出現了大量底層敘事和苦難敘事,階級敘述重新被注入新世紀文學敘事中,但革命的主體卻很難建立起來。小說表現的對象只是受苦受難的底層,本身不具有重新建構歷史的沖動。底層沒有把自己變成新的歷史主體,而只是被悲憫和被同情的對象,歷史本身不可能迎來革命性的變化。我當時寫過一些文章,像《“人民性”與美學的脫身術——對當前小說藝術傾向的分析》(《文學評論》2005年第2期)。我認為,寫苦難和底層,最后獲得了文學敘述上的力量感。追求敘述上的力量感,是中國當代文學追求現代性美學的方式或者說基本態度。在1980年代后期,先鋒派文學不太需要強大的力量感。當然余華似乎是例外,他的《一九八六年》里面動用了暴力,但這些暴力是“小暴力”,不醒目刺激,不是歷史的暴力。還有《四月三日事件》,是在討論暴力的偶然性,以及暴力本身的破碎。但是新世紀的這些作品,它表現的苦難和暴力就很直接。比較典型的是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楊映川的《不能掉頭》、熊正良的《我們卑微的靈魂》、艾偉的《愛人同志》等,都書寫了底層的苦難、暴力,也都是當時備受好評的創作。我當時也探討過它們,認為那些作品里的苦難情緒被緊張地推進,越來越有線性的力量感。在對敘事高潮的期待之中,隱含了悲劇因素。這種線性力量的追求是現代性的美學,現代性的美學是有確定性的。而后現代美學,例如先鋒派,是在似是而非的狀態中,有意地書寫破碎和凌亂,展現不確定性和偶然性。李
:在一般人的論述里,“新世紀文學”是一種多元格局,我們沒辦法用籠統的時間概念去囊括它。您將其定義為“現代性美學”,它就又可以被整合進時間框架之中了,可以和1990年代甚至1980年代的歷史發生聯系。這使我想起了,在您以現代性為敘述框架的《中國當代文學主潮》中,“新世紀文學”部分,也是有某種連續貫穿性的。關于所謂現實主義的回潮,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回光返照,它可能是現代性最后的光芒?隨著“當代”的時間節點在無限下延,會有越來越多現代性甚至后現代性的理論都無法整合的異質性因素進來。現實主義又會發生變形,或者被深刻顛覆。如果我們要對中國當代文學史再做總體性的敘述建構,您所嘗試的以現代性為基礎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框架,有沒有可能也是最后的框架?陳
:嚴格地說,沒有任何時代是不能夠被概括的,從理論上都是可以提出設想去概括它們的。當然也沒有任何時代是可以被概括的,因為歷史本身是無限的。但不管是歷史學,還是我們的文學史,都需要去概括時代。新世紀也是這樣,但是每個人理解的新世紀又不太一樣。今天人們的認識更加多樣,不像1980年代那么容易產生共識。那時的共識可能是歷史實踐本身給予的,也是因為共同體本身的思想和知識譜系非常接近。在新世紀,我們會看到,分歧是到處都有的。就像剛才,我認為“新世紀文學”是現代性重構,而你稱之為現代性的“回光返照”。我們存在分歧,但可能說的都對。不過,我們可以確認的很簡單的事實是,新世紀以來文學中的那種個人的探索變少了,寫作者們不再“做無謂的犧牲”。文學書寫有著對現實的適應性。李
:是多元化探索減少,逐漸適應了市場化的現實嗎?陳
:對,文學已經對這種語境有所適應了,創作中已經隱含了讀者消費的預設。198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都有理想的文學讀者,所以它不斷地去探索、超越。1990年代之后,市場經濟開始形成,理想讀者是逐漸減少的。在這個意義上,新世紀的文學本身也面臨著文學探索方面的“終結”,例如文學觀念的變革,文學的那種超越性,實際上是慢慢被放棄了。這種放棄,直接原因可能是消費社會的形成,作家的生存本身也成為現實問題。可以說新世紀的文學是很現實的文學,是有現實感的文學,這導致文學的超越性沖動不能持續。消費社會形成了某種壓力,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相敵對”。當然,資本主義發展的漫長過程中,也有很多個人化、探索性的內容出現,也有很多優秀作品。文學藝術對社會有適應性。當然這在今天就更加復雜了,“究竟有沒有產生優秀的作品”“產生的作品是否和這個時代相稱”等,這些問題都只能留給歷史去討論了。我們今天對新世紀要做出定義確實是很困難的,它還是時間節點,但它本身在文學上、思想上缺乏強大的內在性,本身也只是一種境況。李
:您提出過“新世紀漢語文學的‘晚郁時期’”這一說法,“‘晚郁時期’表達的是歷史沉郁累積的那種能量與一大批作家‘人過中年’的創作態度的重合”。在《鄉土中國、現代主義與世界性》(《無法終結的現代性:中國文學的當代境遇》第十五章)一文中,您再次提及“今天的文學進入了晚期風格時代,一方面是青春寫作的低齡化和早熟,另一方面是傳統文學創作的高齡化和晚期再生”。這種“中年”“晚年”的代際差異所演繹出來的理論自有其穿透力,也能描述當代文學的來龍去脈。另外,我也注意到您所論述的“晚郁一代”,多是劉震云、閻連科、賈平凹等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即50后作家。我還注意到在《無法終結的現代性:中國文學的當代境遇》第八章討論先鋒文學的時候,您有一個觀點特別耐人尋味,說“如今最保守的創作經驗由50代作家堅守,最激進的創作經驗也是由50代作家得出的”,“先鋒不分先后,先鋒也不分年齡。但其老齡化的現狀,確實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我們以此來關照當代中國文學,認為50后這一代人的創作歷程就是當代文學過去三十年所走過的歷程,他們今天的成就代表著當代中國文學的最高成就,這可以理解。但“晚期”是否也會遮蔽了當代文學場域的復雜性?比如,您如何看待70后、80后作家的創作?陳
:你的感覺是對的。我自己也是50后,所以對50后這批作家關注更多,也更理解他們。我的“晚郁”概念也是從阿多諾和賽義德的“晚期風格”那里來的。我在《中國當代文學主潮》里就曾探討歐陽江河提的“中年特征”概念。在1990年代初,他們也就三四十歲,其實還很年輕,但他們就有某種“人到中年”的感覺。因為歷史的變故比較大,他們有了未老先衰的心態。這一點也讓我去思考20世紀中國文學的寫作狀態。早期是“青春寫作”,是少年中國的氣質。像郭沫若、郁達夫、曹禺的創作,也都是二三十歲。后來他們到了抗戰期間,都是“救亡寫作”。1950年代以后,思想改造,有人被打成“右派”。等到歸來時,他們都是老年人了。1980年代是知青,當然又是年輕人。到了先鋒派,又是年輕人。他們寫作年齡確實和中國文學的變革有一定關聯。其實很長時間一直沒有“中年作家”。1990年代以后,才“積累”了上點歲數的持續寫作的作家。例如1993年時,莫言38歲,寫了《酒國》;賈平凹40歲,出版了《廢都》;陳忠實50歲,寫出了《白鹿原》。直到新世紀,這些作家才開始進入中老年,在五六十歲時寫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還有一件事觸發了我去想這個問題。我的朋友許金龍先生,他是大江健三郎作品的中文譯者。他曾跟我說,大江健三郎先生給他寫過信,說中國文學還是非常有希望的,因為中國有這么一批五六十歲的作家,隊伍這么整齊,經驗也比較豐富,在其他國家都是少有的。我覺得這倒真是一種獨特現象。這一批五六十歲的作家,已經非常成熟,他們自己也覺得老之將至。賈平凹就經常會在小說后記中感慨自己老了。從“晚期”這個角度看,他們創作會顯示出怎樣的風格?那時我讀到了賽義德的《論晚期風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之前也看到阿多諾對貝多芬音樂中的“晚期風格”的論述。把這些問題放在一起,就發現新世紀文學確實有不一樣的地方。這些作家的生命經驗,對文學的感悟,都發生了新的變化。中國新文學已經有了100年的歷史,經歷了這么龐大復雜的變動,一定會有許多寶貴的經驗沉淀下來,對文學造成一定影響。作家們有的是親歷者,有的是在體驗、消化著積累下來的文學經驗。我們要在百年中國文學的背景下來看這批作家,我把他們的創作用“晚郁”來命名。
李
:我從您關于“晚郁”的文章里,讀出了一點悲壯感。陳
:這其實是當代中國文學的境遇,讀圖時代的到來,讓一些人開始討論“文學的終結”。百年中國文學還是很年輕的,但它怎么就老了,到了終結的時候?當影視及新媒體出現,和傳統文學連在一起的時候,網絡文學又宣布“傳統文學的死亡”。但是新世紀的文學確實是多元格局,不只是70后、80后,更年輕的更多五花八門的東西出現了。新媒介的生產傳播方式又在改變我們的百年中國文學。不是說新的70后、80后也好,網絡文學也好,和我們的千年人員就沒有關系,而是說他們確實這樣感受的新的經驗要大得多,要多得多。傳統文學在歷史底下的書寫,總是會考慮傳統的問題,比如余華、莫言他們或多或少地會談到魯迅的影響。他們的寫作都是在新文學傳統之中的。但是在后來那些作家那里,這種新文學傳統不是很多了。它們似乎不是在一個脈絡體系之中。“新世紀文學”確實有著多樣的內容。我關注的依然是傳統文學、經典文學的脈絡,當然它不可能終結。我們今天的大中小學的教育體系中的文學教育,還是在百年中國文學,在千年中國文學的傳統之中展開的,留下的還是這些經典作品,還是在漢語言優美的作品中傳承、展開的。五、今天,我們如何做當代文學研究
李
:我剛剛問“同時代人”“晚期風格”的問題,其實也是出于自己的困惑。很羨慕您當時遇到了這樣一批心意相通的先鋒作家,他們也寫出了水準較高的作品。在一定的時候,您還能深切體會到同齡人的“晚期風格”。但我們現在的批評和研究,很多已經變成學術生產,似乎都是職業行為了。比如,別人找我們寫評論文章,我們經常面臨兩個問題:一是這文章是我自己不喜歡的,但是我還要去講它的“好”。最后就變成了一種知識的“復制”,把我知道的東西跟它發生關聯,削足適履,賦予某種“意義”而已。另一種情形是,我可能遇到了自己很喜歡的作品,但會有點懷疑它可能只是個人口味,我所賦予它的“意義”是不是有什么局限。陳
:你提的問題包含了好幾個層次。我遇見這批作家的時候,是文學轉型的時期,也是文學展開自我挑戰的時期。傳統現實主義發展到一定的地步了,西方文學特別是現代主義涌進來了,促使中國文學經驗做出快速激烈的反應。我也是在現代主義、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這樣的理論建構下尋找自己的話語。我確實是有表達的沖動,企圖跨過一些壁壘。我們那時其實也很困難,我們的話語表達也是受限制的。不管是政治上的還是學術方面的,都有壁壘。我那時也是30歲出頭,跟你們歲數差不多。有權威話語在前面壓制著我們,但他們在話語的構造上跟我們不同,所以他們攔不住我們。就像踢足球,套路都不一樣,他是攔不住你的。對你們來說,現在面臨著新的難題。范式的轉換,理論的轉型,從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就完成了。你們要在同一套語體系中超出上一輩,還是很難的,不像我們當時,會有那么大的超越性。當然,我相信年輕人總是能夠勝出的。李
:就像您說的,當時您寫的碩士學位論文,導師們可能看不懂,畢業答辯是“涉險過關”。但今天情形不同,我們不管寫什么,老師們都能看懂,而且還能提出高明的指導意見。我們多數人目前還是在上一代的框架里。陳
:今天,文學創作本身的挑戰性、理論的挑戰性,基本上都喪失了。這是我們共同面臨的問題。你剛才說的批評的兩大問題,同樣也是我最頭痛的。有時看不到有藝術沖動的東西,但還是要寫文章。有些是任務,有些是人情。中國是人情社會,花在應對事務上的時間很多。另一方面,當下的知識和信息量在劇增,在短期內,學術體系中的大的轉換很難完成。這是大家共同面對的枯竭狀態,理論的枯竭,想象的枯竭。即便如此,還是可以在有限的情境下發現新問題,探討問題的新可能。我們應該懷著美好的愿景,這個時代的當代文學研究,還是能夠有所作為的。李
:好的,還有許多問題需向您請教,可惜時間關系,不能展開了。感謝您在百忙之中為我解惑!
注釋
:①陳曉明:《無邊的挑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頁。
②吉奧喬·阿甘本著,王立秋譯:《何為同時代?》,《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
③陳曉明:《無法終結的現代性:中國文學的當代境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頁。
④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頁。
⑤陳曉明:《無法終結的現代性:中國文學的當代境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75頁。
⑥陳曉明:《無法終結的現代性:中國文學的當代境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502頁。
⑦陳曉明:《無法終結的現代性:中國文學的當代境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