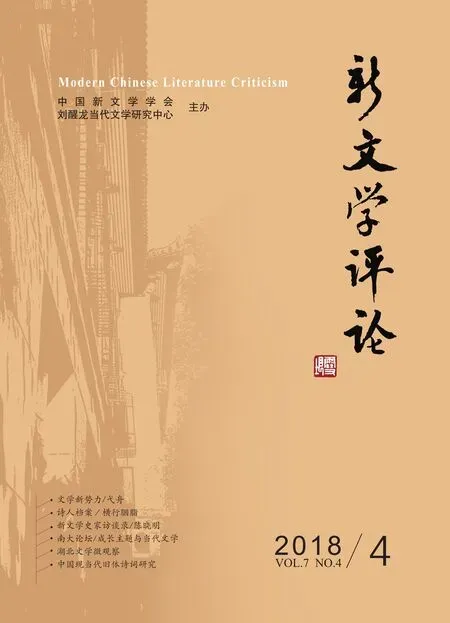主持人語
◆ 張光芒
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在1918年5月號《新青年》上,魯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小說《狂人日記》問世。小說的最后一段只有四個字,“救救孩子”。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作為新文學的奠基之作,這個結尾似乎也預示了此后百年文學最核心的主題,應該正是如何救救孩子的問題。可是,在文學史的實際進程中,以鄉土敘事、都市書寫、知識分子寫作等為主的題材領域,以革命、斗爭、戰爭、婚戀等為主的文學話語,更多地占據了審美創造的書寫空間。人們更為迫切地想探索和解決的是“成人世界”的問題。相對而言,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人格啟蒙與自我啟蒙、教育與成長的互動關系等,這些涉及“救救孩子”的深刻命題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挖掘。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思想解放與市場經濟的發展,伴隨著青少年問題、道德滑坡問題、信仰失落問題等的大面積出現,教育與成長問題的重要性、迫切性,越來越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當代文學也以其獨特的方式介入這一題域,以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層面作出了回應與思考。該組論文便是對當代文學中成長主題的一次集中討論和檢視。
王振的論文以“權威的弱化”為題考察20世紀80年代小說教育倫理關系的嬗變。在她看來,那個時期帶有教育內涵和成長意蘊的小說,在教育倫理關系的隱喻和表達上呈現了較為復雜的態勢:一方面,80年代初以“父”為代表的傳統倫理秩序和教育權威雖然具有一種弱化的趨勢,但囿于公共語境的存在,依然凸顯了合法性的地位,其存在無疑為重建“子”一代錯亂的精神世界以及構建現代化的想象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則是80年代中后期隨著社會文化進一步轉型,公共語境削弱,以“父”為代表的傳統倫理秩序和教育權威得到了較為明顯的質疑與顛覆,更多小說表現出了權威教育的無效性。而小說中兩種意義上叛逆孩子形象的出現,則隱含著對新型的教育倫理關系的想象與投射。同時,探討一種和諧的教育倫理關系的建構與生成,顯示出小說對現實的深度思考和回應。
田青艷的論文則是對新世紀大學敘事長篇小說的一次集中反思。她認為這類創作以高校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為主,輔以為數不多的校園青春小說。兩者在展現在校學生的畸形成長狀態時,都存在模式化、臉譜化的問題,更由于以大篇幅離奇的情感經歷敘述為主調而偏離了敘述目的,這使得學生成長失敗的結局雖合理,卻缺乏引人進一步反思的余地。作家們所構造的在校學生的畸形成長,往往雖有社會現實的影子,卻因為程式化、夸張化的敘述,已經與現實大學生的成長經歷相去甚遠,削弱了現實批判的力度。論文將這些現象概括為“架空的畸形成長”,可謂是有感而發,啟人深思。
新世紀前后,中國大陸曾出現一批某種意義上可視為同齡人學習榜樣的模范少年,王蕤即其中之一。她從中學開始發表作品,關注少年人成長過程中的精神創傷,探索自我的本質。出國留學后,王蕤著力于展現海外華人的生存處境,對東西方文化進行雙重審視,在融合、交錯的視野下追尋更具超越性的新價值觀。回國后的王蕤有感于90年代以來中國時代風氣的劇烈變換,以海歸群體的生活展現了中國社會的光怪陸離。近些年,王蕤幾乎不再進行文學創作,而投身于各種生活指南的編寫,其中反復重現的是她對自身求學、生活經歷的敘述。“王蕤”本身已成為一個文化標識,乃至被打造為“成功學”的典型案例。鄧瑗的論文從青春書寫、文化差異與自敘傳相結合的角度,將王蕤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加以考察。作者的結論十分耐人尋味:王蕤的淡出文壇某種意義上代表了當年模范少年的共同命運,在青春寫作與自身經歷被消費完后,他們也不過成為紛繁社會中的普通一員。
鄭利萍的論文以“從詩性理想到尋常生活”為題,著重考察了王安憶《啟蒙時代》中主人公的成長之路。在她看來,小說敘事呈現了個體的社會化歷程,探索了個體的社會性和歷史性內涵,個體在現實中所必須面對的生存困惑與職業困惑,在社會意義上的主體建構、社會認同和自我實現。
如果說上面四篇文章以客觀理性的筆觸從不同的方面討論了當代文學中成長敘事的不同路向和探索的得失,那么下面三篇則集中于剖析“成長的困境”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對于這種困境的不同審美表現。張云舒的論文呈現的是“成長的三重困境”。從《雨天的棉花糖》到《那個夏季 那個秋天》,畢飛宇一直在從日常經驗層面書寫成長主體的生存困境。無論是紅豆還是耿東亮,都陷入來自身份、愛情與理想的三重困境。身份的困境源自性別的誤認,愛情的困境體現為兩性關系的不對等以及難以結合的遺憾,理想的困境表面上來自理想與現實的沖突,實際上則與個人意志薄弱相關。三重困境反映的都是“自我”與“世界”的沖突。當“自我”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時,成長也就走向了能指的反面。它不再是積極的、美好的,而是成為一場又一場困境,成為“自我”與“世界”的較量。
唐越的論文將蘇童《舒家兄弟》中主人公的成長書寫描述為“反成長的成長悲劇”,這種成長悲劇具有多重成因,“文革”社會中人性缺失的生存群體,成長家庭中父親形象的墮落和顛覆,成長主體自身欲望的淪陷,都推動了主人公的成長走向支離破碎。這種反成長性質的成長悲劇在蘇童的創作中具有較普遍的意義,創作背后是蘇童對“文革”時代下成長的反思和對成長問題的哲理性思考,解構了宏大敘事中的“成長”內涵,具有反叛性和革命性,可以說開拓了成長書寫新的話語體系。
對成長的關注也是黃蓓佳創作一貫的聚焦點。王桃桃的論文認為,不同于兒童文學世界的單純明朗,黃蓓佳的成人小說表現出了成長問題的復雜性,尤其是成長過程中“自我的迷失”。長篇小說《所有的》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主人公艾早的成長過程不是逐漸確立自我的過程,而是自我由有到無的逆過程。自我與家庭、社會的博弈,使她陷入孤獨境地,孤獨的沉重引力加速著自我的迷失,終于形成其依附性人格。最后她連死亡都需要通過他人得以實現,其成長終于淪為徹底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