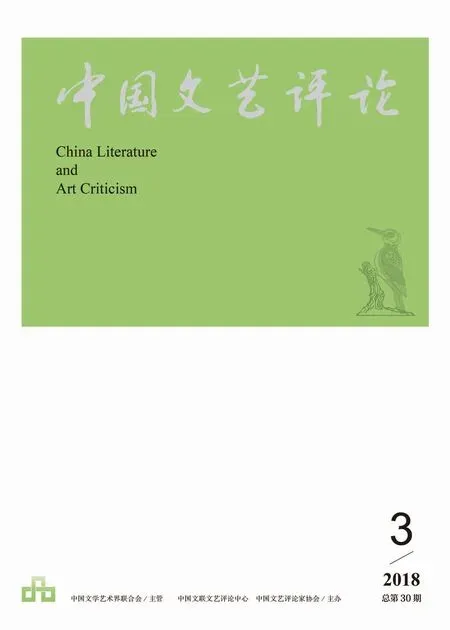論不同文化視閾中同名電影的人物塑造
——以小說《嫌疑人X的獻身》及中日韓同名電影為例
徐藝嘉 徐兆壽
18世紀以來,電影作為“光影魔術新世界”帶給全球一次新興的藝術革命。直到19世紀末,電影才相繼傳入日本、韓國和中國。因為日本和韓國曾受到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使得中日韓三國電影都具有中國古代傳統倫理道德的一些審美情趣,但隨著三個國家的現代化轉型,其表現出來的文化差異也越來越明顯,這可以從電影中看得出來。東野圭吾的小說《嫌疑人X的獻身》在發行后風靡亞洲,受到亞洲各國懸疑偵探小說讀者的追捧。2006年,日本導演西谷弘第一個將小說改編,搬上銀幕。2012年,韓國導演方恩珍也改編拍攝了同名電影。中國導演蘇有朋于2016年也改編拍攝同名電影,并于2017年正式上映。本文以同一文本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為藍本,著力探討中日韓三國不同文化背景對人物塑造產生的影響。
一、人物塑造的各自特點
人物塑造對于一部電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導演以及受眾的不同,根據同一部小說改編的電影往往在人物塑造方面產生很大差異。在東野圭吾的小說中,人物呈現復雜并且多元的特點,主題敘事背后所展現的不單單是法理與情感黑白分明的論述,更是對復雜人性的深入探討。
1. 中版電影人物形象之對立與調和
中國早期電影受戲劇和戲曲的影響很大,上世紀30年代以前電影一直被稱之為“影戲”。鄭正秋、張石川等第一代電影人對人物形象塑造主要是吸取了戲曲人物善惡分明、非黑即白的教化特點。隨后在政治為主導的歷史時期,“對立化”的人物特征在主旋律電影中得到充分的發揮。隨后逐漸轉為中國式電影人物的隱性特點。在蘇有朋導演的《嫌疑人X的獻身》中,王凱飾演的教授唐川在影片開始就表現出高大正義的形象。在警法學院的多功能階梯教室里,導演用仰角鏡頭拍攝臺上穿著筆直西服且帥氣干練的教授唐川為法警講授作案工具的情景,直接塑造了唐川高大正氣的形象,一開始就讓觀眾陷入人物定式符號中。而在日版電影中,開片同樣是對其人物身份進行介紹。教授湯川學身著干凈的白大褂,態度溫和,結合新聞案件在戶外實驗室講授實驗工具。其后畫面才是在學校階梯教室給學生上課的場景,臺下坐的幾乎都是“癡迷”于他的女學生。導演擅于用邊角關系展現湯川學的性格和魅力,鏡頭簡潔但有力地展現出人物的多面性。
在中版影片之中,蘇有朋將唐川“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形象發揮得淋漓盡致。無論唐川在辦案還是與石泓的交往過程中,其正面的光環始終存在。導演在拍攝他們童年友誼時,少年唐川表現出的驕傲正氣與少年石泓的自閉寡言也形成鮮明的對比,不僅沒有體現出他們的友誼精神層面的對等性,也無實質意義的友情基礎。中國電影中,當人物形象對立時,必有一個目的為其歸宿,而最后的結果,必有一種觀念的勝利。觀眾對于影片所得到的教訓,多由影片所表達的善惡而定。這是中國電影中的隱形特質。
除了人物形象對立化,蘇有朋在塑造人物形象上還吸取了韓國電影一向擅于處理情感的特點,同時明顯在情感線路的鋪墊與升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原著中石泓對陳靖的愛本應是純如漿、淡如水,著重表現石泓個人的作案心理。導演將陳靖母女敲門送愛心卡片和陳靖平時溫柔的笑容作為打動石泓內心的籌碼,激起石泓心底最柔軟的部分,使人物情感在溫情化影調的處理下,弱化了犯罪行為的可恨度,給犯罪披上溫情的外衣。然而導演不想過于煽情,一方面在電影中加重情感表達,另一方面渲染正反兩方的智力的博弈,不想完全將煽情催淚作為主線,仍想保留原著中的悲劇感。在最后案件真相大白時,導演一邊拍攝女主角跪在石泓面前撕心裂肺地痛哭請求原諒,一面抓拍教授唐川面對即將失去一位高智商朋友時悵然若失的表情。所有人都在法理與情感中陷入糾結與深思,這是一個復雜的心理展現,也是對人性深度思考的過程。
2. 韓版電影人物形象之溫情與純度
在東野圭吾小說中,女主角靖子原本是酒吧女郎,因撫養女兒,改業“從良”,經營一家便當店來維持生計。這個女性形象是復雜多面的,既有善良堅強的母親身份,又有不愿提及的過往。作為母親,與女兒相依為命,聯手殺人的舉動,觀眾在道德層面能理解但并不十分同情。而韓國電影明顯對女主角的身份進行了改動。原著中的母女身份,變成小姨和外甥女的親戚關系。這種身份的變動,弱化了母女之間的直系血緣關系,使得東野圭吾筆下女主“惡女”的形象變得更為善良、純情,賦予小姨這個角色更多的責任和擔當,引發觀眾同情。
韓版影片伊始就為小姨這個女性角色做足情感鋪墊。其中一個情節是外甥女允兒因胃痛躺在沙發上不能動彈,小姨回家發現后不知所措,著急萬分,用柔弱的身體扶起外甥女去醫院,當然這個情節設計也是引出男主人公數學老師的幫助,為他們兩個人的感情糾葛做伏筆。整個過程中,母愛感染著外甥女,同時打動著數學老師,演員細致入微的情感表現催發了觀眾發自內心的感動。在影片最重要的情節之一的殺人環節,導演并沒有按照原著小說的情節發展去處理,不僅將不得志的數學天才塑造成溫情、可愛的萌叔,而且弱化了前夫兇惡的形象,對犯罪過程也做了人性化的處理。原著中的殺人情節起因是女主的前夫肆意騷擾非血緣關系的女兒并意圖施暴,母親才在憤怒中失手殺死前夫。而韓版電影將此情節改動為小姨的前夫準備離開她們家時,外甥女允兒拿起東西砸暈這個惡人才引發前夫施暴行為,從而小姨在自衛中因過激舉動勒死前夫。
韓國是一個十分重視“血緣”“家門”的民族,導演這種身份安排保留了女主角身份上的純凈度,而且滿足了韓國本土觀眾的審美需求。小姨和母親這兩個身份認同有著明顯差異,方恩珍導演這一改動,著實賦予了女主角更多美好的品質,淡化了女主角性格復雜多元的一面,就連殺人也有一種“遺命托孤”奮力保護外甥女才釀成命案的使命感。身份上的轉換,向觀眾著力促成她“局外人”的身份,使小姨這個角色有著更多的愛和善良的品格。塑造這種無直系血緣關系的相對純美的形象,除了為她與數學老師的純凈溫情化的感情作鋪墊,還十分貼合韓國大眾對女性感情的審美表達。但是這種“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審美塑造,過于本土化的改動,遠離原著作者筆下多面復雜的靖子,失去了深層次探討人物人性的可能性。
3. 日版電影人物形象之悲劇與救贖
東野圭吾認為,人性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沒有人可以說清楚。我們只能不斷地去試著解讀人性。他用不同的故事展示人性的種種可能,卻沒有權力給人性下任何結論。無論是在其小說《白夜行》《時生》《紅手指》中,還是《嫌疑人X的獻身》中,我們都能看到飽滿的人物形象,人物情感背后是多元復雜的思緒,善惡交織在一起。人性確實是在不同的環境下呈現出不同的樣貌。古希臘的悲劇在歷史的長河中沉淀甚久卻依然閃耀著人性的光輝,引導人一次次走上思想的高峰,是因為那些悲劇在對人類精神和人性的不斷探討中,蘊藏著厚重深沉的生命力。回歸電影本身,在日版電影中觀眾一方面清楚地看到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動機,為作者縝密的構思感到驚嘆,并獲得心理上出乎意料的刺激驚喜,另一方面則是在心中留下一絲無法言說的隱痛,刺痛著人脆弱的心衣。
從人物形象看,在日版電影中以堤真一所飾演的數學天才石神性格孤僻自閉,難以與人溝通,在他身上看到了人深刻的命運感。叔本華說,在現實上存在的痛苦,卻無時無刻不受著時間的壓力,它就像監工一樣,手拿著鞭子不讓我們有片刻的喘息。這樣一個能為一道數學公式坐在昏暗的燈光下花費日日夜夜解題的石神,在枯燥無味的生活中逐漸失去信心,在辦完母親葬禮后準備上吊自殺時,靖子母女如沐春風般的溫暖帶給他生活下去的希望,但在目睹靖子母女聯手殺人后,他選擇幫助她們,并殺死流浪漢來頂包。這是對善良母女的生命救贖,但同時也是對另一個生活在底層世界的無辜生命的褻瀆。
而電影中與石神形成鮮明對比的人物——教授湯川學是一個驕傲卻彬彬有禮、自我卻理性的推理天才。他的生活順風順水,無論是事業、年齡和外表都勝過石神。然而在爬山這一情節中,號稱運動健將的湯川學力不從心,屢遭險境,都被石神搭救。這一細節隱喻性地表達出湯川學在現實中遇到了真正的對手。盡管石神敏銳地捕捉到這個時機完全是可以殺湯川學以求自保。有著犯罪前科的石神這一次卻選擇良知,這是高手的對決,心靈上的惺惺相惜。隨后他更改原計劃并設計了“獻身”。如果說石神殺害無辜的生命是為了救贖靖子母女,并使她們活在太陽之下,不必背負道德的負罪感,那后面設計“獻身”的計劃則是石神對自我的救贖,用自己的靈魂堵住已被現實撕破的巨大窟窿。表面上看是故事需要一個合情合理的結局,從精神內涵看,是為正義和情感留了一個可以去探討去解決的出口。
二、不同人物塑造的文化探因
電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與其所屬的民族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電影所呈現出的視感,并不單單是導演一個人的裁定,而是一個民族集體無意識的體現。從一部電影中可以看到一個民族甚至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習慣。
1. 中版電影“中庸化”的抒懷
儒家中庸思想在中國已流傳兩千多年,不僅治國經世、人倫日用,還成為大眾文化中道德修養、經營管理理念的化用。它實則早已融入到中國人的血脈思想之中。《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國歷史上民族的一次次融合、中華文明對外來文化和宗教的包容都體現了中國人中庸思想的寬闊與胸襟的寬廣,從而形成中國人的大局意識和整體觀念。何為中庸?也許“適度”一詞最為貼切,代表事物發展最圓滿的狀態,過猶不及。蘇有朋導演的風格十分貼合中國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他充分吸收日韓兩個版本電影的精髓,保留了原著小說中精練的犯罪過程和精巧的敘事結構,也吸收韓國電影一向擅于表現情感張力的長處,并對電影中每個人物情感表現給予淋漓盡致的展現。
蘇有朋2014年首次擔任電影導演,拍攝了饒雪漫的同名小說《左耳》。他深入研究原著小說中的人物與主題敘事,用影像技術將文學敘事轉化成影視敘事,層次分明,內容結構緊湊,人物性格鮮明。《左耳》是時間線性敘事,以主人公的成長故事和情感糾葛展開,在展現人物命運的同時,引發觀眾對“90后”群體校園文化成長的共鳴和思考。蘇有朋第一次試水采用成熟的小說為藍本,這是一種中規中矩的做法。小說本身就有扎實的讀者粉絲群體,成熟的敘事結構和群體市場,已經讓蘇有朋成功一半,換句話說資金效益和影片成就有了根本的保障。這是他轉型做導演使用“中庸化”的創作模式。他的第二部電影作品《嫌疑人X的獻身》,亦是如此。
該片依舊采用成熟的小說框架進行電影結構。首先,東野圭吾的同名小說風靡亞洲甚至全球,本身就受到一批粉絲的追捧。這一粉絲群體保證了電影的市場票房。其次,在此片上映之前還有2008年日本西谷弘導演和2013年韓國方恩珍導演的同名電影可作參考。他在敘事線和人物表現忠于原著的基礎上,又賦予了中版電影更多的中國元素。這種中庸化的處理方式獲得沒有較大爭議的“成功”。
中版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沿用原著的敘事結構——非線性心理敘事,也就是中國章回體所謂的“話分兩頭,單表一枝”。影片開頭就已經將誰是犯人、犯罪的過程以及犯罪實施的結果這三個在懸疑小說中最主要的因果全部呈現給觀眾。接下來東野把推理小說的精妙之處全部設計在“獻身”環節。與日版電影使用女性警察不同,中版電影以男性警察為主導。警察羅淼通過自身思考不斷請教唐川教授,在請教過程中逐步發現新線索,從而偵破“獻身”案件。中國式影視劇偵查案中鮮有女性警察加入。與西方審美不同,中國電影中公檢法系統普遍是男性,一方面男性代表力量和陽性,另一方面是權力的象征。中國女性代表陰柔和家庭,而西方犯罪片中女性偵探多表現果敢、干練與情感自由。
蘇有朋對《嫌疑人X的獻身》本土化改動最為明顯的就是環境描寫。原小說中環境描寫極少。細數之下,也就四五處,作品整體風格也是偏冷色基調。中版電影開片就看到對居住環境的交代。首先用空鏡頭對景物進行細致描寫,其后用特寫鏡頭拍攝具體環境,營造輕松的氛圍,甚至一改原著中冷淡的風格。空鏡中樓閣一角、嫩綠的盆栽以及午后街道烘托出清新的影調。隨后導演用一組較長的跟拍平搖鏡頭拍攝跳廣場舞的大媽、乞討的流浪者、路邊賣早點的攤位以及晨練的人們。環境拍攝為嫌疑人作案做足鋪墊,同時十分具有中國民眾生活氣息的場景也使電影環境中國化。
2. 韓版電影的“禮節”與“溫情”文化
韓國電影崛起于20世紀90年代,受到亞洲觀眾追捧。韓國文化中蘊藏著儒家含蓄內斂的品調,秉承“發乎情,止于禮”的東方文化觀。即使是表達死亡主題和理性邏輯為主的懸疑推理題材,電影導演也擅長用溫和的角度重新審視人物情感和構建敘事結構。正如高麗大學編寫的《韓國民俗大觀》序言中所言:“至今,儒教在韓國社會中占有絕對的比重……事實上,儒教不僅僅改變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會結構、習慣、制度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所以在當今現代化、西洋化風潮中,韓國在東洋三國仍然是個父法家長制、血緣主義最強的社會,儒教至今仍深深地扎根于我們社會的基層。”從古代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韓國結合自己民族本土文化,形成了一種以中國儒學文化為根基的美學觀念。像席卷各國熒屏的韓國清新唯美的愛情片,就是孔子說的“發乎情,止于禮”,這種含蓄純凈的感情表達同樣應用在韓國版的懸疑推理片《嫌疑人X的獻身》。與中日兩版相比,韓國的版本無疑作了最貼合韓國民眾心理的本土化改動,不僅弱化了犯罪推理過程,而且弱化了人物陰暗暴力的一面。這種本土化改動只為了更多訴諸于情感層面的表達。
相比較中日兩國重視集體主義和國家層面的敘述,韓國電影更著重個人化和民間敘述。韓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現代大韓民國的成立是在美國的強權政治和美韓聯盟的框架下產生的,自由民主的觀念深入韓國民眾之中,但是深入骨髓的儒家文化不會輕易消失。所以韓國文化始終不斷處于一種身份認同和自我質疑的文化心理過程。韓國電影傾向于強化“戲劇性潛力”,尤其是對人物情感線的著力塑造和人物心理特寫化,可以說韓國導演擅長在類型片的框架中再次結構影片。韓國導演在電影改編中進行本土化處理的手法是常常在類型片中再鑲嵌一個新的類型,鑲嵌進去的類型就作為敘事模式。如影片《梨泰院殺人事件》主要講述的是發生在一個快餐店廁所里的殺人案件,但影片的重點不是講述如何破案,而是著重呈現控辯證三方在法庭上人物的情感張力。方恩珍導演的這部《嫌疑人X的獻身》也是如此。
中日版本的電影在敘事脈絡上是按照原著小說文本走向進行的,在人物與情感中,兩版電影將教授與數學老師之間心靈共鳴的情誼和價值沖突、數學老師與女主角之間萍水相逢的救助產生的情感糾葛、以及在案件背后每個人人性的張力三個方面都有所展現。方恩珍導演不重視犯罪推理過程的演繹,而是將影片轉向了在韓國市場上已經打磨成功的犯罪加愛情的敘事模式。韓版影片大大縮減了原著小說中人物性格的多樣性,原著中的湯川學既是教授又是辦案主力,而在韓版電影中“湯川學”就是一個警察,在破案過程中幾乎是一個人的“獨秀”。從發現小貓便簽、查看監控錄像、對比嫌疑人書寫的字跡,將警察這一群體變成個人化敘事,一個人撐起了推理懸疑片中最主要的偵查線路。在中日電影中,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是相輔相成的,即便是想突出教授個人超群的智力和獨特的人格魅力,也會有大量的警方集體出動進行破案的場面。在中日兩版影片中反復出現偌大的辦公室聚集著各種級別和部門的警官,在分析案件過程中,也是集體出現在會議廳進行調查報告的匯報。
而在韓版的電影中,破案這條線不是主線,教授與數學老師之間的情誼和矛盾沖突基本模糊化,人物情感的張力表達才是導演重點。方恩珍導演簡化了偵查人員的設置,弱化教授與數學老師之間的情感沖擊和矛盾。她把大部分功力用于情感線路的鋪墊與升溫,用個人化的敘事手法著重表現數學老師與女主角的感情線路。影片結尾是以凄美催淚的單方面圓滿的結局,完全顛覆原著結尾。這種溫情化影調的處理下,使得主題立意變得淺薄。方恩珍導演削弱原著小說的推理線索敘事結構,強化女主人公與數學老師感情線,使得影片有“主客顛倒”的味道,但更符合韓國民眾的期待心理。
3. 日版電影“人性化”的救贖
日本文化,一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二是受西方近代文化影響。在兩種文化碰撞和糅合下,形成了日本社會獨特的“恥感文化”。這是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為和內部心理、考察了日本人價值體系之后得出的結論。在這種文化下,人們很重視自我審視,其意義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會對自己的評價。作為“恥感文化”的延伸,“恩”和“義理”的觀念在日本人腦海中根深蒂固——受人恩惠等于欠下了沉重的人情債,人們不喜歡平白無故的熱心幫助,甚至會認為施助者是別有所圖。隨著意識形態不斷與經濟發展的沖撞造成日本社會民眾的精神壓抑,人與人之間呈現出一種人際關系的疏離和冷漠。小說《嫌疑人X的獻身》就是基于人與人的隔閡和人與自我的障礙問題展開對人性的深刻探討。從另一方面來說,“自我救贖”成為東野圭吾和日版電影最深層次的表達。
東野圭吾的懸疑推理小說不止局限于懸疑推理和情感表現,而是著眼于對現代人的精神家園的探索,在情節設置中也尋求一種全新的建構方式。與韓版電影對原著小說在敘事表現上較大的本土化改動相比,日版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最為貼合原著的內容。其電影的敘事節奏按照原著的時間順序展開,具有戲劇性沖突的情節也一一符合原著的情節設置,最重要的是對人物形象和情感張力詮釋的非常到位。此外,日版電影中除了加入一個女性警察角色,起到請出教授湯川學參與案件調查的作用,可以說幾乎就是原著的內核沿襲。
首先,在敘事脈絡上,影片中案情一開始就已交代清楚,失手殺死前夫的靖子有著充分的不在場證明,且證據確鑿。隨著劇情發展,也將天才教授湯川學引入這個“盲點題”中。電影忠實地再現了小說中案件全貌,用時間順序架構電影的敘事脈絡。其次,電影忠實還原了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及故事沖突。影片開場是石神穿著老舊的外套,佝僂著腰,腳步落寞沉重,全身散發著與人群格格不入的氣息。電影保留了原小說的厚重與嚴謹的風格,導演用平淡的鏡頭巧妙地展現出石神與靖子蜻蜓點水般的愛。在影片中石神發現工藤送靖子回家,大雨中兩人對望。石神悄悄轉身離去的落寞背影與靖子不知所措的復雜目光相呼應。石神進屋時,收好雨傘放在門邊,放了兩次都倒了,這一個細節拍攝抓住了此刻石神的內心波動。與電影和原小說作者精心設計石神為靖子吃醋的情節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在日版電影《嫌疑人X的獻身》中,導演沒有忘記東野圭吾對人性與愛的闡釋。影片中石神為鄰家母女的付出異常感人,而在最后真相大白時,靖子跪在石神面前表示要承受這一切。日版影片中的石神是咆哮著嘶吼著,而中版電影中的石泓是悲戚仰天,停頓了許久才從嗓子眼兒發出低聲悲慟。正如小說結尾處寫的:“他發出野獸般的咆哮,咆哮里夾雜了絕望與混亂的哀號……石神繼續嘶吼,似要嘔出靈魂。”兩種不同的處理風格顯示出不同的情感張力,日版電影中的人物表現雖然更貼合小說原著,但是中國略為含蓄的情感處理,使得石泓這個角色更具有深意。總而言之,相比較韓國近似“圓滿”的結局,中日版本都表現出東野圭吾想要拷問和關注的人性問題。
三、結語
19世紀俄國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認為:“只有那種既是民族性的同時又是一般人類的文學,才是真正的民族性;只有那種既是一般人類文學的同時又是民族性文學,才是真正的人類的。”這句話同樣適用于電影創作。同一部小說,不同的導演拍攝,不同的文化背景,改編的手法各不相同,也會呈現出不同的風貌。中日韓三國普遍具有傳統儒家文化的思想根基,在思想內涵上體現了對生命的質樸關注和對世界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展現,在敘事觀念和影像風格上也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東方文化的內在精神,浸潤了東方傳統的美學精神和詩意化的旨意。然而不同的文化語境下,在電影藝術的美學創造上,在人物塑造、敘事觀念、背景設置以及主題價值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