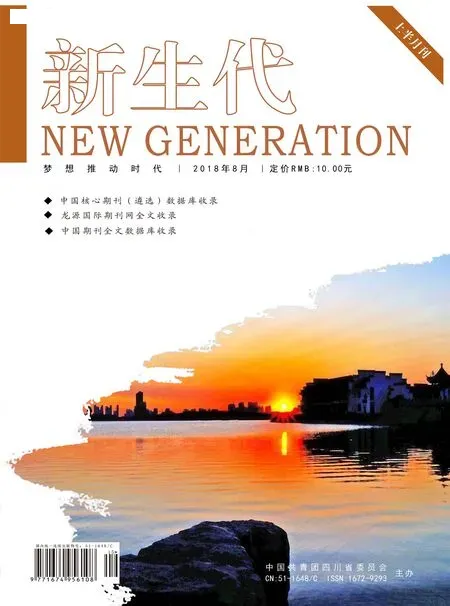簡述唐宋時期的中阿關系
劉文鵬 天津外國語大學
一、唐朝(618——907)時期的中阿關系
中國和阿拉伯國家真正的進行友好往來,要從唐代說起——即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開始,中阿兩國交往頻繁。參考中阿關系史資料,結合唐代文化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他們各自特點,通過論述唐朝時期的中國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以及交往的方式、過程、效果等情況,揭示出兩種文化之間的關系。
伊斯蘭教起源于公元七世紀初,是“封印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島所創立的宗教。在教徒的支持與幫助下,穆罕默德通過十多年的努力奮斗,逐漸地將伊斯蘭教發展成一個絕大多數的阿拉伯人所信仰的宗教,并在麥地那城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阿拉伯——伊斯蘭政權,史料上中國將其稱為“大食”,從此翻開了中阿長達十四個世紀友好關系的新篇章。而在此之前,阿拉伯半島是所謂的蒙昧時期(賈希利葉時期),當時阿拉伯人的文化水平以及文明程度并不高,阿拉伯人之所以聽說過中國這個國家有可能是因為經商或者其他原因。正如先知所言:“學問哪怕遠在中國,也必須去求索”。由此可見,在先知降世之前,中國已同阿拉伯國家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
中國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中國文化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發生了緊密的聯系。如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這兩條道路的交相輝映,把中國和西方、中國和阿拉伯國家緊緊聯系在一起,構成中西交通的大動脈。而唐朝對這種友誼關系的發展有著實質性的作用以及影響。
這一時期的中阿文化交往,首當其沖的應當是阿拉伯使團的傳教。阿拉伯國家第一次正式遣使到中國進行訪問是在公元651年。參考《唐書·西域傳》所紀錄的內容,“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當時,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本·阿凡作為阿拉伯國家最高的統治者與決策者。從這一年開始,直到公元798年,阿拉伯派遣到中國的官方使團,有37次之多。而在這段時間內,最值得一提的是就是白衣大食王蘇萊曼派遣到長安的使節在抵達后,向唐玄宗進貢了阿拉伯特有的寶物,比如金線織袍、寶玉、酒瓶等。究其目的,除了外交任務外,最主要的就是傳教。這種傳教活動,為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鋪平道路。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除了朝貢外交任務外,阿拉伯商人與中國人的商業貿易也被視為一個重要的傳教途徑。因為唐朝的開放政策以及阿拉伯人所享受的福利待遇,除舶腳、收市、進獻外,任其通流,自由貿易,不得加重稅率。唐朝皇帝切身詢問來自阿拉伯地區商人的稅收問題以及唐朝政府嚴厲懲治貪官污吏,確保外來商人正當合法的商貿權利。由于這一系列的開明政策以及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越來越多來自阿拉伯地區的商人先后來訪中國,并在中國從事經商貿易活動,與此同時也促進了伊斯蘭教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在中國地區的傳播發展。
二、宋朝(907——1279)時期的中阿關系
從宋朝開始,政府大力支持并發展海外貿易,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放,廣州、泉州、揚州、明州等港口城市被視為國際港口城市,并慢慢的成為了阿拉伯商人以及商隊第二故鄉。起初,廣州是宋朝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其興旺程度和重要性遠遠的超過其他幾個港口城市;然而隨著時間的發展,特別的南宋以后,泉州以其接近政治中心、政府的大力開發、港口優良等優越條件,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而在海外貿易中的重要性以及繁華程度,逐漸的超越了廣州,成為發展最快的港口城市,這就讓越來越多的阿拉伯商人相繼來到泉州定居,并在這里結婚、生子、生活,慢慢地就被稱為“土地藩客”或者“五世藩客”。來華外商,以大食穆斯林商人最富,最有地位,對外貿的影響也是最大。他們有著自己的聚居區蕃坊和公共墓地,完全按照自己的習俗自由地生活。但是由于伊斯蘭教教義教法需要,阿拉伯人每周必須進行一次集會,因此他們在當地修建了相當多的清真寺,比如廣州的懷圣寺、泉州的清凈寺、杭州的鳳凰寺、揚州的仙鶴寺等等。宋代各地清真寺的建筑,完全能夠證實這一時期已經有大量的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國生活,而這些歷史古跡則是中阿友好關系的最好證明。
以上的陳述,意在反映在上千年的漫長歲月中,中阿兩國之間的交往,相互間進行頻繁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國和阿拉伯都有過輝煌歷史,都曾為發展民族的科學文化而做過不懈努力。當前,我們共同面臨著新的挑戰,就應發揚友好交往、密切交流的傳統,在各自發展的同時,互相學習、督促,共同走向繁榮、富強、輝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