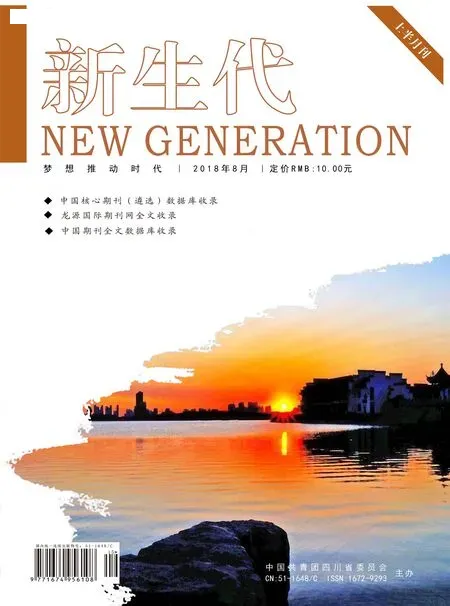于現當代舊體詩詞入史論爭的再思考
周佼 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 浙江杭州 310000
自陳思和、王曉明兩位先生在1988年以“開拓性地研究傳統文學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學現象,對傳統文學史在過于政治化的學術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結論重新評價”[ 陳思和、王曉明:《主持人的話》,《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為初衷,提出“重寫文學史”的口號后,據陳平原先生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 增訂本》中的所言,保守估計已有幾千本的文學史論著。而關于現當代舊體詩詞入史及如何進入的問題,早在上個世紀便已提出,在新世紀初更是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學術界至今仍在熱議,并且論爭逐步深入,也出現了一些專門的現當代舊體詩詞史。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現當代舊體詩詞研究尚未完全進入主流文學史視野之內,即使是有限進入的部分,也并沒有被真正地整合其中,更不必說從根本上改變既定的文學史秩序了。有鑒于此,本文試圖通過“文學史觀”、“話語權力”等角度,對“現當代舊體詩詞入史”這一問題的論爭進行反思與探討。
一、文學史觀之辯
文學史觀是對特定語境下文學史述的觀念預設,是一種有方法論效應的導向性研究框架。“當它設定了楔入文學史的價值視角(曾有人稱‘立場’),也就會衍生出史家甄別與評判相關作家、作品暨思潮的尺度(曾有人稱“標準”)。”
在現當代舊體詩詞入史的論爭中,對于研究主體——舊體詩詞的內涵與外延,雙方基本達成共識,爭論的焦點其實是“史”,更具體而言,是二者文學史觀的沖突與碰撞。支持者的“史”更具時間和空間上的客觀意義,而反對者的“史”則更多帶有文化意義和文學性質。在支持者看來,當前的“現當代文學史”受文學之外的影響太大,而“歷史研究不應該過多地受現實影響”,“尊重歷史是我們的起碼的史德”,應求多元化、更客觀的文學史書寫。在反對者看來,五四傳統、五四精神是當下學科意義上的現當代文學合法性的基礎,而五四革命就是從白話文運動伊始,如果認可舊體詩詞,就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否定,是對現當代文學學科合法性基礎的根本動搖。在這背后,潛藏著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多元“現代”標準。
在支持者看來,自90年代“現代性大討論”后,“現代”被剝奪了“政治寓言”的功能,重建“現代”認同的唯一途徑是“走進歷史,重建歷史理性”。至于“現代性”的問題,“在西方‘現代性’研究從來就是歷史研究,‘現代性’討論的根本應該是對‘現代’是什么的追問,其本質是歷史反思,而不是理念推廣,世界上并沒有亙古不變的現代性標準,”。而在反對者那兒,以王福仁先生為例,中國的“現代性”不同于西方的“現代性”,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獨立知識分子階層出現,將中國社會從一個自上而下的鏈條式權利之塔,拉成一個橫向的“社會”。“中國的現代性”不僅是一種時間觀念和意識形式,更是一種“力量”,一種“能力”。一個認為“現代性”是多元的、沒有恒定標準不斷變化的,需要以多元的認知方式去探索構建真正的歷史理性;一個認為“現代性”具有一個確定的價值取向與標準,最重要的就是“立人”,即人的主體性的自由實現,在這種“現代性”的理解下,只有五四新文化運動才是中國“現代性”的真正起點,所以應徹底堅持五四傳統,并且只有具有完全、純粹的“現代性”的文學,才是真正的“新文學”。在持另一種“現代觀”的學者看來,這便是一種話語霸權。
二、話語權力
王富仁先生明確表示過自己不同意將舊體詩詞寫入中國現代文學史,不同意將二者置于同等地位具有“一種文化壓迫的意味,這種壓迫是中國新文學為自己的發展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戰略”。這種觀點的提出,與王富仁先生對海外新儒家在國內興起、得勢后,可能造成白話新文學價值評價的降低及其在當代文化建構中話語權的喪失這種令其比較擔憂的后果有關。然而,就目前而看,應該是現行的現當代文學學界,通過學科體制、文學史教材、教師講課等話語權力的作用方式,限制舊體詩詞入史,保持文學史秩序、文學史書寫格局和方法論相對穩定不變,以維護自身的話語霸權地位。反過來說,現當代舊體詩詞入史的支持者不斷呼吁、強調入史,正是因為“文學史”是“知識/權力”的一次成功合謀,通過篩選、壓制、改寫、補充等方式,對文學史材料和資源進行重新整合,其最終目的是借助“重新敘述”來實現自己文學敘事的合理性,爭奪話語權力。馬大勇先生認為,現如今與其在是否入史的問題上糾纏不清,不如探討現代舊體詩詞如何入史、如何高水平的入史,將自己的意識形態注入具體的書寫中,而一旦形成自己的新的理論、結構等知識,便會以此來規范文學的生產和傳播,來獲得自身的“文化合法性”。
關于現當代舊體詩詞入史的論爭相信仍會繼續,其他還有許多問題值得去討論,希望通過這些討論,使得學術寬容度提高,價值更加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