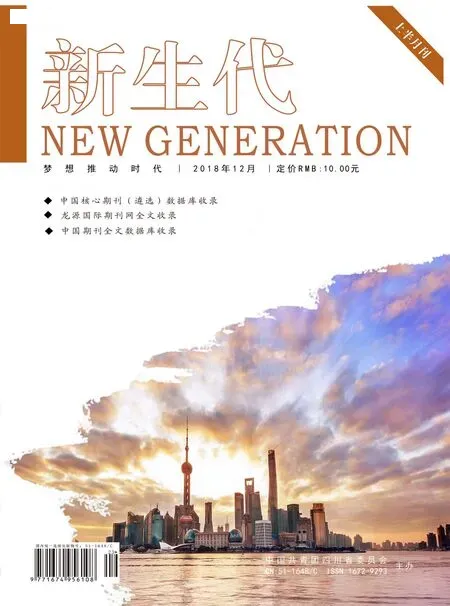論我國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的適用問題
——以“虛假信息”的認定為主要切入口
郭翠爽
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
前言
網絡信息技術的加速發展,信息傳播渠道不斷地更新,網民數量不停地增加,使用信息網絡傳播消息的人也就越來越多。在網絡信息技術發展的同時也滋生了虛假信息,其傳播速度快、范圍廣、帶來的影響不易想象。因此,為了控制虛假信息的產生與傳播,我國出臺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但由于該罪處罰的虛假信息范圍有限,誕生的時間不長,在適用過程中難免存在問題,本文意想通過研究該罪在適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以期能夠帶來一些適用該罪的啟發。
一、“虛假信息”的認定標準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在適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虛假信息內涵不明確,對虛假信息的把握,法官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在此,筆者想通過探討該罪虛假信息的內容,以便為該罪的適用提供思路。
(一)虛假信息的定義與特點
虛假信息是指不真實的、虛構的、根本不存在的信息,或者是對真實信息進行篡改、加工、隱瞞之后的信息。虛假信息具有客觀性、誤導性以及杜撰性。
虛假信息具有客觀性,是“描述性”的事實信息。虛假的主觀性質“事實”信息不應該納入到本罪虛假信息的范疇。眾所周知,我國刑法處罰的是具有法益侵犯性的客觀違法行為,而不處罰思想犯,即是對行為人只存在于內心的犯罪思想不予以刑事處罰,除非該思想予以外化。因此,信息若純粹只表達行為人內心虛假的個人想法,則不應該將該信息納入本罪虛假信息的范疇。如行為人在信息網絡平臺上發布“我想炸汽車站”,對于行為人發布的這個虛假信息就不應當被認為是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所指向的虛假信息。因為“我想炸汽車站”這一虛假信息是一種“犯意”表示,不具有客觀性,不屬于“描述性”的事實信息,一般不會受到刑法的制裁。
虛假信息具有誤導性,會錯誤的引導人們的行為取向以及行為方式。虛假信息是一種錯誤的信息,一旦發布之后往往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不良影響,甚至會造成社會恐慌,這也是我國出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的原因。就是因為虛假信息具有誤導性,會對個人、社會,甚至是國家產生不利,所以我們才需要規制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的行為,遏止虛假信息的進一步擴散。
虛假信息具有杜撰性,即是指信息是虛構的,虛構的虛假信息既包含完全虛假的信息,也包含部分虛假的信息。對于虛假信息的內容有部分真實,但是大部分或者關鍵性信息是虛假的,應當被認定為本罪的虛假信息。
(二)虛假信息的判定條件
對于“虛假信息”的判定條件,多數學者認為,虛假信息不僅包括虛構完全不存在的信息,也包括對真實信息予以修改的行為,但是這種修改必須是實質性的修改。所謂的“實質性修改”指的是故意改變事實,使原真實信息發生了質的變化。關于“質的變化”的把握,可以從“虛假”的反面即真實的角度入手,對于真實信息的界定標準只需要信息本質上真實即可,即是指該信息與所想表達的事實沒有喪失統一性,若是對于所要證明的事實已經喪失了統一性或者該事實在本質上不能證明其真實,就可以被認定為虛假。此外,對于“實質性修改”的判斷還需要結合所可能觸犯的具體罪名,看虛假信息是否對刑法所保護的法益造成侵害。
二、“虛假信息”的規制范圍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將虛假信息的范圍限定在險情、疫情、災情和警情這四種類型,這導致適用過程中存在的第二個問題,即是虛假信息的范圍界定不清晰。
“險情”是指危險的情況,即對民眾財產和人身權益造成迫切的危險或容易造成危險的情況;“疫情”一般是指急性、流行性傳染疾病蔓延、擴散,危及民眾生命健康的情況;“災情”一般指自然災害,如洪水、地震、泥石流等災害,危及局部地區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情況;“警情”是指按照我國法律法規規定,較為嚴重的,應當由人民警察出警處理的相關情況。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疫情和災情還需要與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中的予以區分,從內容上看,虛假災情和疫情是可以包含虛假的重大災情和疫情,從這個角度出發,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是屬于一般法條,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屬于特殊法條;若是從傳播途徑看,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的傳播途徑只能是通過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傳播途徑則廣得多,可以是線上的也可以是線下的,僅從這個角度出發,前罪是屬于特殊法條,后罪屬于一般法條。由此可見,若僅是從特殊法條與一般法條的規定出發是很難對兩罪進行界定。
單單從概念出發,其實是很難把握這四種類型的虛假信息,筆者并不支持將虛假信息的范圍限定在險情、疫情、災情和警情。支持擴大虛假信息范圍的學者認為只將這四種虛假信息作為本罪的規制對象具有局限性,因為虛假信息的范圍很廣,僅限制這四種類型會使其他擾亂社會秩序的虛假信息逍遙法外。反對者認為,限定這四種類型的虛假信息,是出于保護公民言論自由的考慮,要盡量的縮小刑法的打擊范圍,避免因為擴大刑法對言論自由的約束范圍而產生民不敢言的現象。立法者對虛假信息的范圍予以限制是出于平衡刑罰與言論自由的考量,避免虛假信息范圍過于廣泛,而導致人們無法辨別虛假信息,進而引起刑罰適用的擴大化,不符合刑法謙抑性。
三、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其他構成要件分析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在適用過程中,最難以把握的是虛假信息的界定。此外,該罪在適用過程中對行為類型判定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認定也存有疑問。
關于本罪的行為類型,筆者認為存在僅編造行為、僅傳播行為和既編造又傳播行為。對于僅傳播行為和既編造又傳播行為在司法適用過程中沒有太大爭議,基本都認定為本罪的行為方式,存在較大爭論的是僅編造行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的處罰依據在于虛假信息的擴散會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因此該罪處罰的是傳播行為,若行為人只是編造虛假信息而沒有傳播則不宜納入刑法處罰范圍,僅實施編造行為是難以擾亂社會秩序,所以這里的“編造”指的是既編造又傳播行為。但筆者并不認同,筆者認為僅編造虛假信息的行為也屬于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的行為方式,該罪的成立是以信息網絡或其他媒體為載體,基于新媒體的特性,行為人只要編造了虛假信息就難保不會被傳播出去,由此可以推斷出行為人對編造的虛假信息至少出于放任的態度,因而,應將僅編造行為納入該罪的行為方式。此外,編造行為包括兩類,一類是虛假信息的原創者,不管是完全自我創造的虛假信息,還是基于真實信息而改編成的虛假信息,均屬于虛假信息的原創者,是虛假信息的源頭;另一類是篡改已有的虛假信息,在原有虛假信息基礎上繼續胡編亂造,是虛假信息的衍生品。
關于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認定問題。筆者覺得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認定標準可以借鑒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因為在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中網絡只是被作為該罪的一種犯罪工具,其所侵害的客體為社會秩序,自然包含現實社會秩序,本罪打擊造成了現實社會中秩序的混亂,使一般公眾的生產、生活、工作等活動無法正常進行的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的行為。但問題在于網絡秩序能否被評價為刑法上的現實社會秩序?這一直是學界爭議的焦點之一,筆者認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規定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編造、故意傳播虛假險情、疫情、災情、警情的行為,是其打擊對象,即表明刑事立法已經承認網絡空間是具備客觀性與現實性。
綜上,僅編造行為應屬于本罪的行為方式,對于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認定可以借鑒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認定標準。
四、結語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作為《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在適用過程中主要存在著對虛假信息的判斷、對行為方式的界定、對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認定這些問題。
對于虛假信息可以在虛假信息后加上“等”或“其他”,擴大虛假信息的范圍,并不會違反言論自由原則,也不會超出國民預測可能性,只要在適用該罪時明確虛假信息的內涵以及特性。對于僅僅只實施編造行為也構成本罪,編造行為不僅指完全自我虛構的信息,也包括對真實信息予以修改的行為,但所修改的信息要達到質的變化。對于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認定,則可以借鑒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里的認定標準。